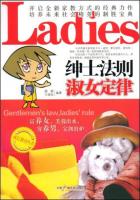小时候,一入冬,穿上棉袄,屋里生着了暖和的煤球炉子,就盼着过年。过年的好处说不完,穿新衣、逛厂甸、买空竹、放鞭炮、吃饺子,来了客人还有压岁钱,哈,最好玩的是堆雪人,打雪仗!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哪年冬天不下几场雪的。而且总有一两场大雪,静悄悄地满天鹅毛飞舞,大人们就会说:瑞雪兆丰年!有时候大雪从夜晚下起,清早推门一看,院里积雪盈尺,我和弟弟撒欢儿似的往外跑,大人也笑着叫着:“别乱踩呀!踩瓷实了扫不净。”赶紧拿笤帚扫出路来。四合院里要扫出好几条通道,北屋通到南倒座,那边是厨房,得过去烧水、洗脸、吃早点,东西厢房也得有路通到大门洞去。大人们总爱把雪扫到枣树根儿和葡萄架下边,说是有雪堆儿捂着,明年的葡萄和枣儿更甜。孩子们另有说法,“家雀儿偷葡萄,老鸹也偷枣儿吃,得有人看着哇!”便齐心协力拍出两个白白胖胖的雪人来。
胡同里的情形就不同了,男孩子们好胜,东头几家,西头几家,组成两队打雪仗。女孩子负责捏雪球,提供炮弹。直打得人人中弹,个个挂花,两只小手冻得通红,大人出来充当“维和部队”,双方才勉强休战。
后来我真的当了兵,到朝鲜去打仗,仍然喜欢下雪,喜欢睡雪窝窝。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在山坡树林里宿营。北朝鲜的隆冬,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雪是零摄氏度,所以每人挖个雪窝窝,砍些松树枝叶垫底儿,铺上雨布、毯子,睡下去的确比外面暖和得多。
复员回北京之后,我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为农业服务,也跟农民一样喜欢下雪。入冬以后如果有几场雪,那可太棒啦,“雪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这等于给冬小麦普遍浇了水,还给它盖上了棉被——雪是暖和的,寒冷的西北风就伤害不着这些越冬小麦了,来年一定丰收!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忙于写作,为减少应酬,常到江南去躲年,都能赶上下大雪,玻璃窗上结满冰花儿,那奇丽的图案,美极了,真是神工造化,舍不得把它擦掉。出去踏雪散步,雪花滤过的空气异常清新,令人心旷神怡,文思敏捷。
妻子的两位姐姐,我也跟着叫大姐和三姐的,家住上海、武汉,都说江南的冬天冷,没暖气呀,退休了,喜欢到北京来过冬。我笑着说,真是怪了,北京今年又是个暖冬,一年比一年暖和,直到十二月中旬还没有一点儿要下雪的意思!你们喜欢北京,那好,咱就换着住,我又可以到江南躲年去了。
女儿不愿意我去南方,说是爸爸不在家,过年都不热闹。她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问道:要是下一场大雪,把空气过滤得清清爽爽,您还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