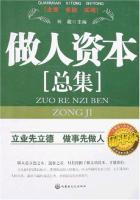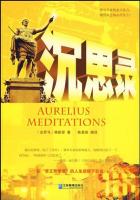曾国藩读书求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世”,从个人角度讲为了建功立业,从国家角度讲为了拯救时局,所以曾国藩的苦学不是死学,更不是毫无目的地瞎学,而是直接为了“成大事”这一目标服务,并为此修炼一身治国治军的真本领。
(1)以安民歌收复人心
曾国藩以文荷道的理念,使他成为桐城学派一杆旗帜。他不但撰写慷慨激扬之文字,以求荷道之本心,还自撰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收复人心。当曾国藩的湘军还没有练成时,太平军又大军压境,湖南人心浮动,四处乱逃,如果老百姓逃光了,还有什么兵可练,什么仗可打呢?曾国藩见了这个局面,深知安民第一重要,乃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派人四处张贴,又派了许多人去各地劝慰百姓,不要乱逃乱跑,果然收效甚大,人心一时大定。这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是: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俱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响。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室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无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为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遭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走徙。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将“文以荷道”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是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大学问”家的特殊之处。湘军训练手本,就是曾国藩自拟的爱民歌。这首《莫逃走》的民歌,是一首白话诗,也就是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深入浅出,富于情趣,它又是湘军的识字教本。曾国藩每日只教一句二句,令其先识字,后识义,循环复习,身体力行,因此湘军纪律较好,曾国藩致函胡林翼:“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又尝自称:“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泣杜鹃之血”。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学为主流,在其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曾表现为由原始儒学而汉唐经学;由汉唐经学而宋明理学。他们各自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们先后替代,显示了各自的别有意蕴。
(2)讲求经世之学
曾国藩崇尚程朱理学,但并无门户之见。他出入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他对儒学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一方面,他在吸取众家所长的过程中,看到了不同意蕴中的本来价值。因此,“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这其中包含着曾国藩有意于超越汉唐宋明,去追溯原始儒学的趋向。这使得曾国藩在晚清诸多理学家中,带有几分“改革”的色彩。他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使理学与原始儒学的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在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衰微理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曾国藩虽然“一宗宋儒”,却把“经济”之学明确地作为孔门学说中不可缺乏的独立门类,讲求经世之学。他一变理学家的传统,抛弃了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风,不仅大力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而且特别注重恢复理学的经世功能。曾国藩在“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基础上,将唐鉴等理学家三种学科的分类,即义理、考核、文章,改为四种,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他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语言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之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目的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为此,他一生不尚虚文。
“荷道”、“经世”是曾国藩学文求理的目的所在。他的经学思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围着经书转、从经书到经书那种书斋式的和学究式的。这是他的经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特点。这个特点根源于曾国藩的效忠封建王朝的鲜明立场。这个特点决定着曾国藩主要不是经学家,而主要是政治家。单就他的思想而言是如此,若就他一生的整个活动而言,自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