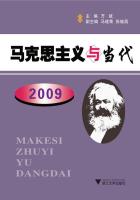处理天津教案恐怕是曾国藩平生遇到的最大难题。因为以前两军对敌,无论多么艰难,他都能明白无误地知道该怎么去做。而这件事却是无论怎么处理,都是几面不讨好。为此,他只好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对之。
(1)天津教案引起纷争
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重大涉外事件,引起朝野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检获拐匪张拴、郭拐两人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是流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愤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多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妇死者数十口,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发生以后,当时七国军舰停泊在大沽口外,以军事威胁清政府惩办天津地方官及民众,法国海军司令竟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法国公使罗淑亚“二十四日致曾国藩照会,内称必须将天津府县同陈国瑞先行在津立即正法,然后余事不难商办,否则饬该国水师提督便宜行事等因,崇厚亲赴罗淑亚处,再三剖析,该使坚持不听。”当法国水师提督伯理赶至天津以后,有了海军作后盾,他们大行炮舰外交,声称如若不按公使要求办理,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同撤往上海,拉出断交开战的架势。天津民众在案发当天,出于义愤,一哄而起,杀洋人,烧洋楼,“人心汹汹,拿犯人说,势不能行。”曾国藩由保定到达天津以后,绅民们的反教狂涛并没有平息,盛传曾国藩是由朝廷派来天津驱赶洋人的。当曾国藩一进天津城门,由天津48保所选派的代表,便拦路请愿,指控教堂残害中国人,并诛杀幼童挖眼剖心。与此同时,在京的王公大臣也高谈阔论,与“清流派”一起大肆宣扬民心可恃,甚至扬言最好乘机“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起码也要与法国断交,以示惩戒。
(2)曾国藩奉旨接下
这个烫手的山芋津案发生以后,清政府两厢为难,于是便把难题推给了曾国藩。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四日(1870年6月22日)的上谕中说:匪徒拐迷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不可赦。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正谕中又说:至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均着查拿惩办,并着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清政府在上谕中,左一个“持平办理”,右一个“秉公办理”,肇事双方都要“严惩”。这似是而非的旨令无非是要给全国舆论一种印象,似乎朝廷并不想示弱,而实际上是“朝廷不肯明持正论,欲从外间发端,于中取决耳。”也就是一旦讥议纷起,便下推责任,诿过于人。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六月七日曾国藩到达天津,面对着业已十分高潮而偏激的民众情绪,如果进一步加以鼓励,势必会造成一场盲目排外的群众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针对法国教堂及其传教士,而且会波及到所有的外国教堂、传教士以及外国人,最终是酿成一场新的战端。
(3)力图以实力外交解决问题
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和捻军人民起义之后的中国,国力孱弱已极,一旦“衅端一开”,必定是“全局瓦裂”。在这场中外交涉中,曾国藩奉行的是实力外交,但他不同于以往的实力主义,只认识到了中西实力相差的悬殊,而对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相反的是曾国藩在看到中西之间的差距后,却用可变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世界,他有了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愿望,鄙视那些“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苟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之徒。正是由于曾国藩奉行的是实力外交的既定方针,他在承办这起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天津教案中,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化解国际国内矛盾,以免授人以柄“致成大变”。曾国藩着手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从调查入手,弄清案情真相。办案伊始,曾国藩向朝廷提出:“总以武兰珍是否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当时朝廷嘉奖曾氏的这一见解,“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
经调查:
1.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时供时翻。
2.仁慈堂查出男女150余人,均称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之事。
3.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查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无实据。
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六月二十七日给美国政府报告天津教案起因时,亦未提到拐骗幼童,挖眼剖心之事,其中说道:“约在五月底六月初,天津育婴堂内发生流行病,有大量孩童死亡……人群多次围集教堂附近,要求把孩子放出。一次,人群喧闹异常,修女因恐暴徒行凶,同意由五名民众组成检查小组入育婴堂检查。法国领事闻此骚动,即于此时赶到现场。五人小组虽已推举好且进入育婴堂,法国领事却下令停止检查,并对五人小组进行怒斥,把他们轰出堂外……”。有人提出,人心人眼等物是由崇厚收藏的,曾国藩辩解说: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心人眼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曾国藩还具体地分析了津民所以产生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谣传的原因有五: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中国人至仁慈堂治病,恒久不出;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不得相见;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天津教案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道者的昏愦和群众的愚昧落后。轻信所谓挖眼剖心,作为点银和药之用的谣传。曾国藩详加辩析道: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眼珠若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既云残害,其尸具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既然对法国教堂是否残害中国幼童这一要害问题,查无实据,造成“审虚则洋人理直”的格局。这就为查处天津教案定下了基调,“若其曲不在洋人,则津民为首滋事者,尤须严查究惩”。第二,把法国与其他国家,分别处理。曾国藩在保定赴天津途中就上奏朝廷,先料理俄国误伤之3人、英美两国之教堂,不与法国一并议结。这一着高明之处在于:使法国不致与其他国家串通一气,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从而扩大事态,增加办案的复杂性。第三,竭力保护爱国地方官的人身安全。案发后,法国公使罗淑亚一口咬住“主使说”,即津民杀洋人烧教堂是地方官员所主使,从而要求惩办地方官员。在这一要害问题上,曾国藩有理有节地驳回了其无理要求。六月二十一日(7月28日)崇厚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按,曾国藩)峻词拒之。六月二十二日(7月29日)洋官罗淑亚复来,词气凶悍,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曾)公将现在查办情形复洋人,并驳诘之。六月二十五日(8月1日)洋人照会仍执前说,二十六日(8月2日)(曾)公照复诘之。六月二十八日(8月4日)曾国藩向朝廷陈述自己的见解:将张光藻、刘杰等革职交刑部治罪,办理已属过当,此次罗使(罗淑亚)欲将天津府县同陈国瑞在津正法,断无如此办理,万难允准。蛮横无理的罗淑亚继续顽固坚持其“主使说”,七月十一日(8月16日)李鸿章奏,罗淑亚必欲将天津府县正法,其照会内称,实由府县帮同行凶,又称有主使动手之人。
七月十六日(8月21日)罗淑亚到京接晤后,仍以主使之说归咎府县各官,持定前议不稍通融。罗淑亚送交总理衙门《天津滋事记》一文,内称:“天津教案,皆府县所刁唆,陈国瑞搭桥助凶,并应正法,以见法国之不能轻纵。”其时,曾国藩巧妙地把张光藻、刘杰二名奉旨治罪人员保护起来了,“一往顺德就医,一往密云安置眷累”,闻天津府县呈递亲供时,承审官以酒食宴会相待。”其所以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也出于不得已的违心之举,他在家书中透露:罗淑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曾国藩对张、刘二员最后之惩处,既有自慰又感不安:“府县到部后,部堂极相关顾,未曾略有困辱,惟定谳时改发黑龙江,微觉过重。”第四,在缩小缉凶范围上有所努力。缉凶,是办案的关键问题。在外有列强内有清政府的双重压力下,作为查办大员虽有所抵制,但一再让步,应负有一定罪责。截止八月十七日(9月21日),曾国藩赴天津两个多月后,缉凶结果是,确有证供应正法者七八人,略有证供应治罪者约二十余人,清政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案情重大,各国伤毙商民亦多。若正凶仅讯出七八人,此外任其漏网,恐无以服洋人之心,且此案为日已久,若不赶紧办结,必至另生枝节了。”朝廷对曾国藩不满的是两点:一是缉凶的数目字少了。二是缉凶的时间拖长。在限期迫近,朝廷催逼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改变缉“凶”人数与被杀洋人数大致相等的初衷,会同丁日昌连夜审问,为拼凑“正凶”人数,不得不变通律例,只要是打过洋人或只要有两人以上的旁证,都以“正凶”定案。
曾国藩在被调离直隶总督任之前,终于向清政府和国人呈上了他议结津案的方案: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二十名死刑,充军流放者二十九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论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有人竟作对联一副讥讽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曾国藩声望一落千丈。
虽然天津教案最后的结案是曾国藩做出的,但是真正的幕后决策者是清政府。在承办该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确曾通过种种努力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而最后却迫于清政府的重重高压不得不滥用他的所谓“霹雳手段”刑加于无辜的平民,落得“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