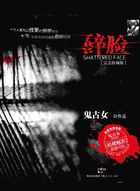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香港)刘以鬯
我是一只苍蝇。
我在一个月以前出生。就苍蝇来说,应该算是“青年苍蝇”了。
在这一个月中,我生活在一个龌龊而又腥臭的世界里。在垃圾桶里睡觉,在臭沟里冲凉,吃西瓜皮和垢脚,呼吸尘埃和暑气。
这个世界,实在一无可取之处,不但觅食不易,而且随时有被“人”击毙的可能。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苍蝇过的,我怨透了。
但是大头苍蝇对我说:“这个世界并不如你想象那么坏,你没有到过好的地方,所以将它视作地狱,这是你见识不广的缘故。”
大头苍蝇比我早出世两个月,论辈分,应该叫它一声“爷叔”。我问:“爷叔,这世界难道还有干净的地方吗?”
“岂止干净?”爷叔答,“那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哩,除了好的吃,好的看,还有冷气。冷气这个名字你听过吗?冷气是人造的春天,十分凉爽,一碰到就叫你舒适得只想找东西吃。”
“我可以去见识见识吗?”
“当然可以。”
爷叔领我从垃圾桶里飞出。飞过皇后道,拐弯,飞进一座高楼大厦,在一扇玻璃大门前面小旋。爷叔说:“这个地方叫做咖啡馆。”
咖啡馆的大门开了,散出一股冷气。一个梳着飞机头的年轻人摇摇摆摆走了进去,我们“乘机”而入。
飞到里面,爷叔问我:“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这地方真好,香喷喷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这样好闻的气息。男“人”们个个西装笔挺,女“人”们个个打扮得像花蝴蝶。每张桌子上摆满蛋糕饮料和方糖,干干净净,只是太干净了,使我有点害怕。
爷叔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好独自飞到“调味器”底下去躲避。
这张桌子,坐着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白脸男“人”。
女人说:“这几天你死在什么地方?”
小白脸说:“炒金蚀去一笔钱,我在别头寸。”
女人说:“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天天给你零花钱,你还要炒什么金?”
小白脸说:“钱已蚀去。”
女人说:“蚀去多少?”
小白脸说:“三千。”
女人打手袋,从手袋里掏出六张五百元的大钞:“拿去!以后不许再去炒金!现在我要去皇后道买点东西,今晚九点在云华大厦等你——你这个死冤家。”说罢,半老的徐娘将钞票交给小白脸,笑笑,站起身,婀婀娜娜走了出去。
徐娘走后,小白脸立刻转换位子。那张桌子边坐着一个单身女“人”,年纪很轻,打扮得花枝招展,很美,很迷人。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朵丝绒花。
我立即飞到那朵丝绒花里去偷听。
小白脸说:“媚媚,现在你总可以相信了,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
媚媚说:“拿来。”
小白脸:“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媚媚说:“什么事?”
小白脸把钞票塞在她手里,嘴巴凑近她耳边,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只见媚媚娇生嗔气地说了一句:“死鬼!”
小白脸问:“好不好?”
媚媚说:“你说的还有什么不好?你先去,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人。我在一个钟点内赶到。”
小白脸说:“不要失约。”
媚媚说:“我几时失过你的约?”
小白脸走了。
小白脸走后,媚媚走去账柜打电话。我乘此飞到糖盅里吃方糖,然后飞到她的咖啡杯上,吃杯子边缘的唇膏。
正吃得津津有味,媚媚回座,一再用手赶我,我只好飞起来躲在墙上。
十分钟后,来了一个大胖子,五十岁左右,穿着一套拷绸唐装,胸前挂着月形的金表链。
大胖子一屁股坐在皮椅上,对媚媚说:“拿来!”
媚媚把六张五百元的大票交给大胖子,大胖子把钞票往腰间一塞:“对付这种小伙子,太容易了。”
媚媚说:“他的钱也是向别的女人骗来的。”
大胖子说:“做人本来就是你骗我,我骗你,惟有这种钱,才赚得不作孽!”
这时候,那个半老的徐娘忽然挟了大包小包,从门外走进来了,看样子,好像在找小白脸,可能她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但是,小白脸已走。她见到了大胖子。
走到大胖子面前,两只手往腰眼上一插,板着脸,两眼瞪大如铜铃,一声不响。
大胖子一见徐娘,慌忙站起,将女“人”一把拉到门边,我就飞到大胖子的肩膀上,听到这样的对话:
徐娘问:“这个贱货是谁?”
大胖子堆了一脸笑容:“别生气,你听我讲,她是侨光洋行的经理太太,我有一笔买卖要请她帮忙,走内线。你懂不懂?这是三千块钱,你先拿去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关于这件事,晚上回到家里,再详细解释给你听。——我的好太太!”
徐娘接过钞票,往手袋里一塞,厉声说:早点回去!家里没人,我要到萧家去打麻将,今晚说不定迟些回来。
说罢,婀婀娜娜走了。
我立即跟了出去。我觉得这“天堂”里的“人”外表干净,心里比垃圾还龌龊。我宁愿回到垃圾桶去过“地狱”里的日子,这个“天堂”,实在龌龊得连苍蝇都不愿多留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