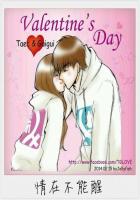失血过多,猛然一下子停止了剧烈的动作,姜成久顿觉全身不住的沁出虚汗,眼前逐渐的开始模糊起来,头脑一阵的眩晕,全身瘫软无力的偏靠在了座位上,悠闲的体会着肉体上的创痛。“老薛,还有多久才到国境线上。“杨从涛放下枪身烧得烫手的MK19自动榴弹发射器,怒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虎眼,躁急的问道:“老薛,到底还有多久才到?“
袖子抹了一把热汗,老薛粗声大气的回答道:“这帮白眼狼的射击很精确,我只绕道飞行,最少也得要三四十分钟。“
“油料还够消耗吗?“李参谋长放下打得冒烟的轻机枪,关切的问了一句。
粗率的扫了一眼油抖表,老薛洪声道:“估计再连续飞上两个钟头没有问题。“
“妈个巴子的,本来早该到了,这些兔崽子们纠缠不休,搞得我们跑了大半天的冤枉路,真他娘的可恶。“杨从涛怨气冲冲的咒骂着那些围追堵截的敌人。
“现在都快下午2点了,我们足足与白眼狼玩了7个钟头的追猎游戏。“邓飞龙用一块抹布擦着手上沾带的血渍,神采飞扬的说着话,像一只斗胜了的公鸡那般的精神抖擞。
危险解除了,老薛就把直升机降低了很多,与地面保持着三四十米高的距离飞行。
危险解除了,并不等于就安全了。邓飞龙放不下心,也闲不住,他打开一箱子弹,取出三个空弹匣压满子弹,又往衣袋和裤兜里塞了七颗手雷,然后从马龙欧遗体上的弹袋里抽出两个弹匣,一副蠢蠢欲动,如临大敌的势头。
一旁,杨从涛有点诧异,有些爽然地道:“怎么了?小邓,你急着要单独出任务吗?“往包里塞进三枚66式反步兵定向碎片雷,莞然一笑,邓飞龙平谈地道:“有备而无患嘛!“
飞跃过一座植被密密丛丛的高峻山岭,旋翼拔风的呼轰声中邓飞龙隐隐约约的听到几声稀落的犬吠声。
有点激奇和谨慎,邓飞龙凑到舱门边上往下俯瞰,映入眼帘的是两道山岭夹峙着一块大坝子。
坝子的上空飘浮着一抹抹袅袅的炊烟,哦!坝子里还座落着一个看上去很贫瘠的小村庄,三五十间用茅竹和叶木修造的低矮草屋横倒竖歪的摆放在那里,仿佛刻意在向邓飞龙彰显安南人民的贫困和落后,也从侧面反映出安南政府穷兵黩武,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种下的恶果。
村庄的两边夹峙着草深林密,郁郁葱葱的山岭,东头覆盖着茂盛的灌木丛,西头密植着大片的茅竹林和绵密的芭蕉树。太阳光金亮亮的洒照在茅屋上,为小村庄素裹上一件熠熠生辉的金色亮装。依稀的看得见村外的田间和菜地里有老百姓匆匆匆忙碌的身影。
直升机飞得更近了,邓飞龙看得清楚些了。村口有三个男娃子抄着竹棍子在绕着几棵芭蕉树在追逐撵打。挨着不远,五六个小女孩在凉晒着农作物的空地里蹦蹦跳跳,欢天喜地的玩乐着。
湛蓝如洗的天空,点缀着零零星星的几朵白云,初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春寒料峭的微风悠然自得拂拭着生机勃发的山水草木,密密匝匝的苍翠竹林随风翩翩起伏,山间小村里呈现出一片春光烂漫,欣欣向荣的气氛,似乎与烽火狼烟,血腥弥漫的战争八尺竿头打不着。
往M79弹膛填进一发M406高爆弹,把剩下的弹药塞进舱座下面,邓飞龙惬怀的舒了一口气,倒想借此机会考察一番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人民生活状况,是富足美满呢?抑或是贫困寒酸。
于是,他提足目力的朝小村庄的西头仔细搜视过去,三点方向,田间里有三个驱赶耕牛犁地的村夫,他们都打着光脚板,身上披挂着破破烂烂,大眶小眼的衣物,矮小的身形干瘦得形同凉衣竿一样,看上去老苍苍的,应该是三个上了年纪的庄稼汉。
安南连年征战,干戈不断,青壮男子的损伤尤其严重,兵源空前绝后的枯竭,就连精干一些的妇女也被征招入伍,甚至还拉上半大的孩子来充当狼子野心的炮灰,增添战争绞肉机中的新鲜血肉。
正因为如此,在安南但凡年富力强的,精壮能干的男人都被强制征招到军队里当兵,或参加民兵和青年冲锋队。留在农村耕作的无非是些年老力衰,体弱多病,或是缺胳膊少腿的货色。
也可别小觑了这些不中用的人,在当局的愚民政策的熏陶下,在仇华思潮的鼓动下,无论妇孺老幼都善于舞枪弄炮,而且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玩起命来毫不含糊,都是些擅长争强斗狠的主儿,跟这些人打交道千万不可马虎大意,也不得掉以轻心,更不能心慈手软。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邓飞龙很同情穷得连灰都舔不起来的安南人。也是的,常年累月,无休无止的战争使安南损失惨重,经济达到崩溃边缘,民不聊生,寡妇哀村。他们有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留下数不胜数的孤儿寡母背井离乡,投奔怒海,苦不堪言,再上资源匮乏,缺衣少粮,更令外强中干的安南雪上加霜,已达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随着直升机轰鸣声的逐步逼近,其中两个有两个家伙停住手里活儿,抬起头伸长脖子仰望着天空中的不速之客,一边对着天空指手划脚,一边叽哩呱啦的交头接耳,俨然一副无所畏惧的架势。
有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家伙怒气冲冲的,狠狠的把锄头抛摔到地边的水沟里,摆出了敌对的姿态,看来这些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家伙倒还灵敏,已经辨认出了天上飞的是中国的军用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