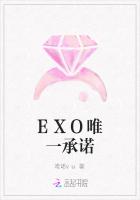公共权力是公民依法让渡的权利,公民是公共权力的主权者,公民选举少数优秀公民代表立法创制确定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公民推举良官执掌公共权力,以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保持公共权力的公正,监督官员不腐败,保证公共权力不被出卖,使公共权力机关具备高度的公信力和廉洁高效的行政效能,始终是国外公民学努力探寻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权力的起源这一问题存在着生物学、心理学、文化、理性和非理性的诸多解释。在这些探讨中,最早从逻辑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了17、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又进行了系统论证。可以说,这两次论证直接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发展,也为国外公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公共权力起源于两种社会需要:一是调整社会关系;二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这两种社会需要的相关分析构成了寻找公共权力起源的逻辑。本节主要介绍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等关于公共权力的思想观点。
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一)人性假设:天生的社会和政治属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公共权力起源的论证建立在他们的人性假设之上——认为人天生就具有社会和政治属性。这一看法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传统,早在《荷马史诗》中,脱离政治生活的人就被视为野蛮的象征,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有一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判断也常被学界归于生物学的解释途径。大意是人就像蜜蜂和猴子一样,有着群居的天性。他们为了获得食物和谋求生存而本能地相互合作、帮助,并像其他群居动物一样,自动排列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序列。在亚里士多德的启示下,现代生物学研究进一步表明:形成一个政治系统并服从领导者是人类天生的行为,是代代相传的。当然,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天生就具有政治性,我们又如何解释政治群体的分裂和人们对权威的不服从。或许我们在理论上可以退一步:人类是不完美的政治动物,人们在大部分时间结成群体、服从权威,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会这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所造的每种事物都有一个目的。人类的目的是实现所谓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是最本质性的。人只有实现了灵魂的善,才真正有别于动物,才实现了人的本性。而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社会团体都不能使人实现这三种“善业”,只有城邦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性,就必须成为城邦的成员,过城邦生活。
基于这一人性假设,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公民、城邦以及二者的关系时,秉持整体主义的观点,即把城邦比作有机的整体,认为个人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城邦,离开了城邦,人就无法完善其身。正如其所言:“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他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只”。因此,城邦是“若干公民的组合”,“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而公民则是“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即有权参加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的人们。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这种抽象的诠释内含着公民的普遍信仰,即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类完善自身必不可少的前提,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人才是完善的真正意义的人。
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假设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们以此论证城邦(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起源,认为它们是自然生成的事物。柏拉图认为,城邦和公共权力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柏拉图那里,城邦和公共权力起源的历史描述与国家基础的逻辑推演是结合在一起的。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有农民、牧人、各种工匠等,而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他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其职责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后来,城邦生活不断扩充,人的欲望和需求不断增长,就出现了城邦之间的战争。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就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他们的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并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最后是统治者等级,他们是由军人等级中挑选出来经过精心教育训练而产生的哲学家,其职责是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至此国家便正式形成,公共权力也就产生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同样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落,若干村落组成城邦,从而形成最高级的社会团体。因而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
(二)目的假设:整体幸福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整体幸福观为出发点,认为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是为了公共利益。对于他们二人来说,公共权力是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像资产阶级启蒙者那样认为公共权力是由个人权利所派生的。在他们看来,公共权力直接来源于对城邦的统治,公共权力的目的皆源于“正义”,而“正义”又具体化为公众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和幸福而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要符合正义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直接为城邦及其权力打上善的标签,认为城邦生活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善,善就是一种优良的生活。同样,奴隶也不是苦难的,因为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位置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合使得二者相互联系而共同保全,奴隶和主人是二者有着共同利害的自然结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被统治者放于一个心甘情愿的位置,并且打上了共同幸福的标签。但亚里士多德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证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行使,即政治体制的建构,同时指出任何违反公共利益的政体都是不正当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一个政治制度就是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其实质是在公民间调整权力关系以更好地达到城邦生活的和谐。
二、霍布斯和洛克的论证
在中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传统得到延续,而这一传统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终被打破,后者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公共权力起源的论证模式,这一模式就是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基于自然状态前提的社会契约论模式。
(一)人性假设:自然状态下的自利人
在人性的假设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学者否认了人天生具有社会和政治性,而认为人是个体式的,这种个体式的人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霍布斯认为,人性的三大自然特点——竞争、猜疑和荣誉感引起人际关系的混乱无序,但同时人在能力和才干上都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彼此消灭的权力,从而使自然状态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判定公正与不公正的公共权力和法律,所以人生来不是社会性的,自然使人们相互分离。但自然状态也有其积极意义,正是因为自然状态的不足使道德和政治生活成为一种需要,并建立了政治社会。而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的社会性本能产生于满足生活需要的动机,因为无论是柏拉图的分工互助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自然生成论,他们都认为单个的人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即使组成家庭和村落,人们也不能自足,要满足就要结成共同生活的社会团体,这其实都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内在倾向的推动。而霍布斯的分析却建立在另一种心理学的层面上,他认为人是自利、竞争、猜疑而又具有暴力倾向的,在这些情感的驱使下,导致的是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由此产生的是人类自我保存的需要,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对人的判断的基础不同。
所谓自然状态学说,就是设想人类在远古时期即产生阶级、国家和私有制以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此状态中没有阶级、国家、政府和法,也没有私有制财产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勾心斗角、压迫、侵略和掠夺及战争状态,也不知商品货币。不过,这样一种状态究竟属于一种理想的黄金时代还是蒙昧未开的蛮荒时代,思想家们在这里产生了分歧。在霍布斯看来,人对人像狼一样,没有政府、国王、贵族、宗教和法,人类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状态,格斗杀戮,相互攻击,搞得人人自危,只得相互订立契约,出让主权,让一个人或一群人统治,以换得秩序和安全。洛克却构造了一个和霍布斯不同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处理自己的事物,而无须别人的许可,或听从任何人的意志。但是,洛克又认为,由于人们利己的天性使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所享有的权利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断受到他人侵犯和威胁,特别是生命和财产,因此人们便“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有三大缺陷:第一,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这个法律是为人们共同承认和接受的,可作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它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判决一切政治的知名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自然状态本身无法克服这些缺陷,为了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人们便订立契约,把自然权利转交给社会,根本上讲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利。
(二)公共权力的目的:个人权利的诉求
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整体幸福观出发不同,霍布斯和洛克把个人权利的自我保存作为设立公共权力的目标,前者是整体主义,后者是个人主义。自我权利的保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取向,它是霍布斯对古典政治学道德传统的一次舍弃。霍布斯认为,整个传统政治学,无论是在探求真理中,还是在引导人们走向和平方面都是失败的。对霍布斯来说,对自我权利提供保护的政治社会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乌托邦蓝图更有效,因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本身来自于人的更切实际的情感需要。
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霍布斯把它称为自然律、道德法则、理性命令。无论是自然的法则,还是政治社会的法则,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到此,我们可以看出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阐发的传统自然法观念和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法的区别,正如施特劳斯所说,“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起始于人类意志”。由此可见,个人的权利诉求构成了霍布斯的学说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本质区别。
同样,洛克的态度也是现实主义的,只是洛克自我保存需要产生得更复杂些,因为他设立了两种状态——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时人们期望和平,因而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权威。自然状态下,尽管人们都按照自然法的支配行事,但是在自然法的执行上还是存在着差别。因为人对自然法的无知和理解的偏差或者人本身的偏见和自私心理会导致对自然法的不正当使用,公民政府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治办法。
(三)社会契约理论
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社会契约是自然社会到政治社会的转换器,公共权力由大家约定产生。如同自然法一样,契约观也是自古有之,但它的系统化却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奠定的。鉴于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利以及大家对自我保存的希求,人们在权利的相互转让中彼此建立契约,但是单以言词来约束契约是不够的,不以强力为后盾的信约永远是无效的,因为信约需要公共权力的保证,所以公共权力的诞生就水到渠成了。而国家同样也是由约定产生,在这个契约中,每个人都和每个人缔约,把国家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公共权力就是人们自然权利转让的结果。霍布斯指出,“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叫做国家,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权者。他把主权者看做“是一个人格”,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霍布斯将主权者看做是国家的本质,实际上是强调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在他看来,主权才是给予国家“整个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灵魂”。他关于主权者的看法表明,“主权者”、“人格”不过是公共权力的抽象体现,这一公共权力是人们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洛克则认为,社会契约是从自然社会转化到公民社会的唯一途径。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取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在这一契约中,人们把他们认为就一个共同体的目的来说必要的权利交由共同体的大多数人,自然权利构成了公共权力的来源。
自然权利经由社会契约转化为公共权力,霍布斯和洛克的逻辑形式上是一致的,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洛克是对前者的继承。但是,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与霍布斯是有区别的:第一,洛克认为不仅保全自己生命的权利,而且自由和财产权利都是人们在订立契约时不可放弃、不可转让的权利;第二,洛克认为人们交出的权利只是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而不是任意伤害他人的权利;第三,洛克认为被授予权力的人也是契约的参加者,必须受契约内容的限制,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委托行使他们的权力。根据契约的内容,洛克推断出,国家即政府权力的性质“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专断的”,而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他们交给国家的权力也只能是“自然法所给予他的那种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力”。而霍布斯却认为,臣民不仅应当在政治上服从主权者,在思想上也应当服从主权者,人民群众不应当有是非判断的自由,而且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必须由君主一人独揽。因此,我们认为,霍布斯得出的公共权力是绝对的、强大无比、不能分割的,洛克的公共权力则是有限的。前者偏好君主专制而否定民主制,而后者则认为民主政府才是正当的手段。
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关于公共权力起源的论证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把社会关系调整作为公共权力起源的基础。前者是拿一个预设的秩序对现行的社会进行框构,后者是从个人权利的保存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社会关系的调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同样得到重视,但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的起源图式是历史的,和逻辑形式上的起源图式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不论他们的差别有多大,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公共权力是以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为基本动因的。
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为公共权力演绎出了公共利益的目标,前者是城邦的幸福,而对于后者来说,一切公共的幸福都可以归因于个人的权利。但是公共权力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规范性质,它只是一种对社会的强制力量,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它对社会作出规定。所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人们对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间的关系状况的一种设定或评判,它是公众的主观认识里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对谁都有利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秩序。如果把公共利益理解为对大家都有利的社会关系的状况的话,那么私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为对某个群体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因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就构成了公共权力的两个方面。公共权力既可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可以为私人利益服务,公共利益只是对公共权力的规范性规定。所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是公共权力的规范要求和其特定群体占有之间的结果。
关于公共权力来源的契约让渡学说尽管是当时历史的现实政治和意识状况的理论反映,但其理论基础的唯心主义性质和概念的虚构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霍布斯、洛克的假设有很强的解说力和可操作性,但却缺乏科学的彻底性。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学说则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从而历史地、科学地说明了国家的本质和公共权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