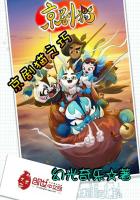堂路易一下子傻了眼。弗洛朗斯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刚才他不是明明见她上了火车,并让马泽鲁去盯着她吗?她就是往回赶,也不可能在晚上八点以前回到巴黎呀!
虽然他的头脑很乱,不过,他还是很快就想明白了:原来弗洛朗斯知道他们在跟踪自己,于是就把他们引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上了车,然后又从另一侧下了车,把善良的马泽鲁留在开动的列车上去监视空气。
可是突然一下,他觉得形势变得十分险恶。弗洛朗斯来这里要求继承遗产,而她本人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成了可怕的罪证。
堂路易顿时觉得怒火冲天,快步走到弗洛朗斯身边,一把揪住她的手臂,恨恨地厉声喝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德斯马利翁先生插在两人之间调解。可是堂路易没有松手,还在吼着:
“啊!总监先生,难道您没有发现弄错人了吗?我向您预告的,我们等待的那人绝不是她。那人仍然躲着,不肯露面。那人绝对不是弗洛朗斯·勒瓦瑟……”
“我对小姐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总监威严地说,“我的职责就是询问促使她来此的有关情况。我不会……”
他把姑娘解脱开来,让她坐下,自己也回到桌前坐下。很容易看出,姑娘的出席给他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可以说,姑娘一出场,堂路易的推理就得到了证实。一个有继承权的新人出场,对任何一个有逻辑的头脑来说,无可辩驳地意味着一个罪犯出场,他本人的到来就是犯罪的证据。堂路易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从此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警察总监。
弗洛朗斯轮番看着他们,似乎这一切对她来说,是最难解的谜。她美丽的黑眼睛保留了平常那种安详。她已换下了护士的大褂,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连衣裙,简简单单,没有装饰,衬托出她匀称的身材。她一如往常,文静而庄重。
德斯马利翁先生对她说:
“小姐,您有什么话,请说吧。”
她答道:
“总监先生,我没有什么话说。我奉命前来见您,我执行了这桩使命,却不清楚是什么用意。”
“您到底想说什么?不清楚你是什么用意?”
“总监先生,是这样的。我最敬重最信任的一个人让我把一些文件交给您,似乎它们与你们今日开会商议的问题有关。”
“柯斯莫·莫宁顿遗产的分配问题?”
“是的,总监先生。”
“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要是这个要求不在会议期间提出,就无效了?”
“我一拿到文件就赶来了。”
“为什么他不早一两小时交给您?”
“因为当时我不在那儿。我不得不匆匆离开我目前居住的房子。”
佩雷纳相信他的行动,通过使弗洛朗斯匆匆出逃,打乱了敌人的计划。
总监继续问道:
“所以,那个人为什么把这些证件交给您,您并不清楚?”
“是的,总监先生。”
“显然,您大概也不清楚,这些证件与您有关吧?”
“总监先生,它们与我无关。”
德斯马利翁先生微微一笑,两眼紧盯着弗洛朗斯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
“据您带来的那封信介绍,它们和您没有关系。确实,它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实,您是罗素家族的后人,所以,您有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的权利。”
“我?”
这一声惊呼是脱口而出的,既带有吃惊的意味,又有抗议的成分。
接着,她又坚持道:
“我,有权继承那笔遗产?没有,总监先生,绝对没有!我根本不认识莫宁顿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她十分激动地说着,也显得很坦率,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觉得真诚可信,可是警察总监怎么可能忘记堂路易的推理和预先对上门要求继承权的人的指控呢?
“把这些文件给我。”他说。
她从一只小包里取出一个蓝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了好些发黄的纸页,折叠处都磨毛了,好多处都撕了些口子。
此时此刻,房间里一片寂静。这些文件被总监先生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他又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又翻来复去地打量,最后拿着一柄放大镜检查了签名与图章,说:
“所有特征都表明它们是真的,图章是政府的。”
“那么,总监先生?”弗洛朗斯问,声音发颤……
“那么,小姐,我想说的是,您不清楚这件事,实在是让我难以相信。”
他转向公证人,说:
“总的来说,这些文件包括的意思,以及所能够证明的情况如下:加斯通·索弗朗,柯斯莫·莫宁顿的第四顺序继承人,如你们所知,有一个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名叫拉乌尔,住在阿根廷共和国。他哥哥在逝世之前,托付一位老乳母,把一个五岁小孩送回欧洲。这个小孩是他女儿,虽是私生女,却得到了承认。小孩的母亲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语教师的勒瓦瑟小姐。这是出生证,这是父亲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声明,这是老乳母写的证明,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三个大商人的旁证,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死亡证,这些文件都得到了确认,并盖了法国领事馆的公章。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除非发生了新的情况。因此,弗洛朗斯·勒瓦瑟就是拉乌尔·索弗朗的女儿,也就是加斯通·索弗朗的侄女。”
“加斯通·索弗朗的侄女……他的侄女……”弗洛朗斯结结巴巴道。
提起父亲他并不激动,因为她从未见过父亲。可是她与加斯通·索弗朗是那样亲密,有着那样近的亲缘,想起他她就哭了。
这眼泪是真诚的吗?还是她善于把角色演得可以以假乱真?这件事情她确实没有想到?还是她故意装出来的?
堂路易并不注意年轻姑娘,他只专心观察德斯马利翁先生的表情,想探出他这个将做出决定的人内心的想法。突然,他确信弗洛朗斯肯定会被抓起来,就像最残忍的罪犯被捉拿归案一样,便靠近年轻姑娘,喊了一声:
“弗洛朗斯。”
她抬起一双泪眼看着他,并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他缓缓地说:
“弗洛朗斯,我想提醒你,你得为自己辩护。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处在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地步。你必须清楚地明白,事件的发展情况,这件事已经把你逼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弗洛朗斯,这个案件本身的逻辑思维,已经导致总监先生确信,前来要求继承权的人显然就是谋杀莫宁顿遗产其他继承人的凶手。弗洛朗斯,进来要求的是你,而且你又确实是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
他发现弗洛朗斯从头到脚都在战抖,脸像死人一样惨白。她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作一个反对的手势。
他又说:
“这些指控是很明确的,难道你不反驳吗?”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然后宣布:
“我无可反驳。这一切都不可理解。你要我怎么反驳?这些事是那么难懂……!”
看着弗洛朗斯一副认命的样子,堂路易急得直哆嗦,期期艾艾地说:
“就这些?……你接受指控?……”
过了片刻,她小声说:
“我求你解释解释。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反驳,就是接受了指控,对吧?……”
“是的。”
“接受指控又会怎样?”
“就会被逮捕……坐牢……”
“坐牢!”
她美丽的脸庞因为惊恐扭曲都变了形,显得极为痛苦。对她来说,监牢代表着死亡,代表着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所遭受的折磨,意味着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未能幸免,而她也将遭受绝望、耻辱、死亡等等可怕的苦难……
她突然感到一阵虚弱,倒在地上,呻吟道:
“我好疲惫!……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我觉得黑暗已经把我吞没了……啊!我要是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该多好啊……”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德斯马利翁先生朝弗洛朗斯俯下身,专心致志地打量她。到后来,由于她不说话,他便伸手去抓铃铛,第三次摇铃。
堂路易一动不动,目光呆滞地看着弗洛朗斯。在他内心,爱慕和宽厚善良的本能与理智在激烈斗争。他的爱慕与宽厚使他相信弗洛朗斯,但是理智又迫使他设防。她究竟无辜还是有罪?他不清楚。一切都表明她有罪,可是,他为什么对她痴情不改呢?
韦贝尔带了他那帮人进来了,德斯马利翁先生指着弗洛朗斯与他交谈几句,他就走近姑娘。
“弗洛朗斯。”堂路易喊道。
她看了看堂路易,又看了看韦贝尔和他那帮手下,突然,她明白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吓得连连后退,身子摇了几摇,就头晕目眩,支持不住,倒在堂路易怀里。
“啊!救我!救我!求求你。”
一种信任体现在了她这个举动里,她的叫喊声里充满了苦恼,让人清楚地感到了受冤枉受委屈的惊愕与恐惧。忽然堂路易心里一亮,一股热流激励着他,心里顿时涌出不可遏制的坚信的浪潮,把他的怀疑、保留、犹豫、烦恼,统统淹没。他大叫道:
“总监先生,不要这样!有些事情还算不得数……”
他紧紧地抱着弗洛朗斯,恐怕有人把她夺走一样。他低下头,脸几乎贴着弗洛朗斯的脸。他感觉到姑娘在他手下,浑身战抖,是那样地柔弱,那样地惊慌失措,他就心疼得直颤。他热烈地对她说,声音小得只有她一人能听见:
“我爱你……我爱你……啊!弗洛朗斯,你要知道我的心事……我为什么难受,我是多么幸福!该有多好哇……啊!我爱你弗洛朗斯,我……”
总监打了个手势,韦贝尔走开了。德斯马利翁先生想亲眼看看这两个如此神秘的人物意外相遇是什么样子。
堂路易松开双臂,让年轻姑娘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然后,他面对面地把双手搭在她肩上,说:
“弗洛朗斯,现在你还不明白。我已经开始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看见自己几乎已经跌进让你害怕的黑暗中了。弗洛朗斯,听我说……这不是你干的,对吗?……是另一个躲在你身后的人干的,他站得比你高……是他指挥你,对吗?你甚至不清楚他要把你领到哪里去,是吧?”
“没有人指挥我干什么……您解释解释。”
“的确是,你不是一个人在过日子。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他让你干的,而且你觉得自己做的也是对的,但你不知道它的后果……你回答我……你完全是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吗?就没受任何人的影响?”
年轻姑娘似乎清醒了,脸上又恢复了一点平日的沉着。不过,堂路易的问题似乎让她感受很深。
“不是,没有,”她说,“没有任何人影响我……我可以肯定。”
他越来越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对,你不能肯定,你别说这话。有个人在支配你,你不知不觉。想想吧……你现在是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了……一笔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财产的继承人,我知道,我敢肯定。那么,这笔财产,回答我的问题,假如你不想得到这笔遗产,那又是谁想得到呢?……你变富了,是否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或者以为可以得到好处?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你是否与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你是他的朋友?未婚妻?”
她反感得一激灵。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说的这个人绝不可能……”
“啊!”他醋意大发,叫道,“我说的这个人……你承认了,他确实存在!啊!这个坏蛋……”
他转向德斯马利翁先生,他甚至都没试图克制自己的仇恨,脸因为仇恨抽搐着。
“总监先生,我们达到了目的。我知道,今夜就可以逮住那猛兽……最迟明天……总监先生,随着这些文件一起来的,小姐交给您的没署名的信,就是领导泰尔纳大道一家诊所的院长嬷嬷写的。只要立即去那家诊所调查,审问院长嬷嬷,让她与小姐对质,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罪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否则晚了猛兽会跑掉的。”
他的激动不可抑制,他的信心很强,使人无法抵拒,不得不接受。
德斯马利翁先生提出不同意见:
“小姐会告诉我们的……”
“她不会开口的,至少,她要等那个男人在她面前露出真面目才会开口。啊!总监先生,请您相信我,像前几次那样。我原来答应的事情不都做到了?总监先生,相信我,不用怀疑了。您想想那所有的罪名,压在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身上,叫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虽说是清白的,最后还是顶不住,死了。难道司法机关希望,像那两个人一样把弗洛朗斯也牺牲掉?况且我的意思并不是释放她,只是保护她的办法……这只是暂缓一两个钟头动手而已。让韦贝尔副局长负责看住她。让您的人同我们一起去。这些人,再增派一些人。因为去窝里捉那可恶的杀人犯,这些人并不多。”
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把韦贝尔拉到一边,交谈了几分钟。看那光景,德斯马利翁先生似乎不太同意堂路易的要求,不过大家听见韦贝尔说:
“总监先生,您不必担心,不会有危险的。”
德斯马利翁先生便让了步。
过了一会,堂路易·佩雷纳、弗洛朗斯、韦贝尔和两名侦探一起坐上一辆汽车。另一辆汽车坐满警察,跟在后面。
警察把疗养院团团包围住,韦贝尔又增加了一些预防措施,更是把疗养院围得水泄不通。
总监亲自来了。一位仆人把他领进门厅,接着又进了候诊室。院长立即接到传唤,赶了过来。总监当着堂路易、韦贝尔和弗洛朗斯的面,单刀直入,立即开始盘问:
“嬷嬷,”他说,“这封信是有人带到总署交给我的,向我报告了一些与一宗遗产有关的文件的情况。据我了解,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是您写的,不过笔迹是伪装的。是这样的吗?”
院长面容刚毅,神情果断,毫不为难地答道:
“确实是这样,总监先生。我有幸给您写了这封信,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让人念出我的名字。再说,重要的只是送交那些文件。不过,既然你们找到这儿来,我也准备回答您的问题。”
德斯马利翁先生盯着弗洛朗斯,又问:
“嬷嬷,我先问您,您认识这位小姐吗?”
“认识,总监先生。几年前弗洛朗斯在我们这儿当过六个月护士,我对她很满意,八天前,我又高兴地收下了她。我从报上得知她的事情,只劝她改个名字,疗养院的人员都换过了。所以,对她来说,这是个安全的避难所。”
“可既然您看了报,不会不知道对她的指控吧?”
“总监先生,这些指控是无中生有。凡是了解弗洛朗斯的人都这样认为。她是我遇到过的灵魂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之一。”
总监接着问道:
“嬷嬷,我们来说说那些文件,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昨天,总监先生,我在卧房里见到一个通知,说要交给我一些有关弗洛朗斯·勒瓦瑟小姐的文件……”
“其他人怎么会知道她在这家疗养院里工作?”德斯马利翁先生打断她的话。
“我不知道。只是有人通知我,文件将在今天上午寄到凡尔赛,写着我的名字,留在邮局待领。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在今天下午三点交给弗洛朗斯·勒瓦瑟,并让她立即送到警察总监手里。另外,他还让我转送一封信给马泽鲁队长。”
“给马泽鲁队长!真是奇怪。”
“那封信似乎和同一件事有关系。由于我觉得弗洛朗斯很不错,于是就派她去送那封信。今天早上我还去了凡尔赛。那人没说假话:文件都寄到了邮局。我回到院里,发现弗洛朗斯不在,她到四点钟左右才回来,我这才把文件交给她。”
“那封信是从哪个城市寄过来的?”
“是从巴黎寄过来的。信封上盖着尼耶大道邮政所的邮戳。那是离这儿最近的邮政所。”
“您在卧房里发现那些东西,不觉得奇怪?”
“当然觉得奇怪,总监先生。不过这件事本身的所有插曲更让我觉得奇怪。”
“可是……可是……”德斯马利翁先生看着弗洛朗斯苍白的面孔,又说,“不过,您注意到那通知是从这儿,从这个院里给您发出的,又正好与住在这院里的一个人有关,您难道不认为,这人……”
“弗洛朗斯趁我不知,潜入我房间,放了那份通知,对吧?”院长嬷嬷叫起来,“啊!总监先生,弗洛朗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
那年轻姑娘一声不吭,可是那张年轻的脸已经抽搐得变了形,一眼就能看出她的内心是多么地恐慌。
堂路易走近她,说:
“黑暗消失了,对吧,弗洛朗斯?这让你担惊受怕了。究竟是谁往院长嬷嬷房里放的信?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是谁在操纵整个阴谋,对吧?”
弗洛朗斯依旧不回答,于是总监吩咐韦贝尔:
“韦贝尔,你去这位小姐的房间看看。”
看到院长嬷嬷反对,他又说:
“我们必须弄清楚,小姐顽固地保持沉默到底是什么原因。”
弗洛朗斯给他们指路。韦贝尔正要走出门时,突然堂路易大声叫道:
“一定要小心啊,副局长!”
“小心,为什么?”
“我不清楚。”堂路易说,的确也说不出弗洛朗斯的举动为什么让他不安,“我不清楚……不过,我还是想提醒您。”
韦贝尔不理解地耸了耸肩,在院长嬷嬷的陪同下,一起上了一层楼。韦贝尔走到门厅又叫了两名侦探跟着他。弗洛朗斯走在前面,走过一条长长的两边都是房间的走廊,拐进一条极短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张门。
弗洛朗斯就住在这里。
门是向外开的。弗洛朗斯往外拉门,身子往后退,迫使韦贝尔也跟着往后退。弗洛朗斯趁机一个箭步跨进门,迅速地又把门关上,这一切完成的是那样地快,想扳住门,却扑了个空。
他气得直跺脚。
“臭女人!她会烧掉文件。”
又问院长嬷嬷:
“还有别的出口吗?”
“没有,先生。”
他使劲拉门,可里面锁上了,上了插销。于是他让一个侦探上前。那是个大汉,一拳就把门板打了个窟窿。
韦贝尔赶紧又上前,把手伸进那个洞里,扯开插销,开门进了房。
弗洛朗斯却不在里面了。
对面,一扇小窗户打开了,表明她是从那里逃走的。
“混蛋!”韦贝尔咆哮道,“她跑了!”
他马上跑到楼梯口,大声下令:
“看住所有的出口!不能让那个女人跑了!”
德斯马利翁先生闻声赶来,碰到副局长,听他说了几句,就来到弗洛朗斯的房间。打开的小窗朝向一个天井,大楼里一些房间就靠这个天井通风。一些管道从上而下。弗洛朗斯大概就是从管道上攀爬而下的。她这样的逃跑,可见她是多么地沉着冷静、性情倔强。
各个出口已经被警察牢牢地看守着。很多警察都涌到一楼和地下室搜索着洛朗斯的踪迹,不久,就得知她从天井又爬到她楼下的房间,那正是院长嬷嬷住的房间。她在那儿拿了一件修女袍罩在身上,借助这身伪装,她即使混在追捕者中间,大家也认不出来。
警察们又迅速地冲到外面,可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大众街区,又怎么能找得到她?况且夜幕已经降临。
总监的不满明显地挂在脸上,弗洛朗斯的逃跑打乱了堂路易的计划,他也十分沮丧,忍不住埋怨韦贝尔笨拙:
“副局长,我已经提醒您了,您得小心防备!看勒瓦瑟小姐那副神态,就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显然她认识罪犯,她想去和他会合,想去问个究竟,并且,谁知道呢?去救他,如果他说的理由让她信服的话,谁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可耻的强盗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院长嬷嬷再次被德斯马利翁先生询问时,德斯马利翁先生很快便得知,在八天前来疗养院避难之前,弗洛朗斯·勒瓦瑟在圣路易岛一家小公寓住过四十八小时。
尽管这线索不怎么重要,却还是不能忽视,警察总监对弗洛朗斯十分怀疑,认为抓获她至关重要,嘱咐韦贝尔和他手下立即循着这条线索前去查访。堂路易随同前往。
查访的情况果然证明了警察总监的安排是正确的。弗洛朗斯确实来过圣路易岛小公寓,并用化名订了房间。可是她刚到,就有个小家伙来到公寓办公室要见她,把她带走了。
韦贝尔他们进房间检查时,发现有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件修女袍。因此,肯定是她无疑。
晚上的时候,韦贝尔找到了那个看门女人的儿子。他问那孩子把弗洛朗斯领到哪儿去了,那孩子始终不告诉他。无论如何,他也不说那个托他做事的人。孩子的母亲求他,父亲搧他耳光,他都始终不说。
无论如何,可以判断,弗洛朗斯没有离开圣路易岛或者圣路易岛附近。
韦贝尔他们在这里守了一晚上,他把指挥部设在一家小酒店里。情况都集中报到这里,警察们也不时来这里听取吩咐。此外,他与警察总署也保持联系。
十点半钟,总监派一小队警察前来接受副局长的调遣。马泽鲁从鲁昂赶了回来,怀着对弗洛朗斯的满腹怨恨,和这队警察一起来了。
调查依然进行着。慢慢地,堂路易取得了领导权。可以这样说,韦贝尔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去敲这家门或者去问那个人。
到十一点,查访仍无结果。堂路易十分着急,心绪烦乱,一肚子的火。
不过,子夜刚过,一声尖厉的哨子把所有人马都召到岛东头的昂儒码头尽头。两个警察等在那里,好多路人都围在了那里。他们发现,出了小岛稍远一点的位置,在亨利四世码头,一座房子前停着一辆出租车,争吵声不断地从那个房子里传了出来,接着汽车就朝万塞纳方向开走不见了。
大家朝亨利四世码头跑去,很快找到了那座房子。底层有一道门直接通往人行道,出租车几分钟以前就是停在这门口的。从一楼出来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是被男的拖着走的。出租车门关上时,听到那男的在里面吩咐:
“司机,圣日耳曼大道。沿河马路……再走去凡尔赛的公路。”
不过看门女人提供的情况更准确。底层的房客她只见到一次,就是当天晚上,他用汇票付房租的时候,汇票上的签名是夏尔。房客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因此她觉得好奇。她的房间挨着他的套房,她就专心听他房间的动静。只听见男的在跟女的吵架。有一段时间,男的叫的声音特别大:“弗洛朗斯,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明天一早我就拿出所有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你要是不肯成为我的妻子,我就上船离开这里,我都作好了安排。”
过了一会儿,他又笑起来,大声说:
“弗洛朗斯,难道你是在怕什么?也许,你是怕我杀了你?我不会那样做的,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
看门的那个女人没有听到下面他们说的话。但是有这几句话,就足以证明堂路易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担心了。
堂路易抓着副局长的胳膊,说:
“赶紧去吧!我早就知道,那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是只老虎!他会杀死她的!”
五百米外停着两辆警察总署的汽车,他拽着韦贝尔就往那儿跑。马泽鲁还想反对:
“最好搜查一下每一个房间,采集痕迹……”
“嗨!”堂路易叫道,加快了速度,“房间、痕迹,再来搜也不迟……而他,他现在占了先……带走了弗洛朗斯……他会杀死她的……那是个圈套……我可以肯定……”
他就这样使出全身的力气,在夜里大声喊叫着,并且拖着两个人拼命走。
他们飞快地走进汽车,他们走近汽车。
“快发动汽车!”一看见汽车,他就吩咐司机,“我亲自开。”
他想登上司机座,可是韦贝把他推到后座,说:
“不用了……司机是熟手,开得比你快。”
堂路易、副局长和两名警察迅速地钻进车里。马泽鲁在司机旁边坐下。
“去凡尔赛的大路!”堂路易吩咐。
汽车开动了。他继续说: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你们要清楚这一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肯定会让司机开得飞快,但我们也不能逼得太近,不能让他知道后面有人在追他……啊!强盗,我们马上就能追上他了……快点,司机!可为什么我们要坐这么多人?副局长,你我两人就够了……嗨!马泽鲁,你下车吧,坐另一辆车……是啊,副局长,这很荒谬,对吧?”
他不说话了。因为他是坐在后座,夹在副局长和一个侦探之间,他便朝车门探起身子,喃喃道:
“啊!这个犯傻的人,这是开到哪了?都走错路了……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答案却只是一阵笑声。韦贝尔快乐得直跺脚。堂路易正要骂,又忍住了,费了好大的劲,想跳出汽车。可是被六只手按着,动弹不得。副局长揪着他的领口,两个警察按住他的手。汽车里面太狭小,没法挣扎,而且,他感到,一支手枪冷冰冰的,正顶着他的太阳穴。
“别动!”韦贝尔假装喝斥道,“再动我就毙了你。哈哈!你没想到有这一天吧……嗯!韦贝尔报仇的这一天!……”
看到佩雷纳还在挣扎,他又凶狠狠地说了一句:
“该你倒霉……我数三下……—……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出了什么事?”堂路易问。
“总监的命令,我刚收到的。”
“什么命令?”
“如果弗洛朗斯仍未抓到,就把你带到看守所。”
“你有逮捕证?”
“有。”
“然后?”
“然后就没事啦……卫生检疫所监狱……预审……”
“可是,见鬼,那老虎在这期间跑了……不,不,一定是脑子没开窍!……这些人多蠢啊!啊!他妈的!”
当他发现汽车开进看守所的院子时,他火冒三丈,猛一挺身,拿下了副局长的枪,一拳把一个警察打昏。
可是汽车门口拥上来十几个警察,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他明白这一点,怒火更盛。
“一群白痴!”他骂道。那些警察把他团团围住,推到书记室门口搜身。“一群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哪有你们这样办案的?罪犯伸手可及,你们却放走他,反把一个正派人抓起来……罪犯逃走了……罪犯要杀人……弗洛朗斯……弗洛朗斯……”
在灯光照耀下,在警察的挟持下,他显得极为无奈,又显得极有活力。
警察拖着堂路易向前走。他猛地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气,站直身子,甩开那些警察——他们就像一群猎狗一样死死缠着他,扑在奄奄一息但宁死不屈的野兽身上——又摆脱韦贝尔,招呼马泽鲁过来,他压着满腔怒火,镇定地吩咐道:
“马泽鲁,快去找总监!……请他给瓦朗格莱打电话……是的,总理……我想见总理……请向他通报。告诉他是我……是我,是那个骗了威廉二世的人……我的名字?他一听就知道。他要是记不起来了,就提醒他。这就是我的名字。”
他的话语像军队命令一样简洁断断续续的。他停顿了几秒钟,待呼吸更平缓以后,又说道:
“亚森·罗宾!让总监给他打电话,就说这个名字,就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亚森·罗宾有要事要面告总理。’让总监立即打电话。要是总理日后知道我的请求没有转达,准会十分生气的。去吧,马泽鲁,先办完这件事,然后再去查找罪犯的踪迹。”
看守所所长慢悠悠地打开了收审登记簿。
“所长先生,写上我的名字,亚森·罗宾。”堂路易道,“写上:亚森·罗宾。”
所长微微一笑,回答说:
“您要是让我写别人的名字,倒真是为难我了。可逮捕证上写的正好是这个名字:亚森·罗宾,又名堂路易·佩雷纳。”
堂路易听说这话,打了个寒噤。亚森·罗宾被捕了,他的处境要危险得多。
“啊!”他说,“看来他们决定……”
“我的上帝啊!就是这样的,”韦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决定打击亚森·罗宾就从正面来,因为斗牛就从牛角上动手。这要点气魄,嗯?好吧!我们还有很多办法等着你呢。”
堂路易站着不动,只是扭转头,叮嘱马泽鲁说:
“别忘了我的嘱咐,马泽鲁。”
对他的呼唤,马泽鲁竟不答腔,他又遭到了打击。
仔细一看,堂路易吓了一跳,因为马泽鲁也团团被人围着,整个人被人牢牢抓着。可怜的马泽鲁队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只是流泪。
韦贝尔更得意了。
“亚森·罗宾,你应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的同伴,如果不是监狱的牢友,至少是看守所的牢友。”
“啊!”堂路易挺起身子,“你们也要关押马泽鲁?”
“总监的命令,合乎手续的逮捕证。”
“什么罪名?”
“亚森·罗宾的同谋。”
“他,我的同谋!去你们的!他可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
“不错,是世上最诚实的人。可并不能禁止人家把写给你的信寄给他,也不能禁止他把信交给你。他知道你躲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证据。再说,还有好多事情,以后都会告诉你的,亚森·罗宾。”
堂路易无奈的低声叹道:
“可怜的马泽鲁!”
又大声说:
“别哭了,老伙计,不过就是住一夜罢了。是的,我们一块儿干,几个钟头之内连国王都要打倒。别哭了,我会给你找一个更美好、更尊贵、更赚钱的位置,你的事包在我身上。可能你会认为我考虑事情不周全,当然,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不过你是了解我的!所以,明天只要我出去了政府就会释放你,还要封你当上校,还要给你元帅的薪饷。别哭了,马泽鲁。”
然后,他转向韦贝尔,用长官发号施令,以知道无人敢争辩的口气对他说:
“先生,我刚才托付给马泽鲁的事,要请你帮我办。首先通知警察总监,说我有极重要的事,要面见总理,然后去凡尔赛,今天晚上就能查到那个老虎的踪迹。先生,我知道你的长处。这事就完全托付给你的热情与勤勉了。明天中午见吧。”
说罢,他仍然像一个发号施令的长官,让人领进牢房。
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五十分。那只老虎带着弗洛朗斯,像带着一件战利品,在大路上逃窜有五十分钟了。他觉得以后难以从老虎手上夺回弗洛朗斯了。
牢门关上,插上了销子。
堂路易心想:
“总监先生肯定会明天早上给瓦朗格莱打电话的。所以,等到我获释的时候,罪犯已经抢先占了八个钟头的时间。八个钟头呀……真倒霉!”
他又思索了一阵,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事可做只好等待的无奈神气。他扑倒在床上,喃喃道:
“睡吧,亚森·罗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