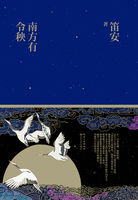伯爵原来在角落里喂他的鹦鹉,这时仍让那只鸟歇在肩上,他像平时那样礼貌周到,从那儿走上前给我们开门。劳娜和福斯科夫人先走出去。我刚要跟着她们往外走,还没绕过他身边,他就向我做了个手势,样子很古怪地跟我搭讪。
“是呀,”他仿佛正在冷静地答复我当时藏在心中尚未全部吐露的话,“哈尔科姆小姐,是出了什么事故。”
我刚要回答“我并没说这话”,那凶恶的鹦鹉便扇起那剪短了的翅膀,尖厉地叫喊了一声,吓得我的神经立刻紧张到了极点,只想快点离开那间屋子。
我在楼梯口赶上了劳娜。真没想到,福斯科伯爵刚才脱口道破的不只是我的心事,也是劳娜的心事,这时她几乎是重复了他的话。她也悄悄对我说,担心出了什么事故。
6月16日——今晚临睡前,我要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再写上几行。
珀西瓦尔爵士离开餐桌,到书房里去会见他的律师梅里曼先生,时间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离开自己的房间,准备到种植场去散步。但是我刚走到楼梯口,书房门开了,二位绅士走出来了。考虑到自己最好别在楼梯上出现,以免惊动了他们,我决定等他们穿过门厅后再下楼。这时他们的谈话虽然放低了声音,但是话说得相当清晰,所以还是传到了我耳朵里。
“您尽管放心,”我听见律师说,“珀西瓦尔爵士,这件事格莱德夫人是完全能做主的。”
我打算回自己屋子里去,等他们离开了再出去。但是一听见一个陌生人提到劳娜的名字,我就立刻停下了。应当说,这样偷听人家的话是不道德的,也是极不光彩的。然而,在我们所有妇女中,如果道德原则和自己的感情,以及由感情而产生的利害关系相抵触,又有谁肯去拿空洞的道德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呢?肯定没有。
我偷听了——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形,我还是要偷听——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甚至不惜把耳朵凑到钥匙洞口去听!
“手续您都明白了吗,珀西瓦尔爵士?”律师接着说,“要格莱德夫人当着一位或者两位证人,如果您想特别周到的话——签好了名,然后用手指点着签的字说:‘这是本人的签字,我愿履行契约。’如果能在一星期内办好这步手续,就可以十分顺利地做好安排,也就不必再为那件事担心啦。如果不能——”
“你说‘如果不能’又是什么意思?既然必须这样办,”珀西瓦尔气呼呼地问,“它就一定要这样办。我向你保证,梅里曼。”
“那敢情好,那敢情好,珀西瓦尔爵士——不过,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两种可能,我们做律师的喜欢大胆面对两种可能。万一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而不能做出那种安排,我想,是不是可以设法让对方接受三个月的期票。可是,那笔款子怎么办,如果期票到了期——”
“去他妈的期票!只有一个办法筹那笔款子,我再对你说一遍,用那个办法一定会筹到的。梅里曼别着急走呀,先喝一杯。”
“珀西瓦尔爵士,非常感谢,我要赶上这班火车,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一旦手续办齐,您要尽快让我知道好吗?您可别忘了我指出的要当心的事——”
“当然不会忘了。我的马夫这就送你去火车站。本杰明,赶车加把劲!要是梅里曼先生误了火车,你的饭碗就丢了。狗车在门口等着你。快上车吧。梅里曼坐稳了,如果你翻了车,相信魔鬼会救他的伙伴。”说完这几句告别词,男爵转身回到他的书房里了。
我就听到这些话,但就凭这几句话就让我感到不安了。所谓“出了什么事”,明明是严重的债务纠纷,而珀西瓦尔爵士必须依靠劳娜才能摆脱困境。一想到她被牵连到丈夫不可告人的麻烦事情里,我就十分忧愁。当然,事情的严重性也许被我夸大了,因为我对这些事情是外行,同时又不相信珀西瓦尔爵士,对他存有偏见。现在我已经不打算出去了,直奔劳娜屋子里,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了她。
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她听了我报告的坏消息,竟然神色自若。显然,有关她丈夫的性格以及他的债务纠纷,她所了解的情况要多于我迄今所猜到的。
“听到那个陌生人来看他,”她说,“又不肯留下姓名,我就害怕会有这种事。”
“那么,你猜想那个人是谁?”我问。
“他是珀西瓦尔的大债主,梅里曼先生今天来,”她回答,“就是为了他的事。”
“有关债务的事,你可有些了解?”
“不了解,详细情形我不知道。”
“不管是什么文件,劳娜,你在没看之前总不会签字吧?”
“当然不签,玛丽安。为了尽可能使咱们的日子过得舒适愉快,亲爱的,凡是能够帮助他的事,只要是诚实的,无害的,我都情愿做。但是,我不能盲目地去做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使咱们丢脸的事。这件事咱们暂时就别提了。既然你都戴上了帽子——要不,咱们到园地里去消磨这个下午好吗?”
离开了住房,我们朝最近的有树荫的地方走去。
穿过住房前面的林间空地,我们看到福斯科伯爵不避六月里午后的烈日,在草地上慢腾腾地来回踱步。他戴了一顶环有紫色缎带的阔边草帽。肥大的身体上披着一件蓝色罩衫、胸前绣着白色花饰,原来可能是腰部的地方束了一条大红宽皮带。本色布的裤子上,足踝以上的地方,绣了更多白色花饰,脚底下靸着一双摩洛哥皮拖鞋。他正在唱《塞维勒的理发师》中费加罗的那首名歌,只有意大利人的嗓子能唱得那么清脆圆润,他用手风琴自拉自唱,拉琴时得意忘形地举起了双臂,姿势优美地转动着脑袋,好像肥胖的圣塞茜莉亚穿了男人的衣服在跳化装舞。“费加罗quà!费加罗là!费加罗sù!费加罗giù!”伯爵一面唱一面展开双臂,得意扬扬地拉着手风琴,从手风琴的后面向我们鞠躬,那副轻盈优美的姿势活像二十岁的费加罗。
“劳娜,你得相信我,那个人对珀西瓦尔爵士的债务纠纷是知道底细的,”我说,这时我们在伯爵听不见的地方向他回礼。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她问。
“否则他怎么能知道梅里曼先生是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呢?”我回答。
“再有,我跟着你走出餐室的时候,他没等我发问就告诉我,说‘出了什么事故’。直觉告诉我,他知道的情况肯定比咱们多。”
“即使他知道得更多,你也别去向他打听。咱们不能把他当作自己人!”
“劳娜,我发现你好像特别恨他。他哪里得罪你了,会使你这样恨他呀?”
“没什么,玛丽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反而对我殷勤周到,有几次就是为了照顾我,他都没让珀西瓦尔爵士发脾气。我之所以恨他,也许是因为他比我更能支配我的丈夫吧。每次我们发生矛盾,都必须由他来从中调解,我想就是因为这点伤了我的自尊心吧。我只知道,我就是恨他。”
那一天中其余的时间就那样很平静地过去了。伯爵和我下棋。头两盘他客气地让我赢了,后来,一看出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先向我打了照呼,第三盘下了不到十分钟就把我将死了。整个晚上,珀西瓦尔爵士一次也没提到律师来访的事。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也许是由于那件事,也许是由于其他什么事,他的态度变得更好了。他对妻子异样地小心温存,连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福斯科夫人也注意到了,于是一本正经惊奇地瞅着他,对我们大家也彬彬有礼,温和可亲,又像他当初在利默里奇庄园受考验的时候那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我们只能猜测——但我相信福斯科伯爵心里是明白的。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整个晚上珀西瓦尔爵士不止一次地看着他的眼色行事。
6月17日——多事的一天。我多么不想这么说:它也是灾难的一天。
早餐时,珀西瓦尔爵士仍像昨天那样一句不提我们为之悬心的神秘“安排”(按照那位律师的说法)。但是一小时后,他忽然到客厅里来找伯爵,当时我和劳娜都戴好了帽子,正在那里等候福斯科夫人一同出去。
“我们还以为他这就要来呢。”我说。
“是这么一回事,我要福斯科和他夫人到书房里去一趟,”珀西瓦尔爵士一面紧张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接着说,“只是为了做一个形式,我要你也去一会儿,劳娜。”他仿佛这会儿才注意到我们都是散步的打扮,于是不再往下说了。
“你们刚回来吗?”他问,“还是正准备出去?”
“今儿早晨我们打算到湖边去,可是,”劳娜说,“如果你有别的事——”
“不,不,我的事可以等一等。”他急忙回答,“早餐或者午饭后都一样。你们一起到湖边去,对吗?这主意好。那咱们就逛一个上午——我也加入。”
难道他这样一反常态,乐意改变他的计划,是为了与人方便吗——即使你误解了他这番话的意思,你也不会误解了他那种神情。显然,为了缓和自己的紧张,他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推迟一下他所说的要在书房里做的“形式”。当我一想到这个必然的结论,心都冷了。
这时伯爵夫妇也来了。爵爷仍像平时那样穿着罩衫,戴着草帽,拿着那个花花绿绿的小宝塔笼子,那里面是他心爱的小白鼠,他一会儿对它们笑,一会儿对我们笑,笑得那么亲切和蔼,使你不由得对他发生好感。伯爵夫人则拿着丈夫的绣花烟叶口袋和许多纸,准备没完没了地卷烟卷儿。
“请诸位原谅,我要把我这小小一家人,”伯爵说,“把我这些可怜、可爱、与人无害的小小乖宝贝耗子也带着,和咱们一块儿出去散步。屋子附近有狗,我不能让狗欺负我可怜的白宝贝儿呀!啊,绝对不能!”他慈爱地向宝塔铁丝笼网里的小白宝贝儿咂嘴。
于是,我们一起离开住宅向湖边出发。
珀西瓦尔爵士一到了种植场上就和我们走散了。好像由于他好动的脾气,每逢这种时刻他总是离开他的伙伴,独自个儿忙着给自己砍一些手杖。仿佛单从随意地砍劈中就能获得一种极大的乐趣。他家里摆满了自己制的各种手杖,但没有一根会被用上两次,他只想制作更多的手杖。只要用过一次,他对它们的兴趣就消失了。
到了那个旧船库里,他又和我们会合在了一起。这里我要原原本本把大家坐定后进行的谈话记录下来。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因为自此之后我对福斯科伯爵在我思想感情上施加的影响就存了戒心,决定将来要尽可能予以抵抗。
船库很大,足够容纳我们所有的人,但是珀西瓦尔爵士仍旧在外边用他的小斧头削光新制的手杖。我们三个妇女很宽绰地坐在那张大长凳上。我仍像往常一样什么活也不做。我的一双手一向是并且将永远是跟男人的手一样笨拙。劳娜做她的活计,福斯科夫人开始卷她的烟卷儿。伯爵高高兴兴地搬过一个比他能坐的要小得多的凳子,试着在上面坐稳,背靠在棚的一边,于是棚板就被他压得咯吱咯吱响。
他把宝塔笼子放在膝上,放出了小老鼠,让它们又像平时那样在他身上乱爬。本来这些小动物的样子是非常天真可爱的,但是当我看到它们在人身上这样爬着,不知怎的我就会感到特别不舒服。这情景使我恐怖地想起那些在地牢中被这种动物公然肆无忌惮地折磨着的垂死的囚犯,于是在我神经上引起一种毛骨悚然的反应。
早晨刮着风,天上飘过朵朵浮云,空旷寂寥的湖水面上迅速地变幻着日照光影,景色显得倍加荒凉、阴森、忧郁。
“有人说那一带景色很美,我说那是贵人领地上的污点。”珀西瓦尔爵士用他没完全削好的手杖指向空阔的远方,“在我曾祖父时代,湖水一直淹到这儿。现在你们瞧瞧!所有的地方还不到四尺深,到处都成了泥坑和水塘,我的庄头儿(那个迷信的傻瓜),说他相信这片湖像黑海遭到了天罚。你觉得呢,福斯科?这里真像是一个杀人的好地方,你说对吗?”
“我的好珀西瓦尔,你英国人的精明头脑怎么会想出这种话来?”伯爵不以为然,“水这样浅,不能淹没尸体,到处又都是沙土,凶手会留下脚印。总而言之,我从未见过一个比这更不适合谋杀人的地方。”
“别胡扯啦!你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珀西瓦尔爵士说,一面恶狠狠地削他的手杖,“我指的是愁人的景色,凄凉的气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存心要了解,你是能够了解的;如果不存心了解,我也不必费神向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