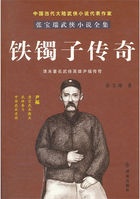清明节扫墓,不知道是何人何年代定下的规矩。今天是清明节,天阴沉着脸,飘浮着似有似无的雨丝儿,很符合扫墓人的心境。
阳冢林地里,鼓起了三个大坟墓,土是新土,坟是旧坟。是民兵连长大汇领着几个民兵连夜堆的。
按照爹的吩咐,二木在每个坟墓前都摆上了香火,供上了果盘三牲。
香烟缭绕,纸灰纷飞,阳开三在父母坟前行了三叩九拜大礼,然后扑到坟墓上哭得死去活来。在结发妻的坟前,他深深鞠了三个躬。
奇怪的是,跟着祭拜的二木没有哭,他看看身边的新兰,似乎也没有掉泪,就连儿子女儿也是干哭了几声。
这是怎么了?二木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娘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爹一走几十年,娘得拉巴小的,又得照顾老的,还要到地里干活挣工分。几十年她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早早的,四十几岁就花白了头发。生活上的压力还在其次,精神上的折磨更胜一筹。海外关系、叛逃台湾国民党的大老婆、反革命家属……无论是哪一条罪状,都能置她于死地,二木至今清楚地记得,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娘凌晨起床,扛起扫帚和四类分子一起去扫街。春种秋收,娘必须去地里义务看坡,少一粒粮食都不行,可怜二木的姐姐大菊,七岁就学会了做饭,十岁就下地干活挣工分。每当娘和姐姐下地干活,就把二木锁在院子里,二木也养成老实听话的性格,娘随手拿起一根干树枝,围着二木画一个圆圈儿,里边放上小板凳,一直到娘收工,二木决不会跨出圆圈半步。可是二木大了,总得上学,总不能老是关在圆圈里吧,这就免不了受人欺负,二木经常挨打,挨打的二木总是瞒着娘。但是娘从撕破的衣服上、打破的脸上总是能发现蛛丝马迹来。娘也不追问什么,只是默默地用针线把衣服补好,用舌头柔柔地舔着还汪着血的伤口,舔着舔着,泪就下来了,娘俩就哭成一团。
以往,每年清明节扫墓时,二木总要大哭一场的,可是今年没有哭的愿望,我这是咋着了?二木狠狠揉了揉发涩的眼睛。
他被爹那个巨大的许诺弄昏了头。
从前有个讨饭的叫花子,在路边看见了一条奄奄一息的小金鱼,就动了恻隐之心,就用讨饭碗在路边的水沟里舀了一碗水,把小金鱼放到碗里,小心翼翼地捧着碗,来到江边,将小金鱼放生。谁会想到这小金鱼竟是龙王的小公主,龙王像接贵宾一样把这个讨饭的接到龙宫,让虾宰相打开仓库的门,让讨饭的选一件宝物送给他。那宝库里金碧辉煌,大颗大颗的珍珠,闪闪发光。各种宝物应有尽有。哪一件都价值连城。讨饭的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挑什么好了。
如今,二木就是那个讨饭的。面对爹的许诺,他不知道该怎么弄好了。
爹是认真的。今儿一大早,爹就问他那件事想好了没有,爹说他向来都是说到做到,决不食言。还说一个男子汉做一件事不可以这样犹豫不决,拖泥带水。
二木实际上一夜未眠,和新兰激动了一夜,盘算了一夜,一张嘴,天上掉下来个大馒头,而且这馒头太大,让人无法下嘴。盖房子,甚至盖村长那样子的二层小楼?买农具,买一辆崭新的拖拉机?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这两样事儿,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你让他使劲想,也想不到比这更大的事来。二木知道自己的嘴笨,没想到脑子更笨,那就要这两件事其中之一吧,但是似乎又不甘心。新兰倒是想起了一招儿,她想买个粉碎机,这样一来粉碎猪饲料就不要出村了。但是她想了想就没有说出口,因为买粉碎机显然还比不上前边两件事。
两口子盘算了一夜没有合眼,也没商量出个子丑寅卯来,天明起床,眼睛都红红的,这件好事儿把他们折磨得好苦!二木有一次听村里老人拉呱儿,有一个经多见广的老人说,你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什么吧?毛主席床头上一个红糖罐,床尾一个白糖罐,他想喝白糖喝白糖,想喝红糖喝红糖,床底下还有一罐子咸鸭蛋呢!当时就让二木笑得肚子疼,没见过世面的父老乡亲啊,叫他使劲想也只能把幸福、享受想象到那么高,那么,自己又能比这位老人高明多少呢?二木甚至想打自己一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