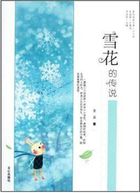从县委礼堂出来,已是华灯齐放的晚上了。其实算不上华灯,只是路两旁亮着几盏昏黄的灯泡而已。街道窄窄的,行人稀少,一副破败冷清的空寂模样。到底是小县城,根本无法跟省城相比。
县委办公室的牛主任告诉我们,县委招待所已为各位准备了晚餐。饭后报告团就住在那儿。明天一早,县里将派车送我们回离县城三十公里远的河西。
按说,牛主任应陪报告团吃顿饭的。不管怎样,报告团在省城出了大名,县委脸上也有光。这次我们从省城回来,也是县委一把手张书记亲自请来的,他热情得像一盆火:
“都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咱县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县里出了这么个好典型,是全县百万人民的骄傲,咱这里就应该墙里开花墙里墙外都香!”
不过这牛主任眼神有些怪怪的,飘忽不定,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只说有急事,不能奉陪,躲闪着就要走,被方大姑死死盯住了。
方大姑就站在牛主任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眼睛盯着眼睛,天很暗,看不清眼里的内容。最后,用狼狈逃窜形容牛主任一点也不为过。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姑的丈夫。
招待所的大餐厅亮着昏暗的灯光,没有暖气,更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一张大圆桌前团团坐定,最先尝到的是空寂和冷落。
饭菜终于在二十分钟以后上来了。一人一碗杂烩汤,温凉不展,碗底是白菜帮,上面放了几片油炸土豆片,用筷子一搅,散发出洗澡堂里一样的味道。馒头上了一筐,数量不小,这肯定是觉着我们乡下人饭量大,怕吃不饱。馒头是凉的,硬如石块,往桌上一放叭叭作响。这群混蛋!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农民。
秦支书脸色有些异常,他向聋老汉要了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聋老汉不吸,他这次捞的烟不少,有鼓鼓的一书包,包不离身地背着,像宝贝似的。
秦支书抽着烟,腮帮子古怪地哆嗦了几下,牙齿咯咯响。一支烟抽完,扔了烟头,用脚狠狠踩灭。很快,他恢复了常态,雨过天晴,眉眼立刻挂上了笑意。他让我叫来厨房里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有四十岁左右,胖得可爱,让人联想起“饿死的厨师八百斤”的民谣。
秦支书站起来,双手抱拳,客气地说:
“麻烦大师傅了。是我不对,忘了言语一声,我们已在别处吃过了。实在对不起,打扰了!”
说完,秦支书扭头就走。我们有些发懵,只好跟上他拔腿走人。
招待所对门是才开张不久的青年饭店。饭店大厅里灯火辉煌,看来生意不错,都晚上九点了,还在营业。大概这是县城最高档的饭店了。秦支书毫不犹豫地领我们直直走进饭店的雅座间,他当仁不让地坐了首席,叫来服务员,让他请饭店的经理来。
经理很快来了。这经理偌大的脑袋上约有五分之四寸草不长,极瘦,像长颈鹿,五十开外的年纪了,怎么也和青年二字沾不上边。
秦支书稳坐钓鱼台,连屁股也没欠一下,只是打了个手势,问:
“经理认识我们吗?”
“认识认识!报纸电视上见过多次了。再说,我刚才听过诸位的报告呢。贵客啊贵客,请都请不到呢!”
“我们想在您这儿吃顿饭,打扰了。”
“可以可以!我这就去安排,请问按什么标准?”
“拣最好的上。”秦支书眼角里飘出一个笑意,“不过,我没带现款,我明天让会计来结账可以吗?”
“当然可以!”经理喏喏退出。不一会儿,四凉四热外加两个大件走马灯似的上来了。秦支书还要了一瓶酒,和聋老汉对饮起来。我们则吃了个大汗淋漓。只是郑三娃吃得拘谨,边吃边嘟哝:这得花多少钱哟。方大姑干脆说:这一桌怎么也得五十块,得卖多少斤瓜干……
秦支书不理会这些意见,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当天晚上,我们到火车站广场租了一辆面包车,打道回府。出租车司机好痛快,认出我们是报告团的,竟然一分钱的车费也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