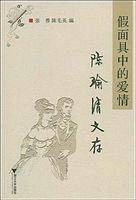胡同两侧竖起的高墙,因太阳和雨水的交替出现而有了浓绿的霉斑,它们的顶端压在山墙的瓦缝里,成条状倒挂下来,越往下越窄,分成了十几条绿丝带,还没有触到地面就停止了,那是久远年代里一场大雨的状貌,流泻的水柱骤然噤声,在墙上凝固。许多年后,我再次回来,站在山墙下,仰头望着流动的霉斑,我耳畔响起那场大雨经久不息的喧哗,其间还伴随着翻滚的雷声,隔着漫长的时空传过来。
胡同的衰老过程缓慢,每天黯淡一分,这一分是那么细小,我们用肉眼根本看不清。衰老的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们天天看到,便不觉其衰老,只有离开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才会忽然发现它的老态,中间的过程被轻易地跳过去了,这正如父母的衰老,也是突如其来,同样让人揪心。幸好胡同里还有些明亮的花,挨着院墙开放,硕大的花盘在风中晃动,古旧的院墙显得更加暗淡,还有的花甚至挡住了道路。花的主人,定是寂寞的人。这条胡同贯穿整个渔村,东侧是丛林般的山墙,午饭和晚饭后,有人坐在山墙下织网。织网人的样子已经记不清了,时间过去了太久,只记得他们坐在板凳上,网的一头挂在山墙的钉子上,另一头在他们手里,碧绿的一捆网,在竹梭的飞舞中变长。胡同另一侧是并排的平顶,院内的台阶能通到顶上,这是为晾晒鱼虾而搭建的,岛上人家以捕鱼为生,整天和鱼打交道。阳光充足的日子,胡同里弥漫着鱼虾的咸腥,各院子的主人赤着脚走在平顶房上,正如农人走在田垄间。他们俯下身子摆鱼,或者从竹筐里抖出一堆虾米,他们站在平顶房上,举起右手测定风向,就像站在自家的船上,飞起的檐角就是船头。有一家摆着几盆仙人球,西瓜大小的圆球上生着若干小球,它们一律顶着尖锐的刺,这家的孩子比我小几岁,那次在胡同里遇见他,他说仙人球摆在平房上是为了防止外人偷鱼,他还看到过仙人球上有血迹。我每天两次看见仙人球,就这样看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圆球上喷溅着尖瓣的白花,还有淡淡的清香,我这才知道,仙人球也是开花的,只不过开花的时候太少,我只当它不开花,却意外遇到了它开花的时候,平淡的日子变得稍异于往昔。如果早知道仙人球开花,我是没有耐心等待这么多年的。我踮着脚尖拔下一根刺,捏在手指尖观看,这刺是半透明的,掰到第三次才掰断,脆响过后,断茬处还淌着淡绿的汁液,我不明白的是,柔软的仙人球上怎会长出坚硬的刺,或许这些刺和我们的指甲是同类。胡同里走出一个裹着粉红头巾的妇女,泼出一盆带着鱼鳞的脏水,等我走到近前时,脏水已经渗进地里,鱼鳞却留下了,是些圆片的鲅鱼鳞,天色尚早,这家的女主人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中午的饭桌上必会有新鲜的鲅鱼,鱼头从盘子里探出来,布满尖牙的嘴微微开启,筷子拨开鱼身最外面的一层青皮,就像打开了绸缎的封套,里面露出耀眼的金黄色鱼肉,久违的光芒,照亮了一家老少的脸。
一天上午,我再次出现在离开多年的胡同里,环顾周围,胡同里一片黑暗,高大的山墙遮住了阳光,在另一侧投下尖角的影子,朝南打开的胡同口,阳光探进来几步,若到了中午,阳光照彻,整条胡同就会变得明亮无比。这个上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上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天的阳光侧身挤进了胡同口,在地上切成斜面,一个少年背着书包,第一次走出家门,胡同外的世界忽然呈现在眼前,他在胡同口稍微停了停,然后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