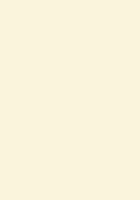那一夜我们在海湾里遇到了大风浪。在此之前,我们一次次提起网袖,又失望地放下,里面只有零星的几条薄得像刀片似的小鱼。显然,这样的情况是不常遇到的,我和父亲都疑惑地抬起头,在我们头顶上,群星像浮在海浪上,跳跃不止。它们纠结缠绕,直让人看得目眩,那应该是我见过的最为喧闹的星空了。
我们看到脖子酸疼,瘫坐在船板上,恰巧我们的身子同时晃了一下。起初我们以为是船板松动了,赶忙按住船舷,谁知船舷也在晃动,定睛细看时,整条船都在晃动,原来是起了飓风。
风贴着水面来了,就像一把笤帚,势必要扫除水面上一切异物。一个巨浪扑过来,一半撞在船身,我险些摔倒,另一半浪头全灌到船里。几个浪头过去后,我们脚下船板上的水已经过了脚踝,水面上漂着点点鱼鳞和海藻。船舷刚刚被浪头撞过,几股水柱肆无忌惮地倾泻下来,它们有飓风在后面撑腰,居然变得神气活现,也学着大浪的样子,横冲直撞。混乱中听到父亲在喊我的名字,他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船尾,手里拄着插网用的竹竿,勉强稳住身子,摇晃着朝我走过来。忽然一阵狂风夹着浪朝我们的小船卷过来,父亲和我都被掀翻了,冰凉的海水浸透了半边身子,前所未有的恐惧把我包围了,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停滞了,眼前闪现出一些纷杂的场景,它们近在眼前、纤毫毕现,仿佛触手可及,却又稍纵即逝,全然不见痕迹。
据老渔人们讲,在风暴中即将沉没的人,都会在一瞬间回忆起许多往事。我首先看到的是十岁那年的夏天,几个渔民往船上搬运桶装的淡水,其中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他从歪斜的水筒下回过头看了看我。他跳到船上,水桶早有人接了过去。他看我还蹲在岸边,在船上顺手捡了一只海星扔给我。他们的船从老鸹湾出去,从那以后一船人音信渺茫,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又看到中学同学艳红,为了供弟弟上学,她没上完初中就辍学回家,跟着本家的叔叔一起出海。现在,她已经被晒得黢黑,姣好的面容被无情的黑幕遮蔽了。她穿着肥大的皮裤,全身是泥点子,她手里还拎着一只洋铁桶,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滩涂上,身后扯出了一溜儿脚印,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霍地疼了。我还看到母亲坐在炕上,用剪刀把干鱼的尾巴剪掉……
父亲伸过竹竿来敲着我的手背,一霎间,十七八岁的水手、拎着洋铁桶的艳红、修剪干鱼的母亲,这些毫无秩序的影像纷纷遁走了。父亲示意我抓住竹竿,我照做了。
不对劲儿,有飓风时都是有雨有黑云,这天上怎么还有满天星?父亲冲我高喊着,他的声音随即被风浪淹没。我抬头看,漫天星斗发出耀眼的光芒,比刚才还要亮。
我们一定是在梦中,不然不会这样。父亲说。
鱼头砂。
我和父亲同时喊出了这三个字。有一种青鱼的头侧有两块指头肚大小的脆骨,宛如白砂,晶莹透亮,半岛人常把它塞到枕头里,据说能破噩梦。
每条船上都会有几块鱼头砂的。我们在没踝的水里摸索,还要顶住风浪,稳住身子。借着星光,我看见船坞子上有一点银白,正是鱼头砂。又一个浪拍过来,溅起的水柱冲得鱼头砂直往下滑,甚至沿着坞子滚落下来。我纵身跳出,劈手攥住鱼头砂,与此同时,我掉进海里,而鱼头砂细腻的肌理通过手掌传遍了全身,在手心断裂,我猛然惊醒,翻身坐起来,果然是个梦。
多年以后,每当我一个人在寂寞的旅途中,总会想起那个梦,想起那个晚上耀眼的星空——那是一个多么热烈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