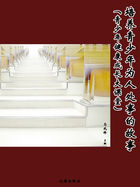去年暑假,做教师的妻子张罗要去旅游。我知道,她是看我下岗后总是憋在家里,十天半月也鼓捣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难受,想让我出去散散心。我俩游完北京,便乘车南下,直奔青灵山,因为妻子要看猴儿。
青灵山位于巴山蜀水之间,那里有许多迷人的传说。在这浮躁的社会里,虚幻的美总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灵的慰藉——这也许正是时下人们热衷旅游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是两天后才抵达旅游景区的。那天,天气很好。下车后,游客们沿着两侧开满野花的山路走出一身汗水,才来到登山口。虽然还没开始登山,但许多人已是气喘吁吁热汗涔涔了。
抬眼望去,一条石板小径一级一级地向山上蜿蜒开去,远远地隐没在云雾中。大多数游客都会在这拍几张照片,便算是“到此一游”了。也有坐“滑竿”上山的,这样既可以饱览山中美景,又不用吃登山的劳顿之苦。
妻子是不会同意只在山下拍几张照片了事的,更不会花钱坐“滑竿”。她此行的目的很明确:看猴儿。为了能跟猴子合影,临行前,她亲自下厨,盛情款待了我的老同学亮子,请亮子教我俩照相。经过培训,从没摸过相机的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光圈、快门,甚至连“景深”也略知一二了。学费就是一桌酒菜,亮子给我俩发的文凭是一台“傻瓜”照相机。说是发的,其实只是借用。亮子还嘱咐说,相机不怕用,怕的是磕碰……
看猴儿的美好愿望就要实现了,妻子把兴奋全写在脸上。不过,爬山对日渐发福的我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妻子却兴致勃勃,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实在爬不动时,我就让妻子给我照相,虽然我对照相没有一点儿兴趣。照相就得停下来,得摆姿势,找角度,这样,我就能喘息一会儿了。
遇到咪咪是在快爬到山顶的时候。咪咪是一只猴儿,鬼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妻子见了它就像老友重逢似的,张口就“咪咪咪咪”地叫开了。
妻子用一袋面包的代价,终于赢得咪咪的信任。在与猴子零距离接触的时候,妻子兴奋得面红耳赤。“快,快呀——照相。”妻子惊喜地喊我。
我连忙举起相机。妻子小心地抚摸着猴子的头,那只猴子抬眼望着她,等待她再次施舍。
“咔嚓”,妻子与猴子被定格下来。
“咪咪别动,”妻子轻轻地拍了拍猴子的头,向我摆手,“快,我也给你照一张。”
我急忙走上前,伸手将相机递过去。正在这时,咪咪一把抢去相机,转身便跑向山顶,并迅疾地爬到一棵高大的松树上。我想,亮子这台相机怕是要报销了。
望着树上的猴子,我默默地祈祷:亲爱的猴子,你可千万别撒手呀!
“好咪咪,还我的相机嘛!”妻子仍用叫猫的方法,“咪咪咪咪”地呼唤着。
山顶游人不多,有几位热心的游客围拢来,一边安慰我们,一边兴致勃勃地仰望树上拿着相机的猴子。
“看!猴子照相呢……”有人高声喊道。
我抬头看去,只见那只猴子正模仿人照相的动作,对着下面不停地揿动快门。
“早就听说这里的猴子爱抢东西……”
“前些天还抢过一个人的挎包呢!”
游人议论着。
我颓然地坐在草地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被汗水浸湿的衬衫紧贴着身体,难受极了。
“听说猴子不要别人的东西,一会儿会还给你的。”有人安慰妻子。
听了这话,我松了口气。果然,过了一会儿,那只猴子要下来了。我和妻子提醒游人向后退,并屏住呼吸向那只猴子行注目礼。
“咪咪,求你了,快把相机还给我们吧。”妻子低声恳求着。
猴子像是听懂了她的话,快速向地面靠近,刚一着地,便将相机往草地上一扔,蹦蹦跳跳向山下跑去。
照片扩印出来是回家后第三天的事。
看到青灵山的照片时,我和妻子惊呆了:有几张照片,上面没有妻子,也没有我——是那只猴子拍的。其中一张,以石阶为背景,画面主体是一对男女抬着“滑竿”,吃力地向上攀登着;躺椅上坐着一个胖男人,手里拿着扇子。远处,三三两两的游人点缀在石阶上。石阶两侧,绿树红花,静谧清幽。
还给亮子相机时,除了带给他一份像样的旅游纪念品外,我还带上了旅游时拍摄的全部照片。
亮子接过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好!这张拍得好!”亮子捧起那张以石阶为背景的照片说,“小角度俯拍,构图多好……”亮子啧啧称赞。
后来,这张照片被亮子放大并装在相框里,他还给这张照片取名为《上帝只眼》。再后来,这幅照片在全省摄影大赛中荣获金奖。再再后来,我就当上了市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了。
成了摄影家后,我就不再写稿子了。没事儿时,我就拿一台“傻瓜”相机到处转,得什么拍什么。别说,我拍的照片接二连三地在各级摄影大赛中获奖,省市报刊也经常刊登我的摄影作品。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再去一次青灵山,亲手拍一张《上帝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