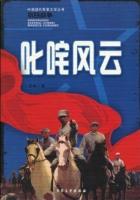鬼嫁
她一回头,看见的仍是那张可怕的残缺的脸,她刚要挣扎,却忽然发现地铁的车轮下有一个满身鲜血的女子,仔细一看,赫然是自己。
漆黑的深夜,没有一颗星星。
玫瑰颓然地坐在路边,脚边堆着好几个空啤酒罐,当她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泪终于掉落,为什么酒精仍然无法麻醉自己?本以为醉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掉那些痛,可她失败了。
泪眼朦胧中她仿佛看到一个黑影慢慢靠近自己,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小野猫,它的两只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诡异的幽光,她忽然听见有个嘶哑低沉的声音在对她说:“死了吧,死了就再没有痛苦,死……”
她心中出现一个念头,她要凄惨地死,让他一辈子后悔!想到这里她的脸上浮出一丝凄凉而得意的微笑。
公路上偶尔有飞速驰去的汽车,小野猫在她脚边来回地踱着步,发着幽光的眼睛盯着玫瑰,似乎在催促着她。
她看着飞驰而过的汽车,忽然有点迟疑,本能让她产生了一种对死的恐惧感,她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这时她忽然看到那只黑色的小野猫慢慢飘浮起来,绿色的眼睛中瞳孔已变成一条黑线,而野猫的脸上似乎有了表情:是狞笑!“不!不……”玫瑰尖叫出声,她想逃跑,但丝毫不能动弹,绝望和恐惧让玫瑰美丽的脸扭曲了。一道刺眼的光由远而近,一辆货车从公路上驶来,越来越近,玫瑰忽然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她向前推去,她跌倒在公路中间。眼看车就要撞过来,货车司机大概看到了她,但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司机慌乱中拼命转方向盘想要避开她,于是车猛地向路边转去,但路的下面是很陡的山坡。一声巨响,汽车掉落坡底,货车司机从车中甩出来,头撞在一块大石上,顿时头盖碎裂,脑浆四溅。玫瑰也在巨大的惊恐中昏迷过去,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漆黑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眼睛逐渐适应黑暗,玫瑰才看清房间里有很多床,一张张的床上都躺着人,一动不动。这是哪里,为什么这么冷?她忽然看到一张床上的人没有盖被单,仔细一看,顿时吓得魂都丢了,她这辈子都没看到过如此悚人的画面:那个人的头骨有一半没有了,脑子里的东西都暴露在外,满脸的血凝固成暗红色,一只眼睛突出眼眶,像是随时要掉出来。玫瑰忽然意识到这是太平间,是专门存放尸体的地方,她浑身剧烈地颤抖,拔腿要跑,可这时那具可怕的尸体却坐了起来,冲着她微笑,朝她伸出一只满是血的手,手掌里是一只染了血的木雕的青蛙。“啊……啊……”玫瑰在自己惊恐的尖叫声中睁开眼睛,原来这只是一场可怕的梦。玫瑰环顾四周,好像是在医院,到底是怎么回事,玫瑰只觉得头痛欲裂,一名护士快步走进来,对玫瑰骂道:“你叫什么叫!还有脸叫!在马路上醉酒,把人家害死,那个死了的司机可是家里的独子……”没等护士说完,玫瑰一脸的惊恐,她跳下床,夺门而出,原来一切都是真的!玫瑰飞奔着回到家里,她坐在床上,无法抑制自己剧烈的颤抖。她发觉四周又是一片死静,她害怕想起那个可怕的梦境。她打开电视,谁知电视里正播放记者采访昨晚车祸死者的家属,那个老太太哭诉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啊!害死我儿子的人一定不得好死!我可怜的儿啊……还没结婚呢……”只见那个老太太一脸怨毒的面对镜头说:“昨晚我儿子报梦给我,他说他找到凶手了,而且他还要在下面结婚了……”玫瑰猛地关掉电视。她觉得房间里冷得彻骨,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玫瑰想起来,这是梦中闻到的太平间的味道!忽然衣橱的门自动打开,一套鲜红的结婚礼服慢慢地飞出来,她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嫁给我吧……”她在极度的恐怖中看到那张可怕的脸在阴影中出现,手中捧着染了血的木雕青蛙……玫瑰奋力地跳起身打开门逃了出去。到哪去呢?去朋友家吧。她上了一趟地铁,大概是因为太晚了的缘故,车里的人异常的少,她靠在门边,心脏仍在狂跳,她觉得累极了,闭上眼睛。“少奶奶,请更衣吧!”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少奶奶?好奇怪的称呼,玫瑰睁开眼,只见一个小女孩正手捧一件鲜红的衣服站在她面前,小女孩苍白的脸上诡异地笑着,竟像极了那种纸扎的童女,玫瑰大吃一惊,一抬眼,才发现自己正被入团团围住,不,那不能够称之为“人”,他们有的少了四肢,有的脸已开始腐烂,都对她诡异地笑着。
“不……”玫瑰闭着眼捂住耳朵尖叫,这时,地铁的门忽然开了,她飞快的跨出去,但竟然不在站台上,忽然一道光照过来,伴着隆隆的声音,玫瑰才发现自己身处地铁的隧道里,而一辆地铁已快速驶向她,随后一声巨响,玫瑰睁开眼,地铁已刹住了,忽然有人拉住她的手:“跟我走吧。”她一回头,仍是那张可怕的残缺的脸,她刚要挣扎,却忽然发现地铁的车轮下有一个满身鲜血的女子,仔细一看,赫然是自己。
(九穗天)
魂胎
我是不相信什么鬼的,但是我却不得不相信微微的话,因为她有医院的报告单,而且我知道她绝对没有必要去编一个这样的谎言来作践自己,可是这一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我陪微微去医院,她说最近胃不太好,连闻到香味都有想吐的冲动。我和她特地请了一个上午的假。
我时常在想,什么时候我和微微这么好,我们在同一个公司,但在不同部门。况且我是主管,她只是一个职员。
似乎是半年前的事了……半年前,微微的丈夫莆清意外车祸身亡。他们共住的房子是租的,微微突然间没了立足的地方。公司知道我单身一人住一套公寓,好心人将她的情况告诉了我,征求我的意见看是否能让她租个房间。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同时我说可以不交房租。一个星期后,微微搬了进来。
我和微微正在候诊室,窗外下着雨。微微一脸惆怅,没有说话。
我不住地安慰她说,没事的。很快医生出来了,我们赶忙迎了上去。
“医生,我的胃没事吧?”微微问。
“没事,你的胃很正常。”
我和微微同时松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过,你的尿液的检查报告显示,你怀孕了,小姐,要注意休息。”医生温柔地吩咐。
“什么?我怀孕?”微微顿时愣住,半晌不能反应过来。
我急了,抢过话头,“医生,你一定是搞错了吧,这不可能,她丈夫去世了,我和她住在一起,生活起居、上班,都在一起,她干过什么事我都知道,她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丈夫的事!”
“我敢肯定没有错,而且我可以确定她怀孕的日子是上个月的6—7日。”医生很冷静地回答。
微微摇摇头说,“那肯定错了,因为上个月6~7日我例假,她——”微微指了我,“她可以证明。”
“是的,我记得。微微有严重的痛经状况,每个月都是我帮她料理生活。上个月特别厉害,后来我给她买了止痛片。我想得起来这些。”
无奈之下我劝微微回家,顺便在外头买了便当。回到家,微微什么都没吃,靠在沙发上就是不开口。我知道她无奈,也委屈。我端着便当在她身边坐下说,“机器检验也有出错的时候,别想了,我相信你,吃吧,下午还有工作呢。”
微微点了点头,低头扒了几口。可是,不久她又剧烈地呕吐起来。
晚饭的时候,微微仍然没有摆脱呕吐的状况。这似乎就是怀孕的征兆。但是我仍相信是她的胃有毛病。可是,我难免还是会担心微微是真的怀孕了。于是我拉她到我房间里坐着。
“微微,你听我说,你真的……干过什么吗?”
微微摇了摇头,“芬姐,你要相信我。”
可是你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啊,告诉我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相信我,我替你保守秘密,真的,说吧。我尽力让她相信我。
“可是我真的没有!”
或许她真的没有,我责怪我的多心。但是我发现她这个月没来例假。我想起上个月公司来了个日本的客户,特别喜欢微微,还请过她吃饭,会不会是……就这样,半个月过去,这个话题我们没有再提。一天晚上,我的房门突然被敲响,“芬姐,是我。”传来微微颤抖的声音。
“进来吧,有什么事?”
“我……我想说,怀孕的事是……是真的。”声音很弱。
“是谁的?微微,我理解你这半年来并不好过,我并不反对你的私生活,但是,如果你当我是朋友,是你的好大姐,你应该把事情告诉我才是。”
“我说了你会相信吗?你肯信吗?”微微用试探的语气说。
“我怎么会不信你呢?笑话!说吧。”我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
“孩子是……是莆清的。”微微战战兢兢地说。
“什么?莆清?微微,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以瞒的啊,莆清不是半年前就……这怎么可能啊?”
“芬姐,真的,我真的没骗你!”微微突然哭了起来。“我知道我说都说不清,但是真的是莆清的啊!你记不记得上个月6号……”
“上个月6号不是你例假吗?那天晚上你疼得哭了,我给你吃了止痛片。”我记得。
“后来,我……”
“我回房看你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啊,搂着莆清的照片,脸上挂着眼泪。”
“是的。”微微面无表情地应着。“我梦见了莆清了,”微微接着说,“因为以前在我最痛苦的时候,莆清从来就没有离开,即使是在他很忙的时候,他都是以最快的时间内赶来。他走了之后,我真的好想他,没有他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
“可是这些和你那些事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我梦见莆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在梦里,我和他……做了……”
“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啊,又能证明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可理喻。
“可是……可是……我醒来的时候,我全身赤裸,衣服都丢在了地板上,而且我身上有他指甲的掐痕,脖子还有他轻轻咬过的牙印啊!我又羞又愧但是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你要知道,我不可能咬到自己的脖子的,而且,我从不留指甲,身上的指甲痕哪里来的,莆清他才有留啊!”
“这些都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只是在梦里你不知道而已!”我说,我有些生气她的胡言乱语,我相信她是无可奈何才急得说胡话的。
“芬姐,你听我说完好不好,”微微哭得更厉害,芬姐,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他在梦里告诉我他以后都会来陪我,不会让我痛苦。
而且真的,在以后的每天夜晚,他都会准时到我的梦里,和我……每次醒来我都是全身赤裸,身上同样留下了掐痕。每天早晨我都非常失落……可是有一天,我梦见他陪我去妇产科检查身体。莆清高兴地告诉我他终于给了我份大礼,弥补结婚两年的空缺……
“微微,”我叹了口气,“你听芬姐说一句,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梦来解释一切,我对你的诉说很不满意,但是你又无法和我说清。”
“芬姐,其实,在去医院之前,我去了……”
“什么地方?”
“我其实看过一次中医,那个老医生说是……是喜脉!芬姐,中医有可能看错,但是医院不可能同时看错吧,如果真的这么巧,那再检查一次也好。昨天,我悄悄地到了医院里做了B超,通过了仪器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胎儿的心跳,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医生和我一起看屏幕的时候,却怎么也看不到有孩子的样子。”
“医生连连说奇怪。可是我明白是怎么会事!”
我突然无话可说,我也只好问,“微微,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真的好怕。如果我把孩子生下来,那这个B超看不到样子的孩子生下来会什么样子的?如果我想拿掉它,医生怎么拿掉这个看不到却一天天在我肚子里长大的孩子呢?”微微哭着。
“没事的,微微。”我安慰着她,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她说些什么,我的头脑也很混乱。我安顿她去睡觉,自己却失眠了。
我是不相信什么鬼的,但是我却不得不相信微微的话,因为她有医院的报告单,而且我知道她绝对没有必要去编一个这样的谎言来作践自己。可是这一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我似乎要去寻找懂得这方面的人来帮忙。
我利用了到郊区厂房查货的机会探访了年过7旬的姨婆。姨婆是这里小村所谓的“神婆子”,也似乎就是从事别人所说的巫婆之类的事情。一阵客气的问候之后,我道出了我的来意,告诉了她微微的事。
姨婆的神情凝重起来,她一言不发。我急了:“姨婆,求求你,我知道,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帮帮忙。”
姨婆摇了摇头,“我无能为力,你去求别人好了。”
“姨婆,我妈在世的时候,和您也是好姐妹,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常来看你,但是,我和哥哥也常寄钱过来啊!姨婆,我求求你啦!”
我整个人猛地跪下。
姨婆苦笑了一阵,“孩子,起来吧!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那么姨婆我也就尽力,但是,那是你同事的,恕我不理。”
我还是没有起来。
沉默良久后,姨婆开了口,“孩子,你知道吗?她的丈夫做了那些事情,虽说是难以舍弃自己的爱妻,但却是违背天理的事!人鬼殊途,怎么能干这种事情!你同事肚子里的是个魂胎,虽然看不到的却能感觉到。我是有能力拿掉,只是……”
“只是什么?只要我可以帮的,我都尽力做好!”我仍然没有站起来。
“呵呵,恐怕你帮不了,我拿掉这个魂胎,那个男的就会魂飞魄散,做这场法事的人阳寿会减4年。”
“姨婆!早知道这样子,我也不会来找你了!”我哭了。
“傻孩子,看我这么把年纪了,吃也吃够,活也活够,虽没有享受过什么荣华富贵,但过得还算安宁,我看,你就带我到你的住处去吧。”
我千谢万谢。
我把姨婆介绍给微微,当然我没有说出法事作成之后,姨婆折寿,莆清将魂飞魄散的后果。微微很感激我为她所做的,她同意了姨婆所做的安排。这天,她早早睡了。半夜我和姨婆分明地听到了她的梦呓:“莆清,这孩子咱不能要!”
“求求你别再求我,我也很爱你,但是,人鬼殊途,即使我怀了你的孩子,也无法生下来抚养!”
“不行!不……不……”
翌日,只见微微坐在床边,脸色苍白。我递了杯牛奶,她推开了。微微转过身对我说,芬姐,“你瞒了我些什么事?”
“没有啊。”我只能装笑。
“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想伤害了姨婆和莆清。”
“你……”我顿时呆住,“你都知道了?”
“昨晚,莆清在梦里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说他对不起我,他只是舍不得我一个人在世上,所以晚上才偷偷地和我幽会,谁知他的冲动又让我……他很后悔,他本想保留这个魂胎,但是如果我把它生下来,我就会死去,而那个孩子也不能在世间存活,只能去阴间。他不想害我,也不想连累其他人……”微微哭着扑到我怀里。
我无奈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微微,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姨婆也答应了,你还年轻,将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去做,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打住。”
微微点了点头,一切就那样在晚上开始了……姨婆点燃了蜡烛,布好八卦阵。她让微微坐在阵中,口里念念有词。慢慢的,她上了香,祈求一切平安……忽然,蜡烛灭了,不知从哪飘来一张白纸,姨婆把它点燃,烧成灰,放到杯子里,加了水,让微微喝下去……这些都是我在门缝里看到的,我不能进去。而后不久我却听到了一声尖叫,是微微的!难道是……我不敢再看,同时,我又听到一声非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我昏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醒来已经是早晨。我起身走动,姨婆在一旁静静地坐着,微微嘴边带有鲜血,衣服上也都是血迹。
“微微!你没事吧?醒醒!”我扑过去。
“她没事的,醒来就好了。”姨婆轻轻地说。
“谢谢姨婆!”我感激地说道。我扶着她到我房间休息。
一周之后,姨婆回到乡下。我花了我两年的积蓄为她在那里建了一套房子。尔后,我陪微微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没有怀孕。
一年之后,一向硬朗的姨婆悄然地在睡眠中去世……
(无鸣)
鬼魂的日记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动了一下滤色片……我看到制片人的怀里根本不是那一只可爱的小猫,而是一具恐怖狰狞的僵尸!
盛夏来了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实习摄像。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环境:亲切的总监,热情的栏目制片人,当然,还有美丽的女主持。
主持人叫阿琳,大概20岁左右,她肌肤似雪,明眸如电,有一头瀑布般的飘逸长发和一双诱人的美腿。
她对我这个新来的小伙子也很有好感,总是弟弟长弟弟短的问这问那。
我的心酥酥痒痒的,现在和以前的学校枯燥生活相比,真像是一下子走进了天堂。
我哪知道,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栏目马上就要直播了,导播让我在直播室调一下摄像机的角度。
我调整的时候,发现光圈好像小了点,刚摸索到调整的位置(说实在的,我对这台机器真的不熟),不小心动了滤色片一下。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发生了:取景器里的主持人忽然变了一个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面庞浮肿,青面獠牙,两只眼睛只有死鱼般的眼白,她狠狠地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