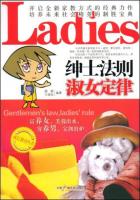王皓
苦难的童年
我祖籍四川屏山县平夷司,是王元寿的后代。明、清以及民国几百年,王家于斯生息繁衍,到我祖父那一代,就已发展到几百户了。几百年来,族内两极分化,也较明显,有的人家“锦衣玉食”,有的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祖父临终,给他的三个儿子留下51亩租后的田地和绥江县城文昌街的一所住房。三子均分,我父亲分得数亩租后的田地和文昌街的两间住房。我们的家即生活于此。
母亲生育我们弟兄姐妹八人,生计十分困难。迫不得已父亲到四川当兵寻找出路,家庭就靠母亲一个支持。后来同胞相继夭折,最后只剩下四姐、五哥和我,五哥过继堂伯父家,母女三人苦熬着,一心指望父亲的好消息。哪知我三岁那年,却盼来了父亲病逝成都的噩耗,真是雪上加霜,家境尤为困难了。1925年,五哥不堪堂伯父的嫌弃,愤而跑去屏山亲戚家,意外地参加了徐容邦领导的农民暴动。事败不敢回家,流落宜宾。母亲只有这根“传宗”的独苗,怎不着急,乃请人去宜宾寻找。五哥倒是回来了,可是找他的人却暴死途中。为了“赔命价”,母亲又将所余田地全部当出,彻底破产了。母亲、姐姐熬更守夜做针线活计,卖点“针头线脑”,勉强撑持一家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我们被歧视、被欺凌,连同院的嫡亲叔婶也把我们不当人看待,经常借故指桑骂槐地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母亲为了“息事宁人”,为了谋求生计,只能笑骂由他了。
1928年,五哥在屏山读高小,因发动罢课、反对校方被斥退,再次去宜宾而后浪迹四方了,绥江社会上风传他是共产党。1934年他突然回到绥江,随即领导了“反选运动”,其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但暗自佩服他的能耐、敢和地霸斗争,替我们也出了口气。
一家人正庆幸团圆,反动派却酝酿着逮捕他的阴谋,于是哥哥再度被迫出走。
艰苦的求学历程
母亲虽一字不识,但却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她和姐姐省吃俭用,千方百计都要供我上学。有次家里揭不开锅了,剩下两个铜板,也给我买包谷带到学校去吃。由于穿着破烂,在学校常被一些同学歧视,班上丢了什么,首先怀疑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几个地主的小姐掉了砚台,商量要用水碗中竖筷子的迷信式嫁祸于我,幸好有正义感的同学们及时报告了校长,将她们训斥了一顿,才平息了风波。
1935年夏末,我高小毕业。为了减轻母亲和姐姐的负担,秋初,我毅然考入了我县的简办师范科,希望一年毕业后,当上一名小学老师,缓解家庭的困境。可是事与愿违,1936年夏毕业,却以我是“赤色分子”王家广的胞妹而不予分配。我很愤慨,同时也感到步入绝境,曾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五哥从成都来信劝勉,并寄来名著。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它给我很大的启迪和力量,暗下决心要摒弃黑暗追求光明,请求母亲送我去宜宾走亲戚,借以打听能否找到什么工作或免费学校。适逢一护士学校招生,但要交30块银圆的学费。天哪!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家。过了不久,我的一位堂姐从自贡归来,她丈夫是警官,沿途有人“保镖”,我同堂姐一道去了自贡,住在她家,寻找就业机会。可是这位堂姐居心不良,劝我嫁给他们的勤务兵,我趁其不备,在一个黄昏时候坐一辆黄包车逃走,而后搭乘货车,辗转到了成都。到成都后,暂住在五哥朋友(同乡)刘嬉的家里,由他帮助找到了五哥另一好友于宏黎(中共地下党员)。于告诉我,五哥是共产党嫌疑被关进松潘监狱,我有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倒。于安慰我说,你哥的事,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好在他只是嫌疑,反动派并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他叫我留在成都读书,学费由他设法筹措。1937年秋,我考入私立成都中学,抗战爆发后,成都是大后方重镇,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天天跑警报,读书也不安宁,反动派还要搞摩擦,更使人义愤填膺。由于吕家搬家,我是三易其居才读完一个学期。于宏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有限的收入,还要供养母亲,在那“米珠薪桂”的年月,就无力再负担我的费用了。他决定送我到崇庆县廖佶然家去,廖是五哥在松潘的同事,曾到成都中学看过我。
1938年1月我去崇庆,黄昏时才到县城,夜宿一大娘的家。第二天到了廖家,廖已返任。他的妻子很贤惠,有个老母,三个女儿,一家人热情接待了我,我很感动,也很自觉,打起精神抢做家务活计,廖家嫂子愈发喜欢我了,对我说:“你去县城读书,学费我会设法解决。”2月,我入崇庆县女中11班就读,我爱看报,每天课余后都要在报栏前站上较长时间,这本来是常事,但却引来一些人的注意,我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我的信也被偷拆过。这时五哥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丢了“乌纱”(保安中队长),住在成都。他经常给我写信和寄书报,有封信上他鼓励我说:“我们的母亲孤独一人(四姐出嫁已去世),在家困难,但别忘了我们中国还有千百万困难的母亲……”启发我振奋精神,为了解救中国千百万受难的母亲,力求上进!
我们的班主任任叫罗雨时,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长,有次他宣布要在学校发展三青团,要我们积极参加,并决定那个星期天去郊外照相,我便于星期六晚课后躲到雷家去了,星期日晚才返校,因此他经常嫉恨我。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一家大恶霸地主被土匪抢劫后杀完了全家……全校大哗,议论纷纷。我在周记写道:“总是作恶多端,方才有此下场。”他的批语是:“你有偏见。”其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暗中监视而已。紧接着,学校来了一个女童子军教官(实际是个女特务),加强了对学生的管制,还搞了一次突击性大搜查,把学生隔离到别处,由他(她)们翻箱倒柜地检查,但扑了个空,一无所获(我们早有准备,把信件、书籍转移出去了)。过后罗雨时找我个别谈话,叮咛我“你不要误入歧途”,同时把蒋介石的言论集给我阅读,想从思想上征服我。我为了想在此校念完初中,也只好虚与委蛇。把所谓言论集的序言死记硬背下来,他又一次找我谈话时,我便照本宣科,侃侃而谈,不但蒙混过了关,还受到他的表扬。
1939年秋季开学,罗雨时要我找保人,否则不准入学,我找同学周汝棋(她哥哥在县党部工作)作保,五哥寄来的信和书都全部寄存在她家。开学后形势愈来愈紧张,蒋介石逐步重施反共伎俩,风言风语充斥全校。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危险,很有被抓的可能,乃借此请她去成都请教五哥。五哥说:“走为上策,立即行动。”我赶回学校匆忙收拾行李,坐黄包车离校,刚出大门,罗雨时嗅到气味追来了,但当时已晚,仅在车后大叫:“王家华,不要误入歧途,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催车夫快跑,才算脱了险境。到成都,寄住在一个地下党员毛念出的家里,五哥托人送我进了一个声称为战地服务的护士学校学习,定期三个月结束分配工作,校址在法国领事馆,主持人是一个留法博士。快满三个月时,同学们听到分配后的月工资只有两元,与招生简章上说的八元大相径庭,于是七嘴八舌地吵开了。我鼓励大家说:“我们写抗议信,要他照章办事,如果不行,我们就趁早回家。由我喊口令。”大家都同意。由我执笔写成抗议书,塞进主持人的宿舍。第二天上课,他果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于是我喊口令:“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大家一哄而散,等他叫来警察,连人影都找不到了。因此我又再次沦于失学、失业的状态。事后,五哥将我寄居在一个姓王的老太婆家里。正值天寒地冻,我衣服单薄,时不时地又交不上伙食费,真是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当时地下党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靠组织或个人设法找职业作掩护搞工作,同时亦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盘踞在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随时都防备中央军把他吃掉。当时日寇的魔爪伸到山西的边沿,蒋介石对他也是虎视眈眈,于是他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然这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成效。党中央派了若干党的干部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同志全面负责。帮助阎锡山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培训革命知识青年,充实抗日力量。1939年夏天,民大派到成都招生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陈恕平。成都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通知已暴露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投考民大(其时蒋介石又挥舞屠刀,镇压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借以保存革命力量。直到12月份,这支民大新生组成的行军队伍才组织就绪,按军事编制成一个大队,共152人。大队长陈恕平,副大队长王家广,政治指导员王怀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下设四个中队,一、二、三中队是男生,四中队是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更名王皓。我学过几天护士,被编入卫生组,每天背上药包行军,每到宿营地,少不了给感冒了的发阿司匹林片,给脚上打了泡的抹碘酒、红药水。
我们是12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1940年2月才到延安,行军57天,行程3000里,在这57天3000里的行程中历尽了艰辛。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了许多“三青团招待所”。如果发现了单个或少数几个青年往西北走,就被抓去关押,然后押送回大后方。我们是阎锡山民大的新生,是到二战区去的,他们当然不敢阻拦,但暗中刁难,不是不解决住地,就是不给粮食。我们有时就挨着饿,露天宿营。吸取了教训后,大队抽人组成了“前沿队”,提前出发,先到宿营地买菜、担水、煮饭……保证队伍吃饱、睡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途中,大队领导反复强调,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不要掉队,要互相照顾,否则就有被抓去的危险。大家都遵守得很好,没有发生意外。1939年底,传来了山西发生新旧军冲突事件的消息,这都是阎锡山发出的反共反人民的信号。因此,队伍到了咸阳,即由大队领导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党中央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传达指示:“将全部人员带到延安。”同时一再叮咛:“要周密考虑,防备阎锡山搞突然袭击。”阎锡山果然也是消息灵通,我们在咸阳休息,他就派了一名姓牛的中队长带了三个武装随员来“迎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来监视我们的。
大队领导经过周密计划,与陕甘宁边区驻山西陕西交界处的边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到茶房镇后将改道去延安,请他们接应,并秘密地向队伍传达这命令:“到茶房镇不解脖,不睡觉,听候指示。”并补充说:“如果有行动,对有病同志要搀扶着走,坚决不丢下一个人。”同时给每个人发了一块银圆,万一被打散了,就作路费往延安方向走,会有人接应我们的。当天到茶房镇已近黄昏,吃了饭天黑了,队伍集合好,队长派人把牛队长请来,由指导员王怀安讲话:“同志们,阎锡山反共反人民,与新军打起来了,这是真的。现在那里(指山西)变得黑暗了,反动了,我们是到黑暗的反动的地方去呢,还是到革命的、光明的延安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喊:“到光明的延安去!”这吼声震动了天,震惊了寒冬的黑夜!我顿时热血沸腾,真是喜极欲狂了。大队长(他是从山西派来招生的)当即表态:“我跟同志们一道走。”当时牛队长气急败坏,呆若木鸡。王怀安指导员命令队伍向左转,152人成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边区甘泉进发。只听到“嚓嚓”的脚步声、“跟上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声,几乎是小跑前进。经常通宵急行军,60纵队黎明前到达。我们在甘泉休息了三天后继续前进。在中途三十里铺的地方,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前来迎接、慰问我们。在一个草坪上,他给我们讲话:“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带来了党中央的慰问……”,大家听了,兴奋得跳了起来,把帽子往天空抛,唱着,跳着……许久未能平静。1940年2月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我们安排在北门外新华书店礼堂住宿。团中央冯文彬同志、大作家丁玲大姐……还有许多负责同志陆续不绝来看望我们,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欢乐中。
中央组织部将我们这批人分别安排到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校学习深造,女同志大都进了女大,我被分到七班。女大是毛主席提议为中央妇委主办的,是我国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骨干的学校。校长是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还经常听毛主席讲话,周总理、叶剑英、范长江、艾思奇等也不时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我们的课堂是露天,膝盖是桌子,十个人睡一个大炕,垫的是谷草,点的是油灯,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土布做的棉衣、单衣。每人每月发边币1.5元,精打细算使用,交党费、买牙膏牙刷、卫生纸,还要凑点钱共同到青年食堂去吃“三不沾”(是面粉掺鸡蛋、糖,用油炸成的,是当时最高级的食品)。大家还风趣地把小米饭锅巴戏称为“列宁饼干”。最伤脑筋的是鞋子最易穿烂,又不会做,后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即拾别人丢了的鞋,只要底子好,把它洗干净,剪掉破帮,再缝上同块布条,拴上线索就变成了凉鞋,穿起来还挺合适,非常高兴,还给其他同志传经送宝!
在班上,指导员和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融洽、亲切、互相关心,照顾得像一家人似的温暖幸福。在领导的教育辅导下,我进步较快,2月进校,5月入党候补期三个月,8月转正,且成为班上的宣传骨干。生活虽然苦一点,但大家精神很愉快,每天课余饭后或节假日,同学们都去附近桃园玩、聊天、打扑克。四川人聚在一起就摆大后方的小吃,说得津津有味,我们叫它为“精神会餐”。学校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每周六都要组织友谊舞会或组织球类比赛。1940年三八节,每人发了一套灰土布做的、领口袖口嵌上白布边的“列宁装”,穿着它参加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在操场跳集体舞。场面壮观,同学们高兴极了,会完后又是一顿会餐,真是说不尽的愉快、欢乐!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女大同学特别关心。有一次,我们正在露天的场中吃午饭,毛主席来了,亲切地问我们吃得饱吗,菜够不够?一星期吃几次肉,生活习惯吗?啊,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高兴极了,饭也顾不上吃,抢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把毛主席围在中间,跳跳蹦蹦,轰动了起来,齐声向他问好。此情此景,而今记忆犹新。1941年11月,我们从女大毕业了。这温暖的幸福祥和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姐妹们就要分别了,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难过,彼此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被分配到甘肃陇东分区庆阳小学教书。踏上了革命征途,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了祖国母亲,为了人民大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指挥,风风雨雨,奔波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