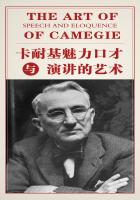严昭
我的朋友,要我告诉您些什么呢?陕北的风?陕北的雪?陕北战士们抗战的炽热?不,这些别人写得已很多,而且写得比我好。我只把在延安女大学习的一些使我至今还欣喜与感动的琐事写出来,作为永远的追忆及纪念。
我总是记得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多亏有了党的教导和指引,使我懂得了人活着应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瑰丽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我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向漫长而多难的人生迈进,是中国女子大学给我点燃起第一把启蒙之火,它使我在人生的白纸上画出第一幅壮丽的图画与憧憬。这火一直照亮了我的一生,无论是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斗争中,在抗美援朝的生死搏斗;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押在秦城苦狱中……这盏启明灯始终指引着我前进。我个人的能力虽不大,但我总是抱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铸成的”信念,“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虽则自己只有萤火之明,但终不甘自灭!
那些过去的岁月,逝去已50多年了,有些事已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冲淡了,有些事亦已尘封,记忆模糊了。唯有几件事仍使我记忆犹新,好似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回忆在年纪大点的人来说是件嗜好,甚至是个安慰,但回首往事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有时它使你快乐,同时也难免有些悲伤。
黑夜行军演习
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形势吃紧,学校备战的空气亦趋紧张。领导上早已说要进行一次夜行军演习,是突击性的演习,目的是要检阅一下学生的参战能力,要背上背包,要打好绑腿,如同真的行军一样。大家的心便揪紧了,天天练习如何更快更好地把被子及随用什物包好,练习如何打好绑腿,要不松又不紧,紧了走路会痛,松了又要脱落……总之,备战的气氛鼓得足足的。可是等了一星期仍无动静,大家的情绪也松了下来。不想有天半夜,突然警哨长鸣,我们一骨碌从炕上爬起,在黑暗中,立即把被子打成长方形,系上背带,打好绑腿,规定时间是十分钟。动作快的同学已提前到窑外集合。我因绑腿打得太紧,第二次重打耽误了时间,这时窑洞外又响起了预备哨,说明时间还有一分钟,我赶忙在炕下找自己的草鞋,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是七个人睡一条土炕,草鞋挨得很近,不知是谁在忙乱中将我的鞋穿走了,没奈何,我在黑暗中沿炕乱摸,找了两只草鞋,立即穿了,唉,却是一只大、一只小的鞋子!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胡乱穿上,刚穿好,集合哨又响了,说明要出发了。窑洞外黑糊糊的,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手拉着手摸索着从山上下来,走出门不多久,我便觉得不得劲了,大的那只鞋还能拖拉着勉强走路,讨厌的是那只小鞋,勒我的脚跟不说,而且头又太小,被挤的前趾如同裹足妇女一般,我一边走一边心里骂:“哪个坏蛋穿了我的鞋?”我们手拉手在黑暗中摸着行军,天上连小星星也没有,可能是个阴天,星星躲进了云层。行军中是不允许讲话的,我熬着左脚的剧痛,拖着右脚一步一挨地默默前进,好在天黑,行军的速度不快,如要跑步,我便只好打赤脚了。好不容易走了一个钟点模样,前边传来低声的口信:“队伍暂时休息三分钟。”呀,老天,总算解放了!我私下庆幸。在坐下歇息的片刻,灵机一动,将头上的帽子包裹了我受伤的左脚,幸好有一条裤腰带是备用的,我将腰带扎好脚,扎得结结实实的。队伍又前进了,我这才知道已经行军八里地,现在是往回走了。一路上我如释重负地跟着大家往返校的路上走,路上的小石子硌着我的脚,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总算比来时的痛少多了!
又走了一小时多,摸索着上了山,自己的小窑洞快到了!我不由得欢笑起来,这时东方已晨光熹微,有点看得清了!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的窑洞前小平台,夜行军胜利了,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可是当队长在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了我。
“你的帽子那儿去了?”
我哭丧着脸说:“那不是!”我抬起了左脚给她看。
这时天已经有亮了,她看着我的脚,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大声说:
“这不成了一个伤兵吗!咋搞的?”
“可不是吗?不信你看,我的左脚后跟受了伤,还在流血呢!”“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我的鞋穿错了……”我委屈得快哭出来了。
这时班长又气又发笑地说:
“还好,你总算坚持下来了,但那只小鞋在哪儿,该不是你丢在路上了吧?”
“要是丢在路上,便犯了错误了,因为我们是夜行军,不能让人知道,如遇到战争,敌人可以凭这只鞋来跟踪追击我们!”指导员补充着。
“看,这不是那只害人的小鞋吗!”我从背包上解下那只鞋递给指导员。同时补充说:“我倒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想留着这只鞋,向鞋主人算这笔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一个同窑住的笑得更凶,原来她是我们的小组长贺曦,那是个河南女孩子,比我大一岁,她边笑边埋怨说:
“我也是受苦的呢!我穿了你的大鞋也走得不得劲!”
“还有一个罪魁祸首,我这只大鞋是谁的?”我发怒地质问。藏在靠边的老余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是我的!我急着要抢第一个整装好,穿错了你的鞋,我也没得便宜,你的小鞋夹得我生痛,只是没有受伤就是了!”又引得哄堂大笑。
一场夜行军便在欢笑声中结束了。
从此后,我同贺曦结成了好朋友,她已是个党员,成天乐呵呵地又说又笑,她经常给我讲革命的故事,讲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斗争,又介绍我看许多苏联的革命小说。就在这一年,她成为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我入了党。
事隔几十年,我俩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一次,我偶然在同学口中听到一个噩耗:贺曦同志在60年代生肺病逝世了!
我为此黯然神伤了好久!
亲爱的战友,但愿你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的欢乐!
中秋节的舞会
那是1939年10月中旬中秋节的前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们五个女孩子,都只有十七八岁,正是花季的年龄,年轻得如同早春的一片新绿,红红的脸庞如同含苞的玫瑰。吃夜饭的时候,白凌从合作社买来一包红辣椒粉,悄悄地对我和葛瑜说:
“你俩有兴趣去鲁艺参加中秋节舞会吗?”
“太远了,去桥儿沟要走二十几里路,一来回便是几十里,星期一还要上课呢!”我回答。葛瑜说:“怕什么?来,多吃点饭好赶路。”说着她从白凌手里抢过辣椒粉往我和她的碗里倒了些。又说:“我包你误不了上课……你老是怕这怕那的!”
于是白凌、葛瑜、莉莎和我(还有一个谁我记不起了)急急忙忙吃完了饭,换上了一身装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装(这是我们出门时最时髦的衣服),大家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到那里没有多余的缸子喝水。”是葛瑜在喊。我们又回来拿上茶缸子,这才上路。
“今天我们同谁联欢?”莉莎问。
“同鲁艺音乐系的同志联欢,所以乐队也不用请了,是他们自己奏乐。”白凌说着催我们快走。
我们一行五人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地出了校门。一路上又说又笑,乐不可支。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走了几十里路,只见一轮金黄色的圆月从东山升起,那么大,那么亮,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月亮!天蓝得如同一泓静静的海水,四周的山色黑黝黝的,使月亮更显得明媚和庄严,它神圣地沐浴着我们,这幽蓝幽蓝的天宇,这黄澄澄巨大的皓月,周围如此静谧,空气又清新得如滤过的一般。这如同梦幻似的仙境,它净化了我,它照耀着我,以致在我以后踽踽独行于暴风雨的岁月中鼓舞着我,这轮壮丽的皓月永远闪亮在我的心中!每念及它,便使我感悟到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使我徒增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为什么月亮那么黄黄的?”不知是谁打破了宁静。“因为四周的山、四周的地都是黄沙及黄土,所以月亮的皓光映照得黄澄澄的了。”我心里想。
同志们亦都为这美景惊愕了,沉默片刻之后,于是大家便纵情唱起歌来。
“沙漠像黄的海浪,奔到无边的远方,蒙古包下起伏的海岛,骆驼在那里荡漾。月光下有人烧着野火,悠扬悲壮地歌唱: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原是自由幸福家乡!”
歌声使我们忘却了疲劳,走过飞机场后不久,我们便到了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早有人看见了我们的来到,估计他们是在等待来客,只听得有人在喊:“来了!来了!”
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那便是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
窑洞前的小凳上摆了花生、红枣、小米糖等好吃的东西,我们取下茶缸边喝水边吃东西,这时主人时乐濛、刘炽、陈紫等同志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宿舍。
嘿,多新鲜!亏他们想得出来的,居然自制了土沙发,在窑洞里离地二尺的地方,挖一个可坐两人的平面,再在上方挖一半圆形的凹面,作为土沙发的靠背,平台上垫着花棉垫子,又美观又舒适。
“你们真聪明,怎么想出这好办法来的?”说得男孩子们腼腆地笑了。
他们又用酸枣刺当做图钉,将列宁像、乐谱等都平平正正地别在窑洞的墙壁上。所有这些布置,使我们大开了眼界,使人感到,人的意志的伟大,只要人的灵性不泯灭,无论处在何等艰难的境地,亦会创造出温馨、创造出辉煌来的。
此时已月到中天,天宇如洗,舞会开始了。主人们轮流吹奏着美妙的乐章,一对对翩翩起舞的少男少女们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如幻如仙,如醉如痴,跳啊!跳啊!忘却了时间,甚至忘却了自身!直到皓月西斜,估计已到三点左右了,还是带队的白凌提醒了大家:
“时间不早了,再跳最后三个舞!”
众人又尽兴地跳起来,最后一个是以扭大秧歌作为舞会的收场。
我们又重新走在返校的路上。这是次日的凌晨,但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口气赶了20余里,东方已现出鱼肚白,月亮已暗淡得同晨曦混而为一了,远远地看到了学校的土围墙。我们也不上山去,便在延水边洗脸漱口,洗尽了路上的尘埃,便坐在延水边上石头上歇息,不多久,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但这场中秋节的通宵舞会也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站岗
1940年,女大实行了站岗,每天在学校大门口由学生轮流值班站岗。
那是秋日的一个礼拜天,恰逢我去执勤站岗,我照例全副武装并手执长枪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上午十点多了,我面对着前边的延河水直愣愣地站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同志……”我蓦地吃了一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转身一瞧,两个人都呆住了,原来来人是我的母亲,她今日特意赶了十几里地从南门外来看我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女同志站岗,会不会让我进去看你……”母亲惊喜地说。
“啊,妈妈,您怎么来了呀!”我冰冷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真不巧,今日是我值班,值班是不让会客的,如没有什么事,你就回去吧。”
“不妨事的,我只要看看你就行了。”
母亲在自然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她是个“改组脚”(改小脚、放大脚),走十几里路也真不容易。可是我“左”得出奇,抱定了共产党员不能假公济私的死理,不与妈妈多讲话,并一个劲儿地催她快回去。门房的老丁同志看不下去了,他从屋里拿出一条长板凳让母亲坐下,并埋怨我说:“你也要让老人家歇歇气再走呀!”
母亲坐下来与老丁闲聊了起来。
母亲说:“现在的孩子不讲情理,动不动就用大道理压人。”
“你老不要生气,孩子还小,太幼稚,不懂情理。”老丁安慰着母亲。
母亲被冷落在一边没有动,坐了五分钟,她便告辞回去了,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只煮熟的鸡蛋,硬塞到我的口袋里,走出才三步,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老二,小心着凉,早晚还是穿上毛衣。”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知道了,您快走吧!”
看着母亲小脚伶仃往回走,看着她逐渐缩小的背影,我无动于衷,还深自得意我做到了因公忘私!
过了若干年,我读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叙述他父亲去火车站送他远行,他见老父蹒跚的背影,产生了父与子的一段悱恻的亲情!我被猛然一击,立即联想起母亲来回30里看我的情景!这引起了我内心无限的歉疚与自责!为什么不多与母亲讲几句使她开心的话呢?为什么一个劲儿催她快走?唉,我这个忘恩负义的忤逆之子,怎么对得起她老人家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首批冲击,可怜的母亲亦被株连殃及……后来我们获平反,母亲亦被昭雪,我去南京看母亲受难的地方,已被拆为平地,一排排丁香在凄风苦雨中摇曳,似乎在向我诉说着母亲的苦难!
母亲死了!我已经不会凄然哭泣,只觉得在这大千世界里我是一个孤人了!过去的一切过错,甚至罪过,我再去向谁忏悔、向谁求得宽恕呢?呀,母亲饶恕我吧!饶恕您可怜的女儿吧!
一个人的悲喜,充其量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片微茫的浪花。在我生命之烛燃尽之前,我祈望着人间不要再有悲剧,我希望看到理想之树绽开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