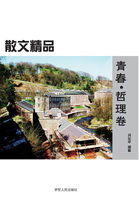谢励
我原籍江苏溧阳县,随父客居太原。父亲是资本家,经商于天津太原间。为人老实寡言,不大过问政治。但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除白天上学外,还请有家庭教师,一个教太极拳,一个夜里课读。母亲出身于溧阳县城职员家庭,粗通文字,但精明能干,为人仁慈善良,勤俭朴实,性格开朗,富有同情心。这些对我的成长都影响很大。我12岁考入太原女师,在班里年纪最小,学习名列前茅。性格好动,爱打球,是篮、排球校队队长。在校被誉为“品学皆优”。
我虽生活优越,但深受进步小说、电影、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十分厌恶父辈间吃喝玩乐、打麻将、抽大烟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对劳苦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深恨旧社会的腐败、黑暗和不公,十分向往光明幸福的新社会。
当时,女师革命气氛很浓,在罢课、撵教员、闹学潮下,聘来一些进步老师,如狄景襄、李一清、李义山等,都是地下党员。给我颇多启迪,教育我要敢于抗争。当时,我校的训育主任是个30多岁的老处女,听说她是复兴社的,属蒋介石的中统。她对同学监管甚严,常蹑手蹑脚偷进教室、宿舍,监视学生思想、行为,引起同学极大反感。我们在同学中酝酿必须撵走她,于是采取揭露、起外号、写匿名信等方法,终于使她威信扫地,灰溜溜地被撵走了,使我初尝斗争胜利的喜悦。
同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武秀英,1934年她参加反帝大同盟后,搞进步活动,数次被捕,与山西大学进步学生乔峰山结婚后,她家更成为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进步青年,他们偷偷地传述着红军沿云、贵、川胜利前进的消息;红军东渡后,一往无敌、神速前进的英勇气概,更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介绍反帝大同盟、抗日武装自卫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薄一波组建牺盟会等进步组织的情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统治,特别是复兴社、蓝衣社、CC派、公道团等特务组织的卑劣伎俩。谈论抗日形势,议论山西政局,分析谁进步,谁反动,明辨是非。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复杂的政局内幕,知道了共产党、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增强了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这时,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何梅协定割让冀东22县后,日寇更加步步进逼,平津岌岌可危。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烈火影响全国;太原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抗日。1936年春红军东渡,北上抗日,一路挺进,直逼太原。城内进步青年和学生积极响应。阎锡山竭力维持他的反动统治:一方面拼命抗击红军的进攻;一方面在城里滥肆搜捕,严厉镇压。先后将穆政等20余名进步青年杀害,枭首示众,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仅推翻旧社会要依靠共产党,当前抗日也要依靠共产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我苦闷而彷徨!
1936年夏,在武秀英家遇到一位年约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看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武告诉我,他名智良俊,新从北平政法大学毕业回来,是省政府的公务员,他就是我要找的共产党员。经武介绍,智对我数次单独考察后,于1936年10月介绍我入党。随即由他介绍我去参加工作。
他领我骑车到城北一座青砖房的四合院,院子较宽大,北房住着主人及夫人、儿女,东西厢房好像住着亲友及佣人,人来人往,很热闹。门洞里停放一辆黄色车,主人每天乘它上下班,智良俊带我进到南房,屋内很空,好像从没有人住。智把我介绍给这家主人胡西安。胡身材矮胖,40来岁,穿着西服,很气派。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省政府的公务员,大约是处长或科长。他布置我每周星期三下午去,用药水抄写情报。抄好后,时间不长,写的字就都看不见了。然后装入信封。信大都是发往延安。至于如何显影、如何发信,我就不知道了。此外,他经常给我看油印的小册子,如党中央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八一宣言》等文件以及西安事变的内幕等,他使我从中接受党的教育,了解党内的情况。并再三叮嘱我:“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每当我骑车去他家时,心情高兴极了,感到有了为党工作的机会,精神有了寄托,过去苦闷彷徨的心情一扫而光。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们都是为党做重要情报工作,他家就是我党华北局的情报机关。
1937年暮春,智良俊把我调出,介绍到地方工作。叫我身穿白衫黑裙,手拿一卷杂志,去杏花岭接头。并告诉对方的特征。这时约是4月份,太原已是绿树成荫,花满枝头。杏花岭里树影婆娑,阳光煦煦,鸟语花香,十分安静。我按时到达后,渺无人迹。心中正忐忑不安、疑虑重重时,忽见女师同学温玉梅,身着灰长衫,手拿一卷杂志,迎面而来。我恍然大悟,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我俩接上关系后,她说:“我们的力量太小了,必须发展壮大。”
按照她的布置,我先后找了同班同学周振淑(离休前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和二班同学仝玉一(离休前任山西省财贸办副主任),对她俩进行思想教育。等我发展基本成熟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全民抗战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大批平津逃亡学生涌入太原,武秀英家也聚满了平津逃亡同学,温玉梅便把我的关系转交给一个北平来的女大学生,她身穿月白长衫,长圆脸,很白净,很文雅,约二十三四岁,化名吴一凡。我向她汇报了准备发展周、仝的情况,她表示同意。约定在女师操场上开会。会上先宣布批准她俩入党,我是介绍人。成立党小组,由我任组长。除学习“党员须知”外,并布置工作任务,决定周振淑去国民师范办的学兵集训队讲课,我与仝玉一分别到晋生纺织厂及晋华烟厂给女工上课,发动她们参加抗日活动。不久,因仝玉一随校搬迁外县而中断。
在我和周振淑参加抗日活动中,一天吴悄悄告知我俩去海子边的大礼堂,听中共领导干部做时事报告。去时大礼堂已挤满了听众,台上的领导干部身穿灰军装,讲当前形势时,激昂慷慨,神采飞扬,批驳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提出“全面抗战”,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励人民参军参战,奋勇杀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才知讲话的是周恩来同志,我入党来第一次看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原来如此博学多才,气宇轩昂,感到党内真是人才济济,令人钦佩不已。使我们对当前形势及党的抗日纲领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俩兴奋极了,散会后,仍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
又一次,吴通知我俩去参加平津逃亡同学座谈会。也是在海子边的一间大房子里,屋里约有五六十人,其中以东北籍学生最多。个个发言激昂慷慨,对东北失守、平津失守、国家危急的形势,都义愤填膺,说到激动处,有的大骂当局不抵抗主义;有的声泪俱下,哭诉有家难归,有书难读;有的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再不在关内流浪!”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些歌声久久回荡在我俩的心头,激发起久久不能平抑的抗战激情。
这时战局总的趋势是敌寇长驱直入,蒋阎部队节节败退,八路军则源源不断开往晋北。战事已进入山西,敌机昼夜轮番轰炸太原,眼看太原即将沦陷。我已暗下决心,离家抗日,但家中弟妹多,年纪小,所以我先动员母亲携带弟妹匆忙南下,解除后顾之忧。不久,乔峰山、武秀英对我说:“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它是我党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组建的统一战线组织,主要进行战地抗日动员工作。参加后可以直接进行战地抗日工作。”我很高兴,随即我们三人都报名参加。三四天后,即派往忻州前线。临行前,南汉宸同志召集我们讲话,大意是:“前两批工作队刚派上去,就被敌机大炮吓回来了,此次抽调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其中还有三位女同志(武秀英、王雨薇和我),无总会命令,决不许擅自跑回。”听后,我决心上前线,决不做逃兵。
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上前线参战,父亲绝不会同意,我若不告而别,又怕他找不到我着急。因此留了一信,大意是:“现在敌寇入侵,眼看国破家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抗日,就得同仇敌忾,杀敌抗战。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女儿已被战地动委会派遣,北上忻州去了。”于是我脱下旗袍、皮鞋,穿上发的灰布军装,偷偷离开家,在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随战地工作团出发到了忻州。从此走上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
忻口战役正在忻县城北40里处进行,大炮日夜轰鸣,震耳欲聋,敌机沿铁路线轰炸忻县县城和太原市。我们到后,但见断壁残垣,处处房倒屋塌,一片凄凉景象。群众大都逃往他乡,城中基本渺无人烟。乔峰山等负责人见状,就地商量,除团部留三四人外,把团员分作城北、城南、城西三个组,每组六七人,我与武秀英、甘重斗(后任内务部副部长)等分在城南组,甘重斗任组长。我们住在城南郊十六七里外的乡下,工作组自己起火做饭,南瓜小米饭、萝卜咸菜,这对于吃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的我,无疑是一种磨炼。但大炮、飞机、小米、咸菜的战地生活,我却十分高兴。白天随农民下地,一方面帮助秋收,一方面宣传抗日。遇敌机来,立即就地卧倒,以高粱秆掩盖周身,一旦敌机走后,又照常起来工作,后来逐渐习以为常。
忻口之役由于八路军、国民党军队正侧面配合作战,坚持40多天。日寇死伤甚众,又强攻不下,只得改攻东路,顺平汉路南下,占井陉,破娘子关,沿正太路长驱直入,直奔太原而来。太原危在旦夕,总会来电,命我们撤往岢岚县,与总会会合。同时转来我父亲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归,随他南下。同志们都在观察我,看我能不能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坚持战斗在敌后。我随即表示,敌后抗战的决心不能动摇,并给我父回电表态。后听说我父痴痴等待,直到太原失守的前两天,见我回去无望,才在兵荒马乱中离太原南去。我们在忻县坚持工作半个月后,告别了当地群众,撤往岢岚。
从忻县到岢岚,途经静乐,约一百四五十里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没经过长途行军的锻炼,所以,每天最多不过四五十里,个个脚上都磨起了血泡,一瘸一拐地走着,晚上睡在老乡的仓房里,常被大耗子咬耳朵,既疼又怕,吓得直叫。经过三天的艰苦行军,总算到达了静乐县。当时的静乐县是晋西北的门户,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二〇师部就驻扎在岢岚县,距静乐60里,是他们前往忻县等地指挥作战的必经之地。南下又可直逼太原市郊,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师部早已派马隆兴(后任东海舰队司令)、朱辉照(1955年授中将军衔)等率工作团前来开展工作。战地总动委会派李蔚然任县动委会主任。他们三人组成县委会,马任书记,朱任组织部长,李任宣传部长。随马、朱而来的营、连干部则分别到四个区去开展工作。此外,县大队长王怀远、牺盟会特派员龚元恭、公道团长时曙明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当时静乐县形势很好。我们到静乐后,县委见来了大批生力军,便再三挽留。经请示岢岚总会后,乔峰山、甘重斗、张韵、侯勇、段春和、武秀英、王雨薇和我八人留下,回岢岚13人。
在县里休息三四天,除乔峰山、武秀英、王雨薇外,我们都先后被派往各区。甘重斗和我派往娄烦镇。该镇在静乐县南约90里,距太原较近,地理位置很重要,而且人烟稠密,比较富庶。县委很重视此地,先后派来八路军干部刘达仁、区牺盟特派员孙竹生等人。接着又派甘重斗任区动委会主任,我任区动委会宣传部长。不久,又派来段心维任区动委书记,孙竹生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搭起了区委的领导班子。另有区游击队大队长赵天任已早被派来。
区动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化,我们按“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由甘重斗兼动员分配部长,与旧区长、旧商会会长及地主士绅等周旋,动员他们捐献粮草钱财,以筹集粮秣弹药等,我与孙竹生则是向群众进行抗日教育,动员他们参军参战。发现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活动,李作基、武三威等就是由我们发展的,另外还发展游击队员30多人。刘达仁则是铲除汉奸,保证社会治安。当时区动委会设在尹家祠堂内,男同志都住西厢房,只有我独住东厢房。抗战初期,革命热情很高,秩序还不十分好。干部、游击队员四五十人,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白天乱哄哄的,不断有人来报名参加游击队。半夜我住处常被敲错了门,吓得我胆战心惊。
这时,日寇已攻占太原,屠杀了大批的士兵和百姓,连城西汾河水都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到处逃窜,骚扰百姓,烧杀打骂,无所不为。娄烦南边不少村民来报,恳请赵大队长解民于倒悬。赵天任听说后,立刻带领两个游击队员前往,收缴散兵枪支。不料在一次收缴枪支中,被一散兵开枪击中头部。由担架送回区上时,人已昏迷不醒。连夜送县城抢救,只走出十几里路便牺牲了。这是我在抗战中看到的第一位烈士。对他的悼念没有花圈,没有挽幛,只能默念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938年初,县委决定成立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除工会主任由当地工人张文焕担任外,分别把侯勇、段春和和我调回,分任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的主任。我任职后,先物色当地妇女积极分子巩凤英、邢爱蝉等,搭起妇救会的架子,内设宣传部、组织部、动员部、生产部。然后分赴各区,组建起区、村妇救会组织。依靠妇救会,做了几件工作:首先,对妇女宣传抗日形势,讲清抗日道理,消除“恐日病”,安定民心,启发觉悟,激发抗日热情。其次,动员丈夫、子弟参军参战。全县2500多名游击队员中,不乏“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事例。这些游击队员经过区、县组建和训练,绝大部分先后补充到一二〇师,当了八路军,上了前线。再次,动员粮草钱财,制作军鞋。全县妇女亲手制军鞋数千双,源源不断支援了部队。第四,在开展反摩擦斗争中,发挥了妇救会的威力。一次是旧军军长赵承绶,反动士绅杨集贤、张秀轩、郝孟九等造谣我方游击队游而不击,合理负担多征了粮草,对我方进行污蔑。续范亭主任、南汉宸部长曾两次从岢岚赶来,解决摩擦。为此召集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妇女界派巩凤英、邢爱蝉参加。摆出事实,展开辩论,据理力争,最后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取得了这次反摩擦的胜利。另一次是解决“张文焕事件”。1938年秋,阎锡山已在晋西南初步站稳脚跟,对敌后各县加强了反动统治。撤走了比较进步的旧县长张方焕,换来了反动的彭德勤。彭借口张文焕私造枪支,把张逮捕了,并准备枪毙。实际上是因为张搞的修械所,主要是给一二〇师修枪,但碍于统一战线,又说不出口,就给张捏造罪名,狠下毒手。为此,县委下决心要在这次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挽救张文焕的生命。李蔚然以动委会主任的身份,直接与彭德勤交涉要人。在工会、农会、青救会、妇女会的积极参加下,发动了全县近万名群众的示威活动,每天都有群众队伍到旧县政府门前请愿。妇女界也十分积极,我与巩凤英亲率全县数百名妇女,到旧县政府门前,名为请愿,实为示威。我们高喊:“张文焕无罪!”“坚决要求释放张文焕!”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使彭德勤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处死张文焕的判决,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最后无罪释放。
太原、忻县相继失守后,群众中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就连旧县长崔云彩都心慌意乱,想交班不干。旧公安局长直唉声叹气,埋怨地方秩序无法维持。群众更是怕鬼子打来而胆战心惊。因此,县委决定李蔚然、乔峰山去做统战人士工作。龚元恭和我兼任动委会宣传部正、副部长,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队、教唱救亡歌曲、写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画、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出了名叫“战潮”的油印小报、举办小学教员和游击队骨干训练班等,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宣传抗日形势,宣传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战论”,鼓舞群众斗志,培养抗日骨干。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克(现名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和我连夜编写了日寇抓壮丁的剧本,我在后台提词,他在前台演出,台下群众看后,很受教育。激动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有的当场报名参加游击队。
从1936年10月入党,到1938年10月,整整两年。前一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党秘密工作的锻炼;后一年则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中,初步经受抗战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开始学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经验。但是,革命圣地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所有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特别是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苏区,在我头脑中印象极其深刻。经再三请求后,终于在1938年10月经组织批准,送我去延安学习。我由沿途兵站转送,只身经黑峪口,第一次跨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到神(木)府(谷)边区。又经佳县、米脂、绥德,这三县当时还是国民党何绍南辖区,街上公开买卖大烟,狎妓嫖娼,歌舞升平,熙熙攘攘。我从前方带着一身硝烟、满腔热情来到后方。而这里却毫无抗战气氛,使我深深慨叹。再经边区管辖的清涧、甘谷等地,终于在10月下旬到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