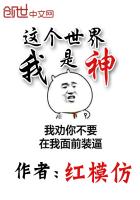李卫平
大姐田秀涓
她的秉性就像她的名字,甜(田)——秀——涓,温良恭俭让中不见丝毫的强劲。可当她向我谈起自己人生经历时,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仍不时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
“1917年,我出生在河北完县一户小经营地主家里。父亲叫田玉茹,是个女人的名字。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不重男轻女,对我们三姐妹非常好。那时乡下的女孩子很少有人读书,父亲用攒下的钱供我们上学。我和大妹都是从当时京、津、保地区很有名气的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不是那种有了钱便为富不仁的人,他有正义感,憎爱分明。七七事变不久,日寇侵占了我的家乡。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们三姐妹为了民族的危亡相继参加了抗日运动,那年我的小妹才13岁。在一次日军‘扫荡’中,汉奸出卖了我父亲,说老田头家有三个闺女都参加了八路。鬼子把父亲抓进据点,软硬兼施,严刑拷打,逼他把我们三姐妹招回来。父亲告诉鬼子:‘闺女是泼出去的水,俺是豁出去的命,你们别指望俺招回她们,等把你们这帮强盗打光了,她们会给俺上坟的!’鬼子恼羞成怒,把父亲的手脚捆在一起,在房梁上吊了整整一天一夜。老人家到死也没吐给鬼子一句软话。”
田秀涓正是从父亲善良、正直的品行中,领悟了爱与憎,辨明了善与恶,选择了自己人生的路。
当日寇铁蹄在家乡的土地上横行践踏时,田秀涓含着泪水辞去保定女师第二附小教员的职业,离开那群与她朝夕相处的孩子。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她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支离破碎的中国地图,在一旁写道:“同学们,我走了。为了我们的家!”
1938年初,田秀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年9月至1942年10月,她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五年中,担任了晋察冀边区抗日妇女救国会主任和中共北方局及北岳区党委妇委书记。在与凶残的日寇拼杀的疆场上,人们很难想象出,这位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色近视眼镜的文静女子,竟率领着抗日边区300万妇女干出了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
她们中有晋察冀边区第一位女县长陈舜玉,有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爆炸英雄崔先瑞,有子弟兵的母亲戎寇秀,有钢铁堡垒户薛兰英……那支由25万妇女组成的抗日妇女自卫队,拿起了各式各样的自卫工具,同鬼子展开了斗争。她们埋地雷、割电线、查路条、捉汉奸、抬担架、救伤员,为敌后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5年春天,太行山细雨如烟,梨花点点。田秀涓奔赴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田秀涓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蔡畅大姐紧紧拥抱着的那一刻,这位来自前线的妹妹痛哭失声。细心的大姐深知妹妹脸上的那一滴滴滚烫的泪水中所含的分量。
八年艰苦岁月,为了民族的生存,田秀涓做了一个女人可能做到的一切,也忍受了一个女人所不能忍受的牺牲。
1939年秋天,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夫人张瑞华介绍,田秀涓认识了当时任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校长的孙毅,在抗日前线俩人举行了婚礼。
田秀涓酷爱孩子,即使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她也盼着做一个母亲。
“我想要个孩子。”
“条件这么艰苦,能行吗?”
“为了孩子,我什么苦也吃得住!”她自信地告诉丈夫。
婚后八个月,百团大战开始。孙毅领兵上了前线,田秀涓带着身孕担任了新区开辟工作队队长,在敌人眼皮底下四处打游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一次通过敌人封锁沟时,她带头跳下一丈多高的沟底,不慎摔昏过去。醒来后,她知道已失去了那个孩子。
1941年春末夏初,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经过与敌人近一个月的周旋后,他们冲出敌人的“铁壁合围”。精疲力竭的田秀涓又一次失去了自己未曾降生的孩子。
“两次流产后,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我不想再要孩子了。心想也许孙毅说得对,条件的确太艰苦了。可我毕竟是个女人,尽管我知道那时肩上的担子有多重。1943年秋天,我终于在太行山里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孩子生下不久,日寇便纠集了四万多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我带着孩子在山里四处转移。我没有奶水,警卫员就提着个小水桶找来山羊奶给孩子吃。有一次敌人把我们包围在一座山上,我藏在一个山洞里,怕孩子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搜山的鬼子过去了,一看孩子的小脸都憋紫了。冬天来了,山里的风很硬,孩子受冻得了肺炎,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为了孩子的命,我和警卫员下山,在一户老乡家里躲起来。那天晚上,孩子不哭不闹了,老乡说,这孩子兴许是好了,谁知天没亮,孩子就死了。他只活了一个月零三天,连爸爸都没见上,连个名字都没起就死了。那会儿我的心都碎了,一连几天老想着和那孩子一起去了。我不是一个好母亲,我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没有保护住啊……”
这位曾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理事的母亲,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摘下眼镜,用手拭去眼角上的泪水,内疚的目光呆望着天花板,许久,许久没有说话。
……
“为了死去的姐妹们和活着的姐妹们,挺住了!”
田老从沙发中站起身,带着坚定的神情,缓缓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年代久远的军用皮挂包。她用微微颤抖着的手取出一个发黄的小本子,双手捧交给我。
“这里面记载着晋察冀边区牺牲的区级以上妇救会干部的名字和事迹。那时,每传来一位姐妹牺牲的消息,我就把她记在这小本上。你看一看,也许能从里面得到些什么。”
我接过小本,只见本子的扉页上写着“英烈名册”四个娟秀的大字。小本里布满了用毛笔、钢笔、铅笔书写的一行行小字,尽管年代久远,字迹却依然清晰:
“吕秀兰,19岁,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带领河北唐县区小队十余名女战士坚守挂云山高地,同200多名鬼子进行战斗,弹尽粮绝,她让姐妹们砸碎枪支,领头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刘桂枝,18岁,1942年4月在山西广灵县带领群众转移时,被敌追逐,因流产死去。
黄正清,19岁,1943年2月在山西广灵县工作时,被鬼子包围,她拉响手榴弹和两个鬼子同归于尽。
杨美亭,18岁,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不幸被捕,鬼子用刺刀挑开她胸膛浇上汽油后焚烧,英勇就义。
刘维熊,17岁,1943年在山西应县工作时被捕,次日被鬼子绞死在应县城木塔东街广场上。
刘明贤,18岁,1945年3月在河北行唐县工作时,被鬼子包围,宁死不屈跳井牺牲。
……
“共计58名,平均年龄未超过19岁。”
我合上小本,还未来得及思考这些死去的少女们会在今人的心灵中留下些什么,田老又从皮包中拿出一张三寸的大小的照片,还是用双手捧交给我。我接过照片,一幅罕见的惨烈影象展现在眼前:
一个裸露着身躯的少女倒卧在淌满鲜血的土地上。她的身体被刀割得支离破碎,被砍断的头颅脸朝上,牙关紧咬,一双怒目圆睁的大眼睛望着天空。我的心震颤着,脑子里顿觉一片空白,仿佛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一切文明在此断裂了,唯有那双圆睁怒视永不瞑目的眼睛像两团烈火在我的胸中燃烧着。
“今天的人们也许没有几个知道这位死去的姑娘了,可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她啊!”
她叫刘耀梅,是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的妇救会主任。1940年,我任边区妇救会主任时认识了她。这位小姑娘心灵手巧,聪明善良,让人非常喜欢,16岁便当上了村妇救会主任。领着妇女们做军鞋、救伤员。1942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秋季扫荡”。耀梅姑娘为掩护两名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没来得及转移被鬼子抓去。敌人把耀梅五花大绑抬到村头,捆在一颗柿子树上。嗜杀成性的鬼子中队长荒井满以为可以很容易地对付一个中国姑娘,威逼耀梅说出八路军伤员藏在哪里。耀梅只告诉他们三个字:“不知道!”这个日本皇族出身的鬼子气急败坏,命令鬼子兵把耀梅的父亲抓来,当着耀梅的面放出狼狗撕咬,老人一声声惨叫着,耀梅的心都碎了。她紧闭着双眼破口大骂。父亲被狼狗活活咬死在耀梅的面前,她也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冲醒耀梅,继续逼她说出八路军的伤员藏在哪里。耀梅仍是大骂这帮凶残的两脚兽。鬼子又拉着耀梅不满10岁的小弟弟,砍去了他的头,弟弟的鲜血喷洒在姐姐的脸上、身上,耀梅又一次昏死过去。太阳快落山了,耀梅再一次苏醒过来。残暴的荒井在一位中国姑娘面前没有别的招数了,他兽性大发,狂叫着:“中国女人有气节,我要尝尝她的肉是什么滋味”。荒井用军刀挑破耀梅的衣服,将耀梅腿上的一块肉割下来,当场烧熟吃了起来。几个鬼子兵跟着荒井用刀在耀梅身上乱剐着。耀梅嘴唇咬烂了,牙齿咬碎了,流着血用最后的气力一遍遍呼喊着: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鬼子又割掉耀梅的胸部,扯掉她的头发,砍断了她的头颅……”
讲到这,田老痛哭失声,无法自制。
悲痛的哭声,冲上云霄,在九天荡响,如同八千里雷霆,震撼着我的心。我的手剧烈地抖动着,泪水模糊了眼睛,不知是否用笔记下了这人类历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史实,只觉得心在流着泪,这泪淌进了周身的血液,并溶进了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全国妇联华北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理事,并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国访问。
她离休后,为了让后人们永远记住中华女儿为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牺牲,她组织起300多名老妇女工作者,在没有一分钱办公经费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八年的艰苦奋战,编写出三部共计100余万字的史料丛书,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二姐田映萱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路东的一座临街小院里,我登门拜访了田映萱老人。
这是一间非常简朴的居室,没有地毯,没有席梦思,几把老式沙发摆在不大的房子里显得格外的笨重。但屋中正墙上却挂着一幅价值连城的中堂,上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中是一幅大照片,古铜色的镜框中一位着长衫、蓄着八字浓须的中年人,正用深切的目光注视着屋中的主人和他们的一切。
他就是田映萱的公公、那位挥笔写下《庶民的胜利》等光辉篇章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
60多年前,当年仅38岁的大钊先生被军阀张作霖凶残地绞杀在北平京师看守所的时候,不满八岁的田映萱正跟着姐姐往来奔波于上学的路上。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位中年男子的死,竟为她和他们的生活凿开了一条路。
八年后,正是那本公公生前留给世人的《庶民的胜利》,召唤着田映萱踏上了求解放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取得胜利的一代人。
今天,在我用笨拙的笔去写这一代胜利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早在50年前发表的战地报告文学——《她们一群》。作者雷加这样记述着她一群中的田映萱:“在离前线不远的一条交通壕里,伴着炮火硝烟,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完县妇救会主任兼妇女自卫队队长。她的鼻子不大,一撮短发从白毛巾里露出来,吊在凸起的颧骨上。她的牙齿像贝壳一样白。柔嫩的乳白色的下巴,长着一层茸毛,只有在阳光下才看得出来,因此显得十分动人。除此之外,她和男人一样,一身青粗布衣裤,扎腿,布底皂鞋,右大襟的纽扣,一直扣到脖颈上。她的胸前,用白线挂着一个日记本和一段铅笔,这是全县救亡工作人员的特有的标志。一个没有星星的夜,田映萱就是这番装束,带着妇女自卫队,一夜间割断了几十余里长的日军电话线。撤离时,一位姑娘不慎丢下一只鞋。第二天,鬼子赶来时发现了这只鞋,惊恐万状地叫着:‘中国不得了了!连女人都来打我们了!’……”
雷加的文章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大意是说妇救会的姐妹们曾围绕着抗日与恋爱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田映萱坚决站到了反对恋爱的一边。
“是抗日第一呢?还是恋爱第一?”
她问对方。“恋爱归恋爱,抗日归抗日,两者分不开。”对方说。
“这会儿摆在咱们面前的是抗日,不是恋爱!”
“抗战十年也要咱们等十年再恋爱吗?!”
“对!抗战不胜利,我就不结婚!”
争辩中,田映萱立下了誓言。
结果呢?
她却食言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42年春节,田映萱与李大钊先生的长子、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结婚典礼。
“田老,您能不能谈一谈那场关于恋爱的辩论后,您又是怎样与李葆华相识、结婚的经过?”
“说起和葆华的相识,用现在的话讲是既偶然又必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全线溃退,华北沦陷,‘无村不带孝,处处是狼烟’。面对危局,党中央决定在华北地区开辟敌后战场。葆华根据中央的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从延安来到华北担任了晋察冀临时党委书记。这段日子里,他先是在山西五台山一带和聂荣臻同志一起工作,后又到了河北阜平县,在聂帅的指挥下,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与姐姐秀涓都被选为代表赴延安开会。在路上,我认识了葆华。那天,我实在是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他牵着一头小毛驴走过来,非要让给我骑。一旁的同志告诉我,他叫李葆华,是边区政府的一位领导,他的父亲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听说后,我很激动,对葆华的好感,对大钊先生的敬仰,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到延安后,领导让我进中央党校学习,葆华先是派到中央组织部负责七大代表的审查工作,后也来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又一次见到了他。在不长的相处中,我发现他不仅心地善良、淳朴,知识也非常丰富。和他在一起总有听不完的新鲜事,学不完的新知识,这样就总想和他在一起。到了后来,我竟忘记了和姐妹们辩论时立下的‘抗战不胜利,坚决不结婚’的誓言,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到了1942年春节,我们就结了婚……”
“结婚后,我倒是觉得肩上的压力重了,熟悉的同志见到我总是说:‘映萱呀,你可得好好地干啊!’我心里清楚,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我是大钊先生家里的人,干不好工作,人家会说她是李大钊的儿媳妇。那时,我丢人现眼是小事,重要的是不能给死去的公公脸上抹黑。结婚后,葆华经常向我谈起他的父亲,每谈一次我就难受好几天。父亲死得很惨、很悲壮,父亲被杀害后,是一位朋友将父亲的遗体悄悄安葬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墓上竖了一块无字碑。解放后,我和葆华来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父亲的墓地。每年4月28日父亲牺牲的这一天,我都要在父亲的遗像前敬一束鲜花。我想,作为一个儿媳,我没能孝敬过父亲,只有用这种方式和更好的工作来告慰他了。这几十年来,我到了许多地方,工作岗位多次变动,不管是干什么,我都使出自己最大的劲,不敢有一点偷懒啊!”
小妹田莉
和两位姐姐相比,小妹田莉怕是“厉害”的一位了。1937年,13岁的田莉在两个姐姐之前参加了革命,15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性格爽朗,爱说、爱笑,嗓子格外脆。1978年9月,当三姐妹同时被选为第四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相聚时,田莉的一首河北小调《回娘家》,赢来满堂喝彩。
有两件事让我钦佩不已。
一件事发生在抗战的日子里。有一次,担任妇救会锄奸委员的田莉,独自到敌占区开展工作。正开着会,百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庄。年仅16岁的田莉迅速疏散了开会的同志,随手抄起房东一只鞋底,往门前一块石墩上一坐,镇静自如地一针针纳了起来。鬼子端着刺刀挨家盘查,见这个小姑娘无事般地做着针线活儿,盘问了几句便走了过去。一旁的房东大娘为田莉捏了一把汗,问田莉:“闺女你怕吗?”“怕啥,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田莉坚毅地告诉大娘。
另一件事发生在那段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大地,一些人在裂变扭曲的心灵支配下,良知泯灭了。时任湖南省株洲市一家千人大厂党委书记的田莉,在精神与肉体上遭受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
她忍受得了吗?她活得下去吗?
早上,田莉走出家门去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10岁的小女儿拉住妈妈的手,流着泪说:“妈妈不去江边,妈妈开完会就回来,我给你做饭,包饺子。”
她在自传中写道:
“政治上的屈辱,肉体上的痛苦,真想一死了之。但我意识到,那样才是真正的耻辱……从1937年到1958年,我干了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妇女真正的解放并不在于妇女能干什么,而在于她们敢于面对一切屈辱折磨,挺起自己的腰杆,坚强地活在世人面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田莉又回到领导岗位,人们会问,这位曾遭受屈辱折磨的女人,又该如何偿还那恩恩怨怨呢?
除夕之夜,她来到一个领头整过她的人家中,送去两瓶老酒、一本年历。不需多说,那人已是泪流满面。
一个领头夺了她的权的干部,托人求她为有病在家待业的孩子找一份工作。她风雨奔波,亲自送去了一份就业登记表,还有治病的药。
……
无须赘述。
面对如此坚强、如此坦荡的一个女人,他们能不汗颜吗?!
在一篇由新华社采写的工业通讯中,我看到有关田莉的一段记述:
“这位女当家人,真有一手,抓产品质量就像老农牵着牛耕地,不划出一道沟来决不松手。她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泡’在车间里,劳累过度低血压病复发了,她摔倒在地上。工人们把她抬回家,劝她说:‘老田呀!你就躺上几天吧!我们不会让你的汗水白流的!’”
……
在给大姐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们都老了,生命的钟快摆到了尽头,如果今后有人写起我们姐妹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我们首先是女人,是尽了全力的女人,是没有愧对父亲和我们自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