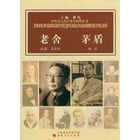在巴黎一个破败不堪的工作区里的窄窄的小巷中,有家名叫赛捷的下层小酒馆。这一天临近11点钟走进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衣着褴褛并且垂头丧气地进来了。他已喝得醉醺醺,歪三斜四地走近酒吧的吧台,嘴中的酒气冲天。
“喂!上酒!来人哪!”那男子大声呼喝着。
“先拿钱!”
酒吧的老板对他这样说。那男子掏出他的皮夹,钞票将他的皮夹塞得鼓鼓囊囊,他从中抽了一张扔在吧台上。
已将那一幕尽收眼中,一个名叫多玛的男子,他本是一名游医,却打扮光鲜。
多玛走上去,坐在那男子一旁。
“来把牌吧!我是多玛。”
“人们都亲热地叫我简德们,这名声很响?”
这名男子说出的法语有股伦敦味。接着这俩人去酒吧的秘室玩牌。这一夜,那名男子输掉了200法郎。
第二天晚上,那名男子又来了。同样输掉200法郎悻悻离去。到了第三日的晚上又来了可没耍纸牌,而是一直在喝个不停,并且一直自言自语。多玛听到他在翻来覆去念叨着“鲁·倍杰尼”这个词。
这让多玛的双目为之一亮,他搀扶着摇摇欲坠的简德们走出了酒吧,扶他坐到街边甬路的椅子上。
“喂!简德们!如果你再胡说八道的话,警察会将你抓走的!”
“什么?警察……凭什么抓我?”
“你在酒吧中,反反复复地讲‘鲁·倍杰尼’,那可是刚刚发生过怪异谋杀案子的一个地名,离这不远处。你哪有那多钱?你一定同那案子有关?”
“胡说!那是别人给我的!”
“什么人?”
“那……那不能讲。”
“为什么给么多钱?”
“这也不能说!”
“这人真是不好糊弄!”多玛心中暗想,随后他装得十分生气。
“既然如此,你不乐意如实讲出,那我可要对你讲清楚,据报纸报道,近来在鲁·倍杰尼有一个装有大宗钞票的灰袋子失窃,肯定是你偷了它吧?”
“你在胡编,那案子与我毫无关联。”
“虽骗我!哪来那么多钱?总共有多少?”
“5000法郎!”
这让多玛圆眼猛睁,这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他盯着那映在河水水面上的夜景不发一言。原来多玛就是那群窃取灰布袋中的一员。
街头浪人布荷米和西文·若力艾实施窃取灰布袋,多玛则在驾驶那辆小卡车,计划窃取成功之后便一同逃之夭夭,而结果却是布荷米遭到枪击而亡,西文也身负重伤,那灰布袋也就下落不明了。
盯着河中夜色而在心里回想以往经过的多玛猛地拍了拍简德们的肩头,说道:
“这案子咱们不再说了!我有个买卖不知你是否愿意做?”
“干什么?”
“那伙窃取灰布袋的小偷还计划着更大的诡计,那个计划让人心惊胆战。我与那人相识,他颇有名气。眼下他藏头换面不晓得居住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够找到他的住址便可获取几十万法郎的报酬!”
“让我协助你寻找那名男子?”
“对!钱我们平分,怎么样?”
“好,一言为定!”
“你怎么打算?”
“现在还没有,但我与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很熟悉,他们常去破解花样百出的谜团以及去搞到他人的隐情。我所得到的5000法郎,就是那家侦探事务所付给我的。”
“哦?他们到底让你做些什么?”
“有人希望侦探事务所去摸一个让警方抓去的年轻人的底细,名字叫做弗休尔。他预付了不少的定金,这5000法郎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假如把那些情况打探出来,我还可以得到5000法郎。”
多玛闻听到弗休尔这个名字,不由得心中一惊,可是在表面上仍然假装一种镇定自若的神态。
“哦?这么说你目前正侦察那个叫弗休尔·萨尔的年轻人?”
“对!我与那名先生已约定好要见一次面,商讨具体的办法,那名先生将派他的司机前往协和广场等候我,接着将我送往他的寓所。据说初次会面,他将付给我5000法郎?”
“你可再得5000法郎?运气真好!那你什么时候去见面?”
“星期六上午11点钟。”
“他叫什么?”
“劳佛·德布尼,就住在鲁·倍杰尼的别墅住宅区。”
“是他……”
多玛在心中思忖了一大会儿。那简德们已酣睡在那张椅子上,可能他今日酒喝得过多了。多玛把他的手伸进简德们的衣袋,指尖摸到了一叠钞票,他刚想将那些钞票悄悄地取出,没想到被猛然间苏醒的简德们握住手腕,谁知简德们力气颇大,多玛匆忙打算将手挣脱出来。简德们毫不相让,于是俩人厮打在了一起。
多玛拼命地把简德们推到一边去,简德们很快就落入了水中。他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晃动以求能重新上岸,然而没过多久就沉入水底,再也未能浮上水面。
“仅是一起酗酒工落水的事件!”
多玛的脸上浮现出奸邪狡诈的笑,他向周围看了看,随即向吵嚷的街市走去。
有个人头渐渐地从下游黑漆漆一片的水面浮出,那便是简德们。他看了看河岸空无一人,便用一流的泳技游向河的对岸,在岸上已有一辆自备轿车守候在那里。
司机发动起车,浑身湿淋淋的简德们立刻坐进了车中,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返回到哥勒尔·鲁杰庄园的罗宾,在第二天一见罗思推事的面,就马上向他打听弗休尔的相关情况。
“那个人如同谜一般,警局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由于他没有身份证件,无法得知他的家庭住址和他的真实年龄,对他进行询问,他也不知道,也许他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他杀人案呢?”
他一直翻来覆去地讲:‘我既没杀人,也没盗窃!’
“据我假设,也许他有着一段惨淡的历史,所以不想涉及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不管我们对他询问什么,他全都回答:‘不知道。’有关他的全部情况,都是个迷,这让我们颇费思量。”
罗思推事似乎非常丧气地讲述。
听到这儿,罗宾集中精力开始冥思苦想。
“推事至今仍然无法断定弗休尔的底细,警方在历尽艰辛地调查之后,对于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不清楚,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年轻人。”
罗宾觉得自己也坠入迷雾之中。
我已命令了在巴黎乃至全国的手下对那案子着手调查,只要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员,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最后发现了在赛捷那个小酒馆有个叫做多玛的游医同本案有着非常重要的干系,我乔装改扮成一个爱喝酒的无业游民。以简德们这个假名与他接触,又故意耍牌时输钱于他,并装作不小心显露那5000法郎来钓他上钩。接下来让他获悉星期六上午11点钟简德们要在协和广场约会,去等名叫德布尼的司机,随后前往德布尼的寓所。
“据我思考,多玛必定假扮成简德们前往约会。他与我从没见面,并且早已以为简德们被他踢入河中溺水而亡,故而他会大胆地前去会面领取那5000法郎。等我见到他,一定要让他将全部隐情全部说出。如此以来,那件怪异的案子便可真相大白了。”
想到这里时,耳边传来汽车停车熄火的声响,司机领那个多玛进了庄园。罗宾高声询问他:
“你就是那个由私人侦探事务所派遣来,为我刺探有关弗休尔的情况,叫作简德们的人吗?”
“不,不是!”
“不是?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这里仅仅,由于你就是亚森·罗宾。”
多玛开门见山地对他讲,他原本着罗宾将会大吃一惊,可是罗宾却是不为所动,反倒心中暗自窃喜:“太棒了!”
“就在这间卧室里,菲斯丁娜也曾说出我就是亚森·罗宾这样的话,菲斯丁娜是那个西文·若力艾的女朋友,与眼前的这位多玛定会有所牵连。所以,我特意安排下这锦囊妙计将他诱骗至此,没料到他居然中计!”罗宾禁不住在心中暗笑。
“是吗?既然你已知道了底细,我也就无需伪装,很对!亚森·罗宾就是我,在下层的小酒馆以坑蒙拐骗为生的你,竟会有这等眼力,多玛!”
听这么说,多玛似乎大吃一惊,可是强装镇定自若地抽着一支烟,并讲道:
“亚森·罗宾名副其实,你已将我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然而,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不久你便会掉眼泪的!”
“我从未那样做过!”
“那以后就未必了。我还会让你哭出声来!”
“真?你何手段?”
“我去揭发你!我要向警方揭发你,对他们讲在鲁·倍杰尼住宅区所发生的那件扑朔迷离的案子就是由化名为劳佛·德布尼的亚森·罗宾一手策划的。”
“这样说来我被抓走,你便可以从某人那里获取高额的奖金,那你跟我说,他是谁?”
多玛无言以对罗宾拍了拍他的肩头。
“咳!多玛!你不要做的蠢事!有没有兴趣与我联手?”
“跟你?”
“对!跟我。我十分渴望知道弗休尔的底细,因而我派遣简德们调查此事,已提前支付了5000法郎。可是他却至今不见踪影,没准儿让人干掉了也是可能的,你是否有兴趣为我调查此事?我可以先预付10000法郎,如何?”
闻听10000法郎,多玛好像有些动心,思索了半天讲道:
“弗休尔是由克拉德大夫向你介绍的,可是那庸医对于弗休尔的事全然不知。在他医院工作的一名男子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让大夫为弗休尔写封介绍信,他十分痛快地应下了,那人便潜进欧拉介力庄园盗窃了那个灰布袋,并且他就是谋害了那位小姐的街头流浪汉布荷米。”
“你所讲的情况我比你更为了解。可是,布荷米将弗休尔介绍于我到底意欲何为?”
“他计划向你勒索巨额的现金!”
“哦,可惜这个阴谋未能得逞!布荷米也死掉了,那个弗休尔也让警局抓住在押。可是这二人是怎样相识的?他们之间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吗?”
“那是在15年之前,布荷米便打算要利用弗休尔!但那里弗休尔还在上学。”
“你了解弗休尔的身世吗?”
“当然!弗休尔要是说起来也很苦命。在他年幼时,他便与爹娘失散了,他被居住在荒凉偏辟的山区的农夫收养了。”
“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吗?”
“可能不了解吧,因为当时他年龄尚小。他从小就聪明好学,上完小学后便去小店中做学徒工,在晚上读夜校,不到20岁就到巴黎闯荡,并在一所美院继续学习,最终获取设计师资历。”
“哦!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然而布荷米又是什么时候与他结识的?”
“在他生长在那户农夫家庭抚养时,农夫的妻子因为丈夫早逝而与布荷米互相勾搭。那女人将弗休尔的来历对布荷米讲了,说弗休尔并非自己所生,而是在很久远的时候由一名女子寄养在此,那女子临走之时扔下大笔的抚养费。那农夫的妻子再三交代布荷米一定不要把这件事露出去,自然也不能叫孩子知晓此事,所以孩子从头到尾认她为妈妈。”
“如此说来,具体的情况只有询问那农夫的妻子便明白了?”
“可是那女人早已死去,布荷米也死掉了,了解此事秘密的仅我一人。”
“那好,你将你所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讲给我听,把孩子寄养在农夫家中的那女子是孩子的妈妈?”
“不,听说孩子是拐骗而来的!”
“什么?拐骗?”
罗宾的脸色转阴,接着问:“那女子为什么要拐骗小孩呢?”
“这个……我……我不十分明白。”
奸猾的多玛盯着脸色阴暗的罗宾,接着他讲道:
“可能是为了报复吧!”
“为了报复?”
“是!那女子与孩子的父母有着仇深似海,因为报复的目的拐骗跑了惹人喜爱的孩子。”
“那女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我不大明白。可是据布荷米所言她是个家财万贯且貌美如山的女子,驾驶着一辆新款豪华车。”
多玛仍旧用奸诈的目光看了看罗宾。
罗宾此时的脸色更加阴沉,在往日里从不把心中的喜怒哀乐表现于色的罗宾,此次居然破例。这是因为在他的心中联想起28年前遭人拐骗的孩子杰恩。
“那孩子从小就叫作弗休尔吗?”
“不,那人放下孩子,孩子的名姓也没说,是那农夫的妻子为孩子取的名。”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
那女子一点儿也没有透露姓名便离开了,可是由于中途出了变故,不想竟被人获知了她的姓名。
由于布荷米觉得那女子必定是拐骗了他人的孩子,因此他打算以此为要挟去诈取钱财,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找寻出那女子的居住地,还有她的姓名。最后终于摸到消息,那女子在寄养完孩子返回的中途,因为汽车抛锚而在附近的修理厂修理过汽车。
布荷米追到那家修理厂去打探,正巧那女子对修理工人讲,在未修理好车子前她先去附近走一走。有名工人在她离开的时候,将她遗忘在车座上的皮包打开,看到里边有一大号信封,误以为装的是钞票,便窃取了。
“那女子对此事毫不知晓,车修好后便开车走了。后来那工人将信封打开一看,里边装的并非钞票,而是张信纸,由于大失所望而随意地扔在工具箱上。布荷米得知此事后,马上花钱从那个工人手中买下那信。”
“你见过那信吗?”
“我从未见过那信。然而,布荷米曾将上边的一段读给我听。”
“什么内容?”
“我忘了!”
“别骗人,说实话!”
“哦,好像,我回想起那女子的姓名来了!”
“叫什么?”
“克利思朵……克利思朵伯爵夫人!”
罗宾立时万分惊诧,几乎要跳起来。他追问道:
“什么?克利思朵伯爵夫人?”
“对!对!真的是这个名字!否则她怎会驾驶着豪华轿车,并留下巨额的抚养费?”
“嗯,克利思朵……伯爵夫人……”
罗宾的心在颤抖,那个女子便是被人称作“地煞魔女”的女人。
“除了这些,你还回想起其他的情况来吗?”
“哦,让我想……”多玛好像在逗罗宾好让他火急火燎,故装作一副苦苦思过的样子,并且双目紧闭。
“哦!还有,还有,我又回想出来一个人的姓名,好像是那孩子爸爸的……噢,是叫腊福·杜立美捷……与你那个劳佛·德布尼十分相似!”
罗宾以往曾化名为腊福·班德累捷;再以前也曾化名为腊福·杜立美捷,地煞克利思朵必定明白这些。
天哪!被那个克利思朵寄养在农夫家中的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那么说,设计师弗休尔便是我儿子,目前他却由于涉嫌谋杀而被警方抓捕在押。克利思朵为了达到报仇的目的不但把我的孩子拐骗走,还要设计让杰恩变成一名杀人凶手,并受到法律制裁而毙命,阴险恶毒的陷阱便是她设计的。
“像这样阴险毒辣的陷阱遍布我与我的儿子杰恩的四周,越想要摆脱愈是摆脱不掉,破解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已被杀掉的布荷米,他必定是克利思朵手下。”
罗宾认为谜团渐渐就要解开了。
“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便是侠盗亚森·罗宾,是弗休尔·萨尔的生父亲。”
“嗯?什么证据?在哪儿?”
“不用着急嘛!那些证据可是布荷米历尽艰辛找寻到的,收藏在一个大号信封中。”
“它如今在你那儿吗?”
“没有!在已死去的西文·若力艾的女朋友菲斯丁娜手中。”
“知道他在哪里吗?”
“此事不容易办到。自从西文去世后我便再没看见她,好像警方也正在找寻她。我相信我能将她找到,而且还可以从她手中将文件买下来,可是你要付我50万法郎才行!”
“呸!为了勒索我的钱财而胡编这些,是不是?”
罗宾凝视着多玛,接着用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罗思推事的电话。
“喂,罗思推事吗?是我,劳佛·德布尼,现在在我的卧室有目睹鲁·倍杰尼住宅区惨案的目击证人,请立刻与古塞警官一同前来!”
罗宾把听筒搁下,脸带着狡黠的笑容紧盯着多玛;多玛却有些目瞪口呆。
“你要……你计划怎么办?叫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不!仅仅是把你送至警局做个目击证人罢了。切记,当推事向你询问时,你定要如此回答,案发之时你驾着小船在欧拉介力庄园附近,接下来又藏身在漆黑的小路。
“推事坚持认定那个藏身在漆黑小路上的人是弗休尔,但他没有有力的证据。假如你能够证实那人是你,推事便可以排除掉弗休尔的嫌疑,他也就能获释了。”
“可是,一旦他们问及我半夜三更驾船去那里干什么?他们将认定我是同谋!”
“本来你就是同谋,这谁也毫无办法!”
“胡说!”多玛予以否认。
“我并没有胡说!多玛,你确系那俩人的同谋。”
“我绝对不是!”
“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认真听好!你便是布荷米的儿子,也就是西文·若力艾的兄长!你们全家都是无恶不作的恶棍!”
“不!不是这样……”
多玛的脸涨得通红,歇斯底里地叫着。
“你再强词夺理也于事无补!我早已调查得明明白白。我的手下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在巴黎也开着侦探事务所,就这段时间,我已将你们的身世及境况查得清清楚楚。”
多玛脸色突变。
“怎么样?多玛?另外你把简德们推到河中,让他溺水而亡,你还是杀人犯!”
罗宾的这番连哄带吓让多玛感到浑身发抖,罗宾的脸色却突然变得温和,他将双手轻按在多玛的肩头。
“多玛,虽然你是布荷米及西文·若力艾的同谋,但既未实施盗窃也未杀人行凶,你所犯之罪很是轻微,最多处以五六个月的判罚。假如你不愿坐牢的话,我采取办法让你出来,无论警局内部还是监狱都有我的手下。”
“你可称得上手眼通天了,侠盗亚森·罗宾真是名副其实!”
“还有让你更难相信的,你瞧这个!”
罗宾从桌斗中拿出一只灰布袋。
“哪来的破布袋?什么意思?”
“这便是你爸爸布荷米从欧拉介力庄园的金库中偷盗出来的,装有卡卜勒的大宗钞票。”
“是么?这……这……便是老爷子用命换来的?你是什么时候把它从我父亲手中夺走的?你真让人不寒而栗!”
“莫要误会,这东西并非是我将你爸爸杀害之后夺取的。”
“那它从何而来?”
布荷米在将这个布袋偷到手后立刻被人干掉了,因此西文·若力艾潜入附近的树林,直到深夜才返回去捡这个布袋,但有个半路上杀出的家伙。对他我也不大明白,可是他打算把西文手中的布袋夺过去,接下来,两个人便厮打起来。
“最终,西文被刺得身负重伤,那个人也未能得手便逃窜了。西文虽然拿到布袋,但他把布袋藏匿在草丛之中,正巧让我找到。”
“嗯!你真令人佩服!”
在警笛的鸣叫声中,警官古塞到了,多玛立刻要被抓去。当多玛行至门口猛回头,假装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会我报仇的。”他冲着罗宾往地上啐了一口。
“随你的便!”
罗宾笑容满面地说。俩人相互使个眼色,他二人假戏真作,演得栩栩如生。
警车开走后,罗宾倒在躺椅上沉沉地思考。
“天哪!弗休尔,你就是我的爱儿杰恩吗?或者……”
罗宾的脑海中反复思索着。
不久之后,罗宾去了鲁·倍杰尼附近的小村庄,敲响了一幢破破烂烂的公寓楼的三层房门。
那就是菲斯丁娜的寓所。自从西文·若力艾去世后,菲斯丁娜天天到医院上班。
房门被打开了,菲斯丁娜喷火欲出的双眼狠狠瞪了罗宾一眼,立刻又要将门关住,而罗宾却奋力地挤进屋内。
“菲斯丁娜,你像是仍在怨恨我。我已向你解释过多少遍了,西文的意外死亡与我毫无牵连。我此行只想消除你我之间的误会。先平静下来,认真听我说一说!”
菲斯丁娜默默无语,双手抱胸直立在罗宾身前。
“前几天我碰到多玛,他向我说了许多往事!”
“那有什么用?”
“多玛是已去世的西文·若力艾的哥哥,他俩都是布荷米之子,你应该明白这些吧?”
菲斯丁娜有些感到吃惊,接着漫不经心地讲:
“居然这些你也能调查明白?”
“那当然。并且多玛已按照我的建议,自觉地与警方合作!”
“为什么?”
“详细的情况日后我再对你细讲。我所做的全部目的在于能让弗休尔得到释放。我十分渴望见到弗休尔,仔细听听他对自己故事的讲述。你肯定会感到好奇,为什么我要关注弗休尔,那是因为我感到他也许就是我的儿子。”
菲斯丁娜静静地听罗宾的述说。
我曾有个叫杰恩的活泼可爱的男孩,可他却在我妻子去世不久被人拐骗走了,那时他仅是几个月大的婴儿。
直到如今,已是二十八年过去,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他。即使我想方设法四处寻找,可是这二十多年来却是音信杳无。我渴望找回我的孩子,哪怕折耗我的寿命,让我失去双手或者让我失明,我都心甘情愿。
可是,我若没了双手,再见我的孩子时我便无法去拥抱他;假如我双目失明,我便不能亲眼看看他了。一旦让我的双手抱过他,让我的双眼看一看他,让我马上失去手和眼我也在所不惜。
可是,我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此五六年后,每次我在马路上看到五六岁的男孩在玩耍时,总要不由得多看几眼;又度过了十个年头,每次与十几岁的少年路遇时坚持撵上去瞅瞅少年的脸;后来,当我遇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便会泪流满面。如今,无论怎样找到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很有可能是我的儿子,这年轻人便是弗休尔·萨尔,可是他却因涉嫌谋杀而受到警局拘捕。
我坚信杰恩不可能是杀人凶犯,尽管我是侠盗亚森·罗宾,但我做盗贼也有我的原则,我从来没有对人痛下杀手,我的儿子也绝不会去行凶的。假如弗休尔的确是我的亲儿子,他绝不是一个杀人犯。
“假如弗休尔真是案犯,他便不是我的孩子!我渴望确认一下弗休尔是不是案犯,也渴望搞明白他的来历。他出生在哪儿?他的双亲是谁?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菲斯丁娜?”
此时的菲斯丁娜已是泪流满面,她的怨恨、她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这名出生于科西嘉岛的女子被罗宾的侠骨柔情深深打动,她的泪水缓缓地落了下来。
“布荷米与西文·若力艾都坚持说弗休尔是我的儿子,因此他们设计以此要挟我,勒索我的钱财。他们能够产生这样念头,必有其存在的依据。菲斯丁娜,他们是否对你讲过关于弗休尔是不是我儿子的事?”
“他们说过。”
“他们有什么证据?”
“从未见到过!”
“不过多玛以前讲过,布荷米将他搜集到的关系到弗休尔的双亲,还有弗休尔出生的情况的证明都好好地装在信封中,那信封是你保管的。”
“可那些证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布荷米把它们交给我保存之前就销毁了。”
“啊?全部销毁了?”
“不!只保留下一件,封存在信封之中。你看,是它!”
说着,菲斯丁娜从衣柜拿出个信封来。
罗宾急速地将信封开开,仅找到放了一张纸片,在纸片上写有两行排得满满的字。
读完那两行字,罗宾犹如触电一般,心脏差不多不跳了,那些字是……
让小孩成长为杀人凶手,让他的爸爸痛苦一生。
让小孩成长为他爸爸的夙敌,使他们骨肉相残。
毋庸怀疑,那字确系克利思朵伯爵夫人所书写。上帝呀!这个“地煞恶魔”对我实施复仇不只是拐骗了杰恩,并且要千方百计使他变成一个杀人凶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煞!
罗宾的脸色惨如白纸,多么令人胆战心惊的复仇之心!已是三十年前的仇恨,凶煞仍旧要复仇。好吧!我除了同她针锋相对,奋起反击外别无出路,让“地煞恶魔”克利思朵与亚森·罗宾决一死战!
“菲斯丁娜,眼下克利思朵藏在哪里?请你如实地对我讲!”
罗宾声色俱厉地询问道。菲斯丁娜犹豫不决地讲:
“好……伯爵夫人……已去世了。”
“什么?去世了?真的吗?”
“对!她死了6年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要提到15年前的事,那时我的年龄很小,与我父母在科西嘉岛的小村里居住,她……伯爵夫人当时被一名男子带领着来到我所居住的小村。
“开始,我不知道她便是伯爵夫人。虽然她年轻貌美,但她的穿着打扮非常简朴,好像十分穷困。在我的双亲资助之下,她在村中租了间小房住下了,然而她的神志不大好。”
“什么?神志不清?”
听到这里,罗宾十分震惊地反问。
对,她是个恭顺贤良的神经病患者,对那时年龄不大的我很是温柔可亲。每当我去她的住处,她一直面带笑容地将我带进房间,可是没和我讲过一句话。
她经常一声不吭地坐着,根本不动弹一下;有的时候便不住地哭,凭泪水在脸上恣意地流,用一种空灵的眼神注视着院子。
“我觉得她十分的可怜,所以时常携带鲜花或金橘去看望她,她有时会把我抱起,与我脸贴着,可是她的脸上常是湿漉漉的。不久,她的状况越来越糟糕,终于死掉了,那已是6年之前发生的事了。她去世时,我与妈妈一同为她守灵,我哭泪流满面。”
菲斯丁娜一边说着,一边拿手绢擦拭泪水。
“领她去你们所住的小村的那名男子如今住在哪里?”
“他带着伯爵夫人来到我所居住的小村,替她租好住房就走了,再也没来过,也可能是个仆人或者精神病院的护士。”
“谁告诉你那女子是克利思朵伯爵夫人的?”
“这都是布荷米和西文讲的。他们为了找到她而走遍了意大利的各地,而他们说那女子是伯爵夫人,这让小村的居民感到十分惊讶。在伯爵夫人死掉之前,他俩就到了小村里,在她去世后,为了丧事,他俩在小村住了几个礼拜,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与西文相爱了,接着我与他一同来到巴黎。”
“为何他俩要找寻伯爵夫人?有什么企图呢?”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他俩时常在商讨着此事,至于商讨的内容我就清楚了。西文也没对我讲过那些,他以前告诉过我你化名为劳佛·德布尼,即侠盗亚森·罗宾。”
“到现在你仍坚信弗休尔是杀害西文·若力艾的真凶,并计划报仇雪恨吗?”
“在他没被我证实不是真凶之前,我将昼夜对他进行监视,伺机复仇。”
科西嘉岛的女子果然名副其实。奔放果敢的菲斯丁娜双目圆睁,怒火熊熊。
“我十分理解你心中的想法,假如我能够证明并非是弗休尔杀害西文的,恳请你放弃刚才的想法。”
“那是自然!我仇恨害死西文的人,却不是要仇恨弗休尔。”
“这个我明白。我要证明弗休尔并非案犯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我将与弗休尔会面,并仔细地问一问他。”
罗宾从房间出来,慢慢地下了楼梯。
克利思朵已不在人世,由于得了精神病死掉了……也许是对我的仇恨而精神失常。据说她时常涕哭不止,必定明白她自己离死不远了,是为大仇报而悔恨流下的泪。
在她去世后,仇杀的心理仍存活在一些人的心中,导致弗休尔涉嫌杀人。
还算庆幸的是,多玛已成为我的手下,由他去警方那里证实弗休尔是无辜的。假如弗休尔被判为杀人凶手而处以极刑的话,作为他爸爸的我将悲痛欲绝而死。
“这便是克利思朵的全盘计划,尽管她死掉了,也要对我报仇雪恨,上帝呀!像这样恐怖的‘地煞魔女’处在漆黑、阴暗的地狱中还注视着人间悲痛、忧愁的我而高兴不已。”
罗宾好像觉得“地煞魔女”死去的灵魂在把他紧紧缠住,正用那止余骨头的手摩挲着自己的脸庞,一股冰冷从后背脊椎处窜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