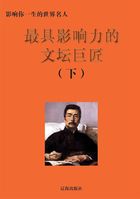苏轼在御史台监狱度过了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最后以“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之职贬谪黄州。他虽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以自嘲的口吻讽刺朝廷对自己的处置,但他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从京官变成了罪人,从热闹走向了寂寞。
苏轼到黄州,首先是生活发生了变化。一个不许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工资待遇是很低的,这使他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窘。苏轼到黄州,名为官员,实为罪犯,并无官舍供他居住,而是住在定惠寺中。不久,又迁至江边旧时的一个水驿——临皋亭。他在《寒食雨二首》其二中写到过当时的生活情形:“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而在写给秦观的信中更有具体的记述:“初到黄,廪入(俸禄收入)既绝,人口不少……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断(分)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天亮)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与秦太虚书七首》),真可谓严格的计划经济,不敢随意多花一文钱。其生活之苦况,可见一斑。
在临皋亭,屋漏失修,后来他的同年蔡景繁使有司稍加修葺(qì),才稍有改善,对落难时友人的相助,苏轼曾写诗为谢。
元丰四年(1081),这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个年头。当地一位叫马正卿的书生,实在看不过去,于是替他向官府申请到郡中一处旧军营的数十亩荒地。这对苏轼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苏轼带领家僮们开垦了这片荒地。因为这片荒地在州门的东面,苏轼就给它取名叫东坡,自己也自号“东坡居士”。在早春二月的一片飞雪中,苏轼又在这里修建了房屋,屋成,又在正堂上“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没留一点空白)也。”并号其堂为“雪堂”(《雪堂记》)。苏轼至此才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住所。
除了生活上的困窘之外,让苏轼最感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压抑。他虽不需要上班办公,但也不可随意悠闲度日,因他是朝廷的罪人,所以要受到官府的管制。苏轼素有文名,朝野士人一向争着与他交往,此时却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答陈师仲主簿书》)。他只能“深自闭塞,扁舟草履(lǚ,鞋),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淑书》)。而他自己也时时自我提醒,不但“灰心杜口,不曾看谒(拜访)人”,而且也尽量不与朋友笔墨往来,以免再因文字狱弄出是非。他每天闭门读书,闲对妻子,手抄《金刚经》,解《易》(《易经》),作《论语说》来打发日子。为了排遣苦闷,他除经常饮酒赏花,郊野寻春,谈佛问道,修炼养生外,也常与客人往来。“所与游者,亦不尽选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zhěnqí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隔阂)。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可见,他所交往的“客”,大多是和他相从于溪谷间的田父野叟。
苏轼在黄州东坡的生活并不如意,但他却能以“自娱”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的处境,保持自己旷达、洒脱的心态。如其《东坡》一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luò)确(山石险峻不平)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一位月夜杖履野步、傲世独立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