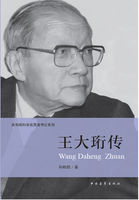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提出“变风俗,立法度”为当务之急,着手变法。熙宁三年,王安石出任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实施变法。当苏轼为苏洵守丧期满,第三次回到京城时,正赶上这场变革兴起。
苏轼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切关注现实,力主改革。仁宗末年,他在其《进策》中就提出过不少好的见解。但他强调“得人”而忽视“法制”;主张渐变而不赞成突变;主张“节用”却不重视理财,这就使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出于忠心和为国为民,苏轼写下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洋洋万言,针锋相对地全面批评新法,并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在这封万言书中,苏轼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建议:“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而已。”在谈到“结人心”时,他说道:“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油脂),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并指出:当今人心之不悦者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否则的话,“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就是说,不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天下百姓将无宁日。接着又指出农田水利法“甚非善政”,两税之外另收庸钱,会使百姓“必怨无疑”;青苗法所谓“不许抑配”(强行摊派)之说,亦是“空文”,其结果必定会“亏官害民”;均输法是朝廷投入很多,而“所损必多”。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极言青苗法、均输法等之得不偿失,并且质问神宗:“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最后又语重心长地劝神宗,不要听信那些“贪功之人”的“侥幸之说”,“若陛下信而用之,则是循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民怨必起。
在谈论“厚风俗”时,他明确提出:“夫国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强调道德之深,风俗之厚,乃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根本。“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
在谈论“存纲纪”时,他明确指出要加强御史台和谏院,因为“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他提醒神宗:“臣恐自兹以往(从今而后),习惯成风,尽力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一定要加强监察工作,不可让宰相集权过重,否则,纲纪已坏,后患无穷。
此文除向神宗皇帝献三言之外,又重申了自己过去已经给神宗提出过的意见,即作为人主,“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快),听言太广。”即是说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是“求治太速”,急于求成,而欲速则不达;“进人太锐”,提拔官员太快,难免鱼龙混杂;“听言太广”,什么人的话都听,难免偏听偏信,其矛头仍是指向王安石变法。
这封给神宗皇帝的上书,和当时神宗竭力支持并实际推行的“熙宁变法”大唱反调,全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反对急功近利,提出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把“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作为治国的根本之道。这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最集中、最系统、也最激烈的批判,是苏轼一生政治见解的集中体现。
平心而论,苏轼此文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弊病,这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认识问题的深刻;但他全盘否定新法,也自有其片面和保守之处。这封上书本身并未直接给他带来灾难,但他此后的一系列坎坷和挫折,根源确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实践和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苏轼对新法的认识也产生了一定变化,如肯定新法中的某些举措,反对旧党全盘废除新法等。他在晚年与朋友滕达道的信中曾说,过去自己对新法虽也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但“所言差缪,少有中理”。(《与滕达道书》)说明他已认识到虽然自己的出发点是“忧国”,但有些话说的不在理。这也充分体现了苏轼诚恳坦率、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