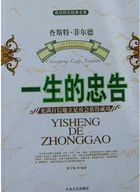双脚都是干的,头发也是干的,一切都是干的。窗户紧闭,窗外的大树在风中摇晃,但我书桌上的纸张却一动不动。我的座椅也一动不动。一切都是稳当的,固定的,结实的。我安然无恙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在几株参天大树的摇曳不停的枝叶间,可以见到蔚蓝色的海水。这就是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桥梁,欧、亚、非三个大陆之间的纽带。波峰上冒着白沫儿,但听不到拍岸的涛声。若要听得真切就必须打开窗户。如今又能安全地呆在这四壁都是书橱的书房里,令人多么惬意啊。但可怜的水手,在这样的大风天气里,还要在海上搏斗。窗前挂着一幅很大的地图,我把它打开。浩瀚的大西洋在地图上只是一个毫无生命的天堑,把一个四四方方的世界分成两部。右边是非洲,左边是美洲,上边是北极,下边是南极。把大西洋这样一个最为能动的、精力充沛的、永无止息的、不断奔腾的运输通途和传送工具画成这个样子,真是天大的误解。正如把一头跃在半空的羚羊摄入照片一样。这幅地图把永恒的运动画成静止的画面,正如把富有活力的海洋变成像撒哈拉沙漠似的静止,像阿尔卑斯山脉那样的僵化。惟一的区别只在于用色的不同。流动的海洋涂上蓝色,静止的陆地用绿色、黄色和白色。
真是一个美妙的游戏棋盘啊!你掷一下骰子,然后把你的小人儿移动几格。再掷一下,再移动几格。直到小人儿都被蓝颜色的地方挡住为止。你若把小人儿跳过蓝颜色的地方,就是作弊了。传播学的信奉者的确在作弊。他们把小人儿处处放在蓝格上。如果这蓝色的地方像海洋一样会转动的话,玩游戏的人全都要惊呆了。若是果真如此,就得制定几条新的游戏规则。只要白色和黑色的小人儿走到摩洛哥外面的一格,就可以借助加那利洋流,跳到美洲去。如果黄色的小人儿走到印度尼西亚外面的一格,就会碰上从波利尼西亚那里传来的日本洋流和美洲西北洋流,必须退回原处。总之,小人儿走动的方向若同转动的方向一致,就可以跳一大步,若同它相反,就停步一次。在这个比较现实的游戏中,只有黄色的沙漠、白色的坚冰和绿色的沼泽才是天堑。
我收起那挂在窗前的地图。窗外的地中海又出现在眼前。我推开窗户,静听那拍岸的涛声,任凭那海风吹乱我的文件,打乱我的沉思。让文件见鬼去吧!让那些“学派”,无论是传播学派还是孤立学派,统统见鬼去吧!洞开的窗户、清新的空气、暴雨、迅雷,这才是现实。只要那隆隆作响的大海会说话,它就会讲到古代那些未经文字记载的航行,足能同中世纪时正式记载下来的任何一次航行相匹敌。中世纪走的是下坡路,还不如古代哩。古代人民并不是游戏棋盘上的棋子。他们那些伟大的创造,表明他们是何等地生气勃勃、富有幻想、追根究底、勇敢大胆、聪明伶俐。他们比我们这些“电钮时代”的人要健壮得多,对于他们的上帝要比我们虔诚得多。但他们全身充满着自从亚当以来一直贮存在人类的腺体和神经中的全部虚荣、热爱、仇恨和欲望。古埃及水手离开红海,去访问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遥远的亚洲海港。他们从尼罗河口出发,交叉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在遥远的岛屿上强行征税,赋纳于法老。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虽然语言不同,文字迥异,但却相互交往,并都在遥远的岛屿上养育着水手和建筑工匠,把这些岛屿当做台阶,向北和向西进发,通过海洋来传播文明,并使这种文明生根发芽,开出灿烂的花,但仍是语言不同,文字迥异。我们不知道这些古埃及人是在何时涉足这些岛屿并造成上述影响的。但腓尼基人逐渐取而代之。对于他们的族源,他们最古老的船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东面和南面的近邻都用的是芦苇船。甚至西面的近邻也是如此―克里特岛的一枚古代指环上刻着一艘新月形的芦苇船,桅杆、船舱和索具俱全。马耳他岛的巨石寺庙遗迹上也镂刻着许多芦苇船。古代的文明,从腓尼基海域又传播至直布罗陀之外,传播到利克索斯,那里的芦苇船沿用多年不衰。如今,谁也无法追溯当年这些船舶来往的路线了。谁也不能根据遗迹来设想当年那些各种各样的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的原来面貌了。比如,葡属亚速尔群岛距离北美要比直布罗陀近得多,那里发现了一坛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金币和铜币,谁能说出这是哪些海员带来的呢?为了寻找财宝,为了躲灾避难,在古代的时候,有成千上万只船离开自己的港口出航,而没有只字可考。王室的画家把法老的红海之行描绘得十分显赫,垂诸不朽。可是,只是机缘凑巧才给我们留下一份材料,记下当年埃及商人航行到印度最远角落的壮举。这是古代历史学家埃拉托塞尼斯叙述他们用尼罗河上的芦苇船装备由锡兰航行到恒河的这段距离而以航行的天数来表示的记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纪念这些商人而建造一所寺庙。至于那强大的君主汉诺在公元前5世纪时带着六十条船,塞满了给养,载运着腓尼基男女移民,到大西洋航行之举,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件事至少镂刻在迦太基的石柱上,留诸后世。在汉诺时代以前很久,寻找锡矿和紫色染料的商人和寻找未开发的陆地的移民,就驶出了直布罗陀。因为在汉诺的船队沿大西洋海岸航外的第四天,就抵达了利克索斯古城,并找到了当地的向导,从而能把随后二十八天的近海航行中所经过的海角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汉诺的船队携带着充裕的给养。记载说,他的船队一直航行至西非的赤道地带,两个月以后才回到利克索斯。根据后来希腊人的记载,这位君主的石柱所镂刻的文字讲到利克索斯的居民时,把他们当做异国人,而前来探索的人在此逗留很久,获得了他们的友谊和指点。这些古代的航行者甚至同怀有敌意的原始部落也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他们总是先把一件诱人的礼物放在沙滩上,当做友好的表示,由当地的土著捡去,然后才敢离船登岸,这个法子应用于西非的丛林海岸,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没有组织的丛林部落中也能起作用,正如哥伦布及其追随者后来所体验的一样。
古代人充分了解在远航至异国他乡的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的好处。因此,在汉诺的著名探险前将近两个世纪时,腓尼基人和埃及人自然而然地在第一次有记录可考的环非航行中携手合作。法老尼卓的这次环非航行是由埃及人主持而由腓尼基船舶和船员参加的事业。但因法老本人没有亲自前往,所以埃及王墓和腓尼基的古代石柱都没有记述这件事。只是希罗多塔斯在访问这两个国家的时候,才在他著名的世界史上记录下来,不然就将被人遗忘了。
如果有一个船队,载着埃及人和腓尼基人驶过大西洋,那么,在大洋彼岸丛林的原始狩猎人将兴起什么样的文明呢?他们将兴建什么样的金字塔呢?
这幅愚蠢的地图把大西洋画成静止的蓝色无人区,把摩洛哥与墨西哥的距离(以航行时间计算)从几个星期拉长到几千年。的确,在哥伦布以前,美洲人不知木板船为何物,但他们的芦苇船却与地中海世界的芦苇船相似,从东到西的大洋流把美洲和地中海世界之间的一切幻想的疆界冲得一干二净。在几个湖泊人民的帮助下,我们造成了两艘芦苇船,并在两次航行中跨越了六千海里或一万一千公里,每次航行耗时两个月。在第二次航行中,我们登上了美洲的海岸。如果我们制造了一百艘“太阳”号,我们也会像利克索斯人民一样,学会在朱比角外的非洲海岸安全地往返航行。可是,我们也会多么经常地蒙受舵桨折断并在美洲登岸的危险啊!真要这样,我们“太阳”号上的八个人,在美洲丛林的原始部落中,将建立起什么样的文明呢?只有老天爷才会知道了。
我关上窗户,振笔疾书起来。
芦苇船是能够航海的,大西洋是一个由东向西的运输工具。除了这两条以外,其余的我们仍然不知道,还是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不过,在上下几千年的过程中,如果地中海的航海者从来没有追随太阳的轨迹而向西远征,如果自古以来没有一艘芦苇船在直布罗陀之外不幸折断舵桨,如果在躲避那危险的朱比角时竟没有一艘芦苇船偏离了航道,那倒是咄咄怪事了。我们“太阳”号如今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难道这是由于我们史无前例地折断舵桨,或是由于我们绝无仅有地能始终呆在芦苇船上的缘故吗?
写到这里,我倒的确掌握了一条理论:我们能够跨越大西洋,也许正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地图上航行,而是航行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