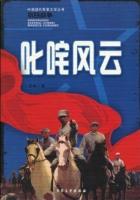这些天,徐俊芝做啥事都心神不定,常常丢三落四的。她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后,替村民办些实事的承诺,除花卉公司在侄儿翁建华的管理下,阻止了业务下滑的势头,为村民们代销了部分花木,让他们获得了些收入,能够让他们过一个比较实在的春节外,其他没有一点进展。特别是恰怡乐度假村非法开发的问题,不仅没有任何人制止,村民要求赔偿的事,也不了了之。于是她到村委会办公室,找荣树林,希望荣树林出面,再次向县里反映。
村委会办公室在桃花岛西北角。这是一幢两楼一底四合院样式的建筑。别看它外表黑不溜秋的,里面的设施、装饰却富丽堂皇。除了宽大的办公室外,舞厅、茶楼、餐厅、招待所一应俱全,甚至连洗头洗足室也齐备。村里专门招聘了几名青春年少的姑娘,整天嘻嘻哈哈地管理着这一切,接待着从县、镇两级来村检查、指导工作的公仆。村委会的一帮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一般小城镇的不三不四的服务。这是村委会主任古建华上任后,动用村提留款一百余万元修起来的。修好后,古建华以展示桃花村率先富起来的小康村风貌,体现村干部为民办事的作风,要求村干部,什么会计哟、民兵连长啊,计划生育专干啊,还有五个社的社长,统统集中到村委会办公楼办公。还每月实行工资制。刚刚开始时,被邰庚生树为勤政为民、村务公开的典型,引来许多穷村村干部暴瞪的目光。其实,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如果村官们不认真履行职责,像桃花村这样的集体企业早就租赁、承包或者转让的村,村经济结构就是农、副业生产的村,村干部的管理事务,没有像过去大集体时那样组织生产的任务,就只是催收公粮农业税,追大肚子等,就是农民说的“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打狗(狂犬病)挖坟(火葬),说长道短(调解纠纷)”等,就没有必要修那么大的办公楼。但古建华却天天在这里吃喝拉撒。
因此,村民们把它称为古公馆。
办公楼修好后,村支部书记荣树林,一不打牌,二不唱歌跳舞,不习惯到这儿办公。古建华对他说:“你不来上班,怎么考勤?怎么发工资啊?还有中午的误餐费,奖金呢,我总得公事公办吧?你是书记,要带头执行纪律吧?”荣树林算了算,古建华说的这费那奖的,每月不下五百块,他便来办公室练坐功了。
徐俊芝来到支部办公室,荣树林今天不在。徐俊芝看到一个叫细妹的勤杂工,正在收拾胡乱地丢着的一堆堆报刊。报刊多达二十余种,按上级部门的硬性考核指标,有的报刊必须订到社的小组、院坝,因此每种报刊订阅数就达二十来份。有中央级的《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有省市县的日报、周报。更多的是市县有权部门自办发行的内部报刊,如《工商行政》、《税务报》、《消防信息》、《女性人才》等等。仅仅这些报刊,全村需要订费几万元。村里的办公费,是由村民缴纳的统筹费开支的,仅报刊一样,每户需缴纳近两百元。村民说,相当于喂一头大肥猪赚的钱。这些报刊,全部堆码着,没有人翻过,更不用说发挥它们的作用。徐俊芝看到,昨天才到的每个社必须订阅的二十余份《陵江日报》、《古风周报》,码在墙角。细妹正用编织带将那些报刊捆起来。她见徐俊芝进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徐老板,反正没人看,我捆回家能煮顿饭呢。”
“你收拾吧,收拾吧。”徐俊芝嘴里说着,心里却想:这都是村民的血汗钱啊。
徐俊芝出了支部办公室,听到旁边的娱乐室传来稀里哗啦的打牌声,便推门走进去。
娱乐室里,古建华、荣光宗等人,和村里广播员、水利员、卫生员、防疫员等七大员,围着两张麻将桌,赌得正起劲。其实,这七大员,目前在村里很难发挥作用,大多数村早就不设了。但桃花村是县里的典型,是小康之村,便保留着。他们无一不是村、镇领导干部的子女或者堂客、姑爷舅子。他们天天到村办公室打牌,就算上班了,每月虽说只有三五百元工资,但干这些“事”,并不影响家里的生意,坡上的农活,谁都愿意领这耍耍钱。徐俊芝看那麻将桌,居然是自动的。徐俊芝不打麻将,但为了陪好客户,她的公司也准备了这些玩艺儿,有时也搓几把,输几个钱给那些公仆。她知道,这种麻将桌,价格在万元以上!她不知道古建华是用什么钱来置办这些家当的。
到这儿来打麻将的人,都是包包有钱,赌起心里不慌的角色。徐俊芝看到,张张麻将桌上,都码着二十元、五十元以上面值的钞票。古建华那一桌,堆着的是百元大钞。大家对徐俊芝这个不速之客,视而不见,继续豪赌着。
这时,从外面进来炊事员古胖子,他向徐俊芝点点头,走到古建华背后,弯腰说:“古主任,今天喝啥子酒?”
古建华抬起头:“喝啥子酒?老口味,百年好合,五星的哟!”说完,他的目光瞄到了徐俊芝,便说:“哎哟哟,大妈啊,你这个村民的青天老爷,今天来村委会,替我们当家作主了?”
徐俊芝本来想马上离开,但听到古建华酸不溜秋的话,心里就来气了:“建华,我还没有见过村干部是这么上班的!你们活得真是逍遥自在啊。”
“该逍遥自在呀,现在下班了,吃饭前大家玩玩,违了哪家法?谁管得了那么宽?”
徐俊芝说:“你叫村民们订的《村规民约》,要求村民不要赌博,你还好意思在村委会办公室干这个?如果我今天带了摄像机来,把你们的光辉形象公之于众,村民们恐怕要吼了吧?”
“大妈哟,村规民约,有屁用呀?你是堂堂的县人大代表,张起嘴巴说,要为村民办实事好事,你办了几件呀?不就是哄着村民买你的花木苗,让你赚大钱?”
荣光宗走过来,指着徐俊芝说:“徐大代表,你吐出去的口水,又吞回去了!说的话,比放的臭屁还不值钱!你根本没有钱来修大桥!捞到了代表,就当缩头乌龟了!”
“你听谁说的我不修大桥了?”徐俊芝忍住气问。
古建华吼道:“谁说的?镇里的大官说的!这不是癞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你想替你的男人赎罪,又没得能力和水平修好大桥!你想借修桥捞一把,看到没黑心钱赚,就不干了!”
荣光宗说:“徐大代表,幸好我没有投你的票,不是的话,你骗得我把堂客卖了,还得替你数钱哟。真他娘的!现在这世道,骗钱的花样百出,骗女人的甜言蜜语,骗官的堂堂皇皇,现在又出了骗代表的欺世盗名!”
荣光宗的话音一落,其他七大员就议论开了。
“桥真不修了?徐老板,你舍不得出钱了?”
“现在呀,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啥子鸡巴为民作主啊,都是哄老百姓的!”
水利员况冬生是荣树林的舅子,平时很信任徐俊芝的。他拉着徐俊芝的手说:“他大嫂呀,选民们投你的票,就想你能替我们说说话,办点修善积德的事。这桥不修了,让人寒心了。”
徐俊芝有口难辩。
炊事员古胖子打圆场:“别说空了吹的事了,吃饭,喝酒!古婶,你也在这里将就吃?”
古建华也笑嘻嘻地邀请道:“大妈,别怄气。雷也不打吃饭人。村委会的工作餐,虽说不像你们公司那样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将就填饱肚子。”
徐俊芝满怀一肚子气愤和懊恼,出了村委会办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