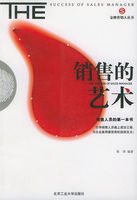〔中国〕朱光潜
我生平有一种坏脾气,每到市场去闲逛,见一样就想买一样,无论是怎样无用的破铜破铁,只要我一时高兴它,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钱。我做学问也是如此。今天丢开雪莱去看守熏烟鼓测量反应动作,明天又丢开柏拉图到古罗马地道下阴森曲折的坟窟中湖“高惕式”大教寺的起源。我已经整整做过三十年的学生,这三十年的光阴都是这样东打一拳西踢一脚的过去了。
在现代社会制度和学问状况之下,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一个人总得在许多同样有趣的路径之中选择一条出来走。
这已经成为学术界中不成文的宪法,所以读书人初见面,都有一番寒暄套语:“您学哪一科?”“文科。”“哪一门?”“文学。”假如发问者也是学文学的,于是“哪一国文学?哪一方面?哪一时代?哪一个作者?”等问题就接着逼来了。我也屡次被人这样一层紧逼一层地盘问过,虽然也照例回答,心中总不免有几分羞意,我何尝专门研究文学?更何况是哪一方面和哪一时代的文学呢!
在许多歧途中,我也曾碰上文学这一条路,说来也颇堪一笑。我立志研究文学,完全由于字义的误解。在我幼时所接触的小知识阶级中,“研究文学”四个字只有两种流行的涵义。做过几首诗,发表几篇文章,甚至翻译过几篇《伊索寓言》或是《安徒生童话》,就是“研究文学”。其次随便哼哼诗,念念文章或是看看小说,也是“研究文学”。我幼时也欢喜哼哼诗,念念文章,自以为比做诗发表文章者固不敢望尘,若云哼诗念文章即研究文学,则我亦何敢多让?这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个大原因。
谁知道区区字义的误解就误了我半世的光阴!到欧洲后见到西方“研究文学”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所有的准备,才懂《庄子》海若望洋而叹的比喻,才知道“研究文学”这个玩艺儿并不像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尤其不像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有趣。文学并不是一条直路通天边,由你埋头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极境的。“研究文学”也要绕许多弯路,也要做许多枯燥辛苦的工作。学了英文还要学法文,学了法文还要学德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等;时代的背景常把你拉到历史、哲学和宗教的范围里去;文艺原理又逼你去问津于图画、音乐、美学、心理学等等学问。这一场官司简直没有方法打得清!学科学的朋友们,往往羡慕学文学者天天可以逍闲自在地哼诗看小说,是幸福,不像他们自己天天要埋头记枯燥的公式,搜罗枯燥的事实。其实我心里有苦说不出,早知道“研究文学”原来要这样东奔西窜,悔不如学得一件手艺,备将来自食其力。我现在还时时存着学做小儿玩具或编藤器的念头。学会做小儿玩具或编藤器,我还是可以照旧哼诗念文章,但是遇到一般人对于“研究文学”者“专门哪一方面?”式的问题,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置之不理了。那是多么痛快的一大解脱!
我这番话并不是要唐突许多在外国大学中预备博士论文的人,只是向国内一般青年自道甘苦。青年们免不掉像我一样有一个嗜好文艺的时期,在现代中国学风之中,也恐怕免不掉像我一样以哼诗念文章为“研究文学”,倘若他们再像我一样因误解字义而走上错路,自然也难免有一日要懊悔。文艺像历史、哲学两种学问一样,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出来。如果人手就想造成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艺思想和政教已有半世纪的接触了,而仍然是隔膜,不能不归咎于只想望尖顶而不肯顾到基础。在文艺、哲学、历史三种学问中,“专门”和“研究工作”种种好听的名词,在今日中国实在都还谈不到。
这番话只是一个已经失败者对于将来想成功者的警告。如果不死心塌地地做基础工作,哼哼诗念念文章可以,随便做做诗发表几篇文章也可以,只是不要去“研究文学”。像我费过二三十年工夫的人还要走回头来学编藤器做小儿玩具,你说冤枉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