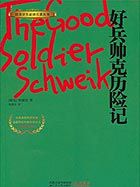有一天,我和托宾俩往科尼去,一来是我们有四元钱可花,二来是托宾正心烦,要消消遣。原来,他的女朋友卡蒂·马霍纳三个月前从北爱尔兰的斯莱戈郡到美国来,谁知却失踪了。她身上带着自己的两百元积蓄,还有托宾卖掉在博格尚诺继承的一所漂亮小房子和猪所得一百元。托宾接到过一封信,说她已经动身上他这儿来,可是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更没见过卡蒂·马霍纳。托宾在报上登了广告,但就是没找到这姑娘。
这样我和托宾便同去科尼,以为换换环境,吃吃香喷喷的玉米花,他的情绪会好起来。谁知托宾是个死脑瓜子,横竖开不了窍。听到人叫卖气球,他咬牙切齿;
看到电影,他便开口骂;邀他喝一盅他还会干,但他见了柠檬水会嗤之以鼻;见到给人拍照的来了他就想动手揍人。
于是,我带他走铺木板的小道少惹事生非。走到一个六八见方的小棚子边,托宾站住了,眼神恢复了正常。
他说:“只有这地方称我心。尼罗河来的相命师本领大,我请他们看看手相,看命里注定究竟会如何。”
托宾相信预兆,还有稀奇古怪的东西,什么黑猫啦,预测吉凶的数字啦,还有报纸上登的天气预报啦,他都莫名其妙地当真。
我们走进相命师鸡笼似的小棚子里,只见里面挂着红布,还有像铁路枢纽般线路纵横交错的掌纹图,很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门上的招牌写着:
埃及女手相大师佐佐。里面坐着个胖女人,身穿红短褂,短褂上绣着歪歪斜斜的字和小动物。托宾给她一角钱,摊开了手掌。他那手跟拉车运货的马的蹄子差不多。女手相大师抓起来细看着,想瞧瞧托宾登门是不是为一颗宝石让青蛙吞到肚里了,或者是掉了鞋样。
这位佐佐大师说道:“老弟,从你的手相来看呢——”
托宾打断了她的话:“你看的不是我的脚。漂亮固然算不上,手总还是手。”
女大师说:“从手相看你从小到大不是一帆风顺。往后还有灾。这根婚姻线——哟,是石头碰伤了还是怎么的?线上显得是动了姻缘。为了女朋友你已经遭到了挫折。”
“她这是在说卡蒂·马霍纳。”托宾把头偏过来对我一个人说,但声音不轻。
手相师又说:“有个人你总忘不了,又伤心,又着急。从纹路上看,是个女的,名字里有个字母是K,还有个是M。”
“哟哟!听见了吗?”托宾对我说。
手相师往下又道:
“遇见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和一个轻浮相的女人你得小心,这两个人会叫你遭灾。不出多少日子你会行水路,要破财。有一条掌纹使你时来运转。你要遇上一个人,他会带你交好运。这人长着个弯鼻子,你见了能认出来。”
“他的名字手相上看得出吗?遇上了他带我交好运,知道名字好让我跟他打招呼。”托宾问道。
手相师若有所思说:“手相上看不出名字怎么拼,但是看得出名字很长,当中必有字母O。相看完了。再见。别把门堵住了。”
“这女的真神!”托宾边上码头边说。
挤过码头的门时,一个黑人手里的雪茄烟烫了托宾的耳朵,闹出了乱子。托宾在他脖子上使劲来了一拳,在场的女人一个个尖叫起来。我见势不妙,没等警察赶到,便把托宾一把拉开。这家伙兴起的时候有得好瞧!
坐上往回开的船以后,托宾听到有人叫卖名牌啤酒。这时他知道了刚才的错,很想喝杯啤酒,可是伸手往口袋里一摸,发觉口袋空了。刚才有人在混乱中掏走了他的零钱。我们只好不喝,坐到长凳上,听甲板上的南欧人弹琴。要说这一趟出游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托宾又遇上了倒霉事,比原来更丧气,更无精打采。
船上有个年轻女人靠在栏杆上坐着,凭一身穿着的费用够得上坐高档红汽车,头发的颜色像没抽过烟的海泡石烟斗。托宾从她身边过时无意中踢到了她的脚。平常他喝了酒对女人也是彬彬有礼,这一次更是,想抓起帽子表示道歉。可是他倒把帽子碰掉了,又遇上风,帽子吹落到水里。
托宾走回来后坐下了。我留心看着他,他老兄遇上的倒霉事已经太多。如果让倒霉事怄急了,见到穿漂亮衣服的人他真会抬腿踢,还会抢过船来开。
托宾坐了一会儿,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兴奋地说:“约翰,你看我们现在怎么啦?我们不是在走水路吗?”
“走水路也别兴奋,船再过十分钟就靠岸了。”我说。
“你瞧,瞧那坐在凳上的轻浮相女人。还有那烫了我的耳朵的黑人,你没忘吧?我不是丢了钱吗?有一元六角五分呢!”
我以为他只是在数他遭的难,像许多人那样,发作起来有个借口,便好言劝道,别把这些事看得太认真。
“得啦,”托宾说,“预言家就是有天才,通了神的人说话就是灵,你长着耳朵还听不进。那手相师看了我的巴掌说什么你忘啦?
眼见着都应验了。她说‘遇见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和一个轻浮相的女人你得当心,这两个人会叫你遭灾。’你就忘了那黑人?
虽说我也揍了一拳,让他遭了报应。我帽子吹到水里去要怪那黄头发的女人,你说说看,这种女人不轻浮谁轻浮?
出了射击场以后放在我衣服里的一元六角五分钱又是到哪儿去了?”
托宾说得头头是道,似乎当真有人能未卜先知,但我认为,这些事无论谁到科尼都可能遇上,不能说是手相师灵验。
托宾起身满甲板地走,用发红的小眼睛细细打量船上的乘客。我问他这是为什么。托宾心里想的事你不知道,除非他干了出来。
他说:
“告诉你吧,从我手相上看,我能遇上救星,我这就在找。我要找着那个能使我时来运转的弯鼻子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救。你这辈子哪儿见过该下地狱的人长着直鼻子的,约翰?”
船九点三十分靠岸,我们下了船,从二十二大街进城,托宾没戴帽子。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气灯下路面高的地方望着月亮。他个子高,衣着讲究,嘴里叼着一根雪茄。我还发现他的鼻子从鼻梁往下拐了两个弯,就像蛇爬行时身体摆动着一样。托宾这时也看见了。我听见他呼吸声很响,如同一匹刚卸鞍的马,直喷鼻息。他直向那人走去。我也跟着他走。
“你好!”托宾对那人说。那人善交际,拿出根雪茄,也还礼问好。
托宾说:“请问你尊姓大名,让我们看看是长是短。也许我们有必要跟你结识结识。”
那人很有礼貌地说:“我名叫弗里登豪斯曼,就是马克西默斯·格·弗里登豪斯曼。”
“长短倒对上了,”托宾说,“这么长的名字拼起来是不是用得着一个字母O呢?”
“那没有。”那人说。
“你就写进一个O不行吗?”托宾问道,心急了。
“如果你从心底里不喜欢外国拼法,那么悉听尊便,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加上一个O未尝不可。”长弯鼻子的人说。
“这就行啦。”托宾说,“我们俩一个叫约翰·默伦,一个叫丹尼尔·托宾。”
“幸会,幸会!”那人说着一鞠躬,“想来两位不会在十字路口举行拼写比赛,那么请问,刚才说这么多话究竟有何贵干呢?”
“就为你有两个特点与埃及手相师替我看相时讲的一模一样。”托宾答道,开始讲他的缘由,“我遇上个黑人,倒了霉,坐船又碰到了个黄头发女人跷起脚,又没好事,还破了一元六角五分的财,都应了手相师的话。她说只有你能消灾,让我时来运转。”
那人不再吸烟,看着我,问道:“你看他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们俩该不一样吧?我看你的模样像是在照看他。”
“是这回事。”我对他说,“而且我朋友的手相上注定要遇上你这么个人,你跟手相师说的没两样,就像左马蹄跟右马蹄没两样。要是有两样,丹尼尔的手相上也许还是看得出来,那谁能说?”
“你们俩是一起的。很高兴见到了两位。”长弯鼻子的人说着往街两头望,盼望有警察来,“再见吧!”
说完他把烟塞进嘴里,横过马路快步便走。但托宾紧跟到了他身边,我也跟到了他另一边。
“干什么?”他马上在人行道上站定了,把帽子往后一推,“你们还要跟着我?”他提高嗓门,嚷道,“告诉你们吧,见到两位十分荣幸,可是我不想再跟两位打交道。我现在要回家。”
“那行,回家就回家吧。”托宾说,靠到了他衣袖上,“我就在你们家门口等,到明天早上你总还得出来。我遇上了黑人跟那黄头发女人,又破了一元六角五分的财,倒了霉,除霉气非你不行。”
“这真是莫名其妙!”那人转身对我说,他认为我是两个疯子中神志清醒些的,“请你带他回家好吗?”
我对他道:“先生,你不知道,丹尼尔·托宾现在精神正常,平常也正常。是这么回事:
大概他多喝了两盅,兴奋了,又理不清思路,便有一点点糊涂。他就想脱掉手相师说的倒霉气,也没做出什么越轨违法的事来。我这就向你详细说说。”接着我把手相师怎么怎么相命,他的特征与从手相上看出的救星怎么怎么相合,都告诉了他。最后我说,“现在你总该明白我在这出戏里唱的什么角了吧。我已经说得清楚,我是托宾的朋友。当有钱人的朋友容易,有便宜占。做穷人的朋友也不难,他们会对你千恩万谢,还可以在报上登个照片,让人看到你一手提着一箱煤,一手抱着个孤儿站在一家人家门前。但是当天生傻瓜的真朋友就难,要有几手当朋友的本领。我现在当的就是这种朋友。我知道我伸出手看手相看不出好命,条条纹路注定了要干为难的事。没错,全纽约就数你的鼻子最弯,我还是不相信算命的人就那么灵,能看出你可以让人时来运转。不过呢,你的特点与丹尼尔手相上看出的一点没差,所以我想帮他试试看,除非是他知道了你真办不到。”
那人听完以后便马上笑起来,靠在墙角上放声打哈哈。笑过以后手往我和托宾背上一拍,接着又抓住我们的手臂,一边一个。
他说:“误会,误会!我哪能料到会遇到这种凑巧事?
差一点就对不起两位了。离这儿没几步有家咖啡馆,里面舒服得很,去聊聊各人的个性最合适。我们就喝上一杯,边喝边谈有没有绝对的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
说着,他领我和托宾进了一家咖啡馆的后厅,要了几杯,把钱放在桌上。他看着我和托宾时的神态,仿佛他是我们的兄长。他还请我们抽烟。
“两位还不知道,”命中注定相逢的人说,“我干的那一行就是所谓‘动笔杆子’。今天晚上我出门寻找人的个性和上天遵循的永恒。你们见到我时,我正在思考明媚的月亮与路的关系。明月照马路的暂时现象很有诗意,很美,虽然月亮只是一个万古不变、没有情感、不停运动的物体。当然,各人的看法不会相同,在文人眼里,条件是颠倒过来的。我很想写一本书,解释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千奇百怪的事。”
“那你可以把我写进去,”托宾迫不及待地问,“你会把我写进书里吗?”
“我不会,”那人答道,“因为你上不了封面。现在还不行。至多我只能个人喜欢你,摧毁出版界限制的时间还不成熟。你的事见诸文字会绝妙。这份高兴只好归我一人独享。但是两位,我谢谢你们,我真心感谢你们。”
“你越讲越叫我憋不住了!”托宾开口了,在桌上当地一拳,还吹胡子瞪眼睛,“你长着个弯鼻子,本来弯鼻子会让我时来运转,可是你给人的好处像大鼓响,听得见摸不着。你口口声声书呀书,有什么用?
只是吹过缝的风,会呜呜叫。这样看来,看手相不顶用,灵验了的只有那黑人,黄头发女人,还有——”
那高个子打断了他:“别瞎闹!
你别让相命那玩意儿迷了心窍。我的鼻子只能干它分内的事。来,把杯子倒满,谈人的个性得边喝边谈,一本正经只谈不喝,人的个性谈不起劲。”
我觉得这动笔杆子的人没有白相逢。我和托宾让人算准,已身无分文,但这个人高高兴兴,把三人的账全付了。托宾却只闷声喝着,很不痛快,眼都发红。
最后我们出了咖啡店,在人行道上站了站,这时已是夜晚十一点。那人说他得回家,邀我和托宾送他一程。过了两个路口后,我们到了一条小街,这里有一片砖房,屋前有高坪台和铁护栏。那人走到一所砖房前停住了脚,抬头一望顶层窗口已没有了灯光。
“这就是寒舍,”他说道,“看样子我太太已经就寝。恕我冒昧,两位不嫌弃就请进。想请两位就座地下室,我们吃上一顿,也好提提神。有美味冷鸡,干酪,还有一两瓶酒。欢迎两位来进餐,你们陪我一程,十分感谢。”
我和托宾已经饿了,同时也觉得吃一顿并不能算昧良心的事,便都没推辞。托宾不过还是迷信他那一套,认为喝上几盅,吃上一顿冷餐,也应验了手相上注定的交好运。
“请下阶梯,”长着弯鼻子的人说,“我先从上边门进,再领两位。厨房里新请了位姑娘,我去叫她烧壶咖啡,让两位喝了再走。卡蒂·马霍纳是才来三个月的新手,咖啡烧得倒挺好吃。请进吧,我去叫她伺候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