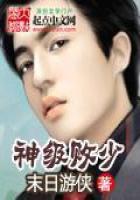《淮南子》中“道德”的基本内涵,是先验与经验并具的。道家之“道”不仅是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同时也是道德伦理的最高范畴,得道是道家所设定和追求的最高的人生修养目标。人性论不同,那么道德价值定位以及政治观也随之不同。“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指出了道德的形上依据。德是源于道的,道是在德的修行实践中才能获得,而能保持这份得于道的天性实际就具有了德性。因此,“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此自然道德论基本袭用原始道家的观点,道德具有质朴自然的特征,与儒家人为制定的仁义不同。“往古之时……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道德是自然的,而智故是人为机巧的,当道德显扬时,智故则无处存身。《淮南子》以道为万物的本原,以德为万物的本性,因而道与德都是自然或本然的。道产生并包容万物,道是事物之理,德则为事物的特性,二者是表与里的关系,道与德就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无须外求。这是一个普遍自然的宇宙的道德法则,超越了人为制定的仁义礼智的社会道德和法则,显示了容纳万物的博大观念和广阔的思维空间。道家的自然道德特征实际是坚守了道德的纯正本质,以抵制俗世的伪诈,寻求身心的超越,试图从俗世的道德桎梏中解脱出来,探寻符合人的本真的道德。
道与德是形影不离的。从二者存在的先后顺序看,道是先于德的,德是道的内在属性,若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二者是可以分离的,德是可以脱离道而存在。“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道高于德,德本于道。“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迩,近之则远,不得其道,若观?鱼。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道与德如同革与韦,革为去毛的兽皮,韦是加工过的熟皮。德源于道,道是万物的本原,是未经加工的,而德是道的功用,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无道则无德,道与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二者没有截然的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道在德的背后,德是道的显现,人们只有通过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道。圣人之心若明镜一般,万物无遗地呈现于前,无为而能得物之真,但自身并无损伤和缺失。“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道与德具有一致性。“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是事物运行变化的根据,决定和引导事物的发展。德与性相连,对性有辅助功能。道落实于人生的层面上就被称为德,德又常常反映人的品质,因此德总是与人性相连,成为人性的本质内容。“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道是德产生的根本和治理的依据。“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德既然存在于个体之中,能反映人的品性,因此则可以通过个体的修行获得。道是作为治世的总原则和总根据,道与德既是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又是个人修行的理论依据,实际将修身与治国从内部自我管理的角度统一起来。《管子》曾对道与德的关系进行过分析,“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道存在于德之中,德总是与生命相连,因此,德是生的表现。德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二者是不分的。《淮南子》认为道与德相连,“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德是道的外化,拥有德即合乎道,才能得到道的偏爱。
道德可以自治,但需有外在条件的允许,《淮南子》注意到时机在成事中的重要性,提出要“待遇”、“待时”: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
德可以使个人的修养得到提高,得道能够使社会自治,但二者都不是用来役使他人,使社会暴乱起来,而是通过自修自治使整个社会、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呈现出的有序和谐。道与德是社会必不可缺的,圣贤在和平时期依此可以保全自身,在乱世却能借此成就霸王之业。而要成为贤人和霸王,除自身的道德修养外,且须具有外在时机的成熟,这不是单靠个人的智能所能达到的。因此,主客观条件都要重视。此外,君子在立身行事时不应追求和计较彰显外在的名誉,并且当百姓能淡泊名利而不追究利的根源,这样社会才不会有争端,个体的自立与自足才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治。因此立足于个体自身的完善,等待适当的时机则自然能成就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