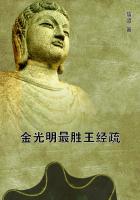然而,随着《州际商务法案》(1887年)和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案》(1890年)的出台,宗教的千禧年主义的力量和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冲动力都在减弱,特别是铁路的力量。由于农场主是铁路运费长期、大幅度下降的受益人,所以提高铁路运费的议题很少能够在价格听证会上提出。《州际商务法案》提出的热门问题是非常低的长途运输费率和高得不成比例的短途运输费率。但到此时,受到损害的是东部的商人;而西部狡猾的商人兼农场主们早就明白,正是这种运费差异才使他们能够在商业中生存。
在确定铁路运费方面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只要铁路方认为能够承受,他们可以随意定价。当横贯东西的长途铁路线刚刚开通的时候,铁路按照里程把运价定得很高,结果业务量非常少。只有当铁路调低了运费之后,美国西部的小麦才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被运到了海港,从而逐渐统治了世界市场。纽约的农场主和粮食商人们都是大输家,而且,通过国会来要求提高从西部到东部的铁路运费的机会几乎为零。另一方面,农场主们并不担心运价的变动,因为长年不断的价格战经常使运价出现大幅度的此消彼长。东部运输联盟是东部一个大型的铁路联营;在19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能力很强的阿尔伯特?芬克领导着这个联营,并采取了一些稳定东部运价的措施。少数国会议员公开地抵制改革家们反对联营的言论,但是许多人逐渐相信,对联营加以规范将有可能提供一个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使铁路运价稳定下来。
在通过谢尔曼的《反托斯法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正、反两方面的感情。底层民众担心“垄断”得到临时性的补贴:为了使人民党在1896年获得认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提出了人民党唯一的政纲——银币的自由铸造。同时,正在兴起的学术派,如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约翰?贝茨?克拉克[19]和理查德?伊利,也开始质疑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的合法有效性;而且,至少有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思想。一种看法也在探索中形成了,那就是在钢铁和石油这样的工业领域,全球性的竞争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销组织。就像《州际商务法案》一样,改革家们经过多年的活动才最后实现了公众期盼已久的结果;但是,人们还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法案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
总而言之,并不是必要的腐败和无能促成了像《州际商务法案》和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案》这样缺乏效力的妥协。国会议员们可能是以故意的“等等看”的态度创造出了这两个法案。《州际商务法案》规定了新的、广泛的监督权力,可以决定运价是否是“合理而公平的”;但是,它却没有设定价格的权力,或者除了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外的强制权力。法案也的确禁止在长途和短途之间存在运价歧视,但是又因为一个限定条件而大打折扣:它只适用于“充分相似的情况或情景”;法庭为此规定的范围也非常狭窄,因此,只要存在竞争,就足以突破这个“充分相似”的框架。法案明确禁止的内容只有折扣和联营。这个法案也没有获得一致的支持;例如,在芬克的影响下,法案的发起人之一、纽约州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就拒绝签署有关反对联营的条款。
同样,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案》的表述也非常谨慎。第一个草案中有禁止限制“充分和自由的竞争”这样的条文,但后来却被替换成了传统的习惯法的程式:法律只禁止下列合同或者联合——“限制交易或者商务”,或者试图“垄断任何部分的……交易或者商务。”久经世故的国会议员们充分注意到了习惯法先例的灵活性。改革者们认为他们赢得了一轮胜利,可以对那些违反者施以可怕的惩罚:监禁、巨额罚款以及没收公司资产。但是,大家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法庭根本不会使用这些惩罚;最后,连那些改革者们也都游说国会减轻惩罚的力度。
这两部法案都产生了一个未曾料到的结果,那就是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在《谢尔曼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追加了一个有关“合理性”司法解释。20世纪初,最高法院逐渐地朝迁就主义者的立场转变,与英国的习惯法更加相似。到1911年标准石油解体的时候,“合理性”的原则已经占了上风:标准石油的市场份额被推定为90%,被认为足以证明其“不合理的”集中性;但是,美国钢铁公司也拥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却通过了审查。(偏见战胜了逻辑,许多年来,最高法院一方面坚持认为工会组织是“限制交易的组织”,但另一方面,它却拒绝把适用于商业组织的“合理性”审查适用于工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