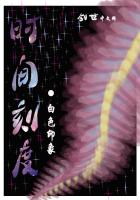最后,公司结构向规模更大、更加官僚化的方向转变还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重构。
劳工组织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工资和工作时间方面的纠纷而引起的停工也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工会基本上是地方性的组织,而且是以不同的工艺为基础组成的:如果纽约市的制帽工人组织一场罢工,费城或者波士顿的制帽工人是不太可能与他们配合的。此外,在内战以前,制造业的主要模式还是手工工匠制造;工厂的所有者兼管理者原来通常也是与他们的工人一样的工匠,而且大多数企业规模都很小,能够形成一种“共有企业”的精神。19世纪50年代,这一点还曾给英国的调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在规模较大的工厂,这种工匠模式也通过内部合同的方式一直存续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计件产品为基础,许多工厂被出租给当地的一些行家,这些行家自己组织工匠和设备,并可以分到工厂里相应面积的工作场地。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霍利式的连续加工制造工艺得到了巩固和提高——除了钢铁业以外,石油、化学制造、磨粉以及肉类加工业也是如此——从而淘汰了许多传统的工匠制造领域。劳工历史学家们有时也谈到这种制造业的“非技术化”现象,这种说法是不太精确的。在轧钢厂里,要想熟练地控制高速运转的钢轨生产设备,需要操作者有极强的判断力和丰富的经验;而且,那些被淘汰掉的通常都是最危险、最耗费人力的工作,如用手工把熔化的钢水倒入钢锭模具中。19世纪80年代,一个来访的英国小组评论说,美国的炼钢工人“必须留心记住操作指南,而且在操作控制杆时动作必须要快……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像英国工人那么繁重。”工作虽然变得简单了,但是即使使用已有的工匠,新的流程模式也使工厂不得不损失大量的动力。现在工厂里所需的技术都是由雇主发明并控制的,所以工人不用再当上好几年学徒才能掌握这些技术。在美国的工厂里,新工人接受培训的时间非常短,这让上文所说的那些英国来访者感到非常吃惊;卡内基的一个主管曾声称,只用六到八星期的时间,他就能够把一个来自农场上的孩子培训成为一个熔炼工——这在以前是一个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岗位。整体化的运营也抹掉了内部合同的最后一丝残迹。对生产线上的雇佣工人来说,他们的直接上级也是雇员,这样,他们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就拉大了。一个劳工历史学家把这一转变总结为“从工匠到工人的转变”。
新的工厂模式激发工会组织迈出了走向产业工会的第一步;“一个钢厂的工人”成了一个比“铁水搅拌工”更加重要的范畴,所以旧的、以工匠为基础的工会组织分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19世纪70年代,类似“劳工骑士”之类的组织大量涌现也是这种冲动的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1886年,在干草市场广场爆炸案之后,这些组织都跨台了——这个爆炸案是极度压抑和自身组织瓦解的一个牺牲品。(干草市场广场位于芝加哥,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制造厂发生暴力对抗事件之后,这个广场上发生了劳工集会。制造爆炸案的人一直没有找到,但他很可能是芝加哥一个比“劳工骑士”成员更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个组织都参与组织了这次集会。七个警察在爆炸中丧生,但其中只有一个是在炸弹旁边被炸死的,其他的人都死于枪击,而且很可能是他们自己开枪打死的。)
在“劳工骑士”之类的组织崩溃之后,“合并钢铁工人”是当时出现的力量最强大的产业工会之一——但是它正式地声称只代表熟练技术工匠。1892年,“合并钢铁工人”组织与卡内基钢铁公司旗下的“宅地钢厂”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不仅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永久的污点——事件中死亡的人数可能多达35人——对于卡内基的人格和名声来说,也是一个造成损害的污点。从更长远来看,政府对“宅地钢厂”罢工工人的干预和镇压,以及两年之后对在芝加哥附近发生的、著名的普式卧车工人罢工进行的镇压是那么的毫不犹豫,那么得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它非常有效地压制了产业工会运动。在这两次罢工之后,受到恐吓的工人运动退缩成了小心谨慎的、以工匠为基础的组织——塞缪尔?冈珀斯[3]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直到1935年,约翰?L.刘易斯[4]才领导他的矿工们重新燃起了劳工事业之火。
宅地钢厂
劳工问题给卡内基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冲突。在当众发表一些奉承的言论之后,他累得直喘气;他不得不说一些能引发工人们鼓掌的话,即使这会使他背上虚伪的恶名。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他每年都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花上大约一半时间;在那里,他到处宣传自己拥有苏格兰宪章运动主义者的根源。他还购买了一小批“激进的”报纸,并且慷慨地为“激进事业”提供捐赠(“激进”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自由”)。当他开始发表文章广泛地维护劳工权利并反对那些蒙昧的、同样身为管理者的同事的时候,那些格莱斯顿式的改革家们赞扬他是开明的现代资本家的典范。的确,他们怎么能够反对一个天真而又大方的大亨优雅地大讲改革者的格言呢?下面是卡内基的一段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