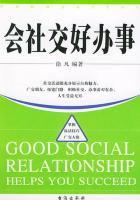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补充世界的人口。有些婚姻制度对此过于尽责,而有些又过于不足。本章对于性道德的讨论,就是基于这一论点。
在自然状态中,一只较大的哺乳动物需要相当大的区域才能维持生命。因此,大型野生动物的总数是很少的。牛和羊的数量虽然很多,但这是由于人的力量的缘故。人的数量是任何其他大型哺乳动物所无法比拟的。当然,这是由于我们有技能的缘故。弓箭的发明、反刍动物的驯化、农业的开发和工业革命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每平方英里人口的生存数。据统计,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多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人类智力用于发展人口超过用于任何其他单一目的。
诚如卡尔·桑德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口数量通常没有多大变化,19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增长实属极为例外的现象。我们也许会说,当埃及和巴比伦使用水利和农耕方法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纵观整个历史,这种情形大概是再没有了。对19世纪以前人口的计算都是推测的,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却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口的徒增是一种罕见和例外的现象。至于说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中人口又趋于稳定不变,这只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摆脱非常状态,又恢复了人类的一般习惯。
卡尔·桑德斯先生撰写过一部有关人口问题的着述,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指出,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区,自动控制几乎都在起作用;在保持人口稳定不变的问题上,这种自动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减少人口更有效果。在这里,他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例如,在印度和中国,人口所以不会徒增,似乎主要是由于死亡率高的缘故。中国固然缺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印度还是有的。在印度,人口出生率虽然很高,但人口的增长却比英国还要略微缓慢一些,卡尔·桑德斯先生本人也曾指出过这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婴孩的大量死亡、瘟疫和其他严重疾病所致。我相信,假如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统计数据,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然而,除了这些重要的特殊情况之外,卡尔·桑德斯先生的理论总的说来无疑是正确的。人们使用过各种限制人口的方法。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屠杀婴儿,在宗教不加干涉的地方,这种方法得以极为普遍的应用。有时这种方法极得人心,以致人们在接受基督教时竟要求基督教不能干涉屠杀婴儿。杜克霍波人曾因拒绝参军而与沙皇政府产生冲突,其理由是,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接着他们又与加拿大政府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赞成屠杀婴儿。当然,其他方法也是很普遍的。在许多民族中,女人不但在怀孕期间,就是在哺乳时也不能有性交活动,这种状况往往要持续两三年。这无疑会极大地限制住女人的生殖能力,尤其是在野蛮民族中间,因为他们要比文明民族衰老得快得多。澳大利亚的土着居民实行一种极为痛苦的手术,这种手术能够极大地破坏男性的生殖能力,从而达到限制生育的目的。我们从《创世纪》中了解到,在古代至少有一种明确的控制生育的方法为人们所熟知和实行,然而犹太人不赞成这方法,因为他们的宗教是反马尔萨斯的。通过这些方法,人类避免了因繁殖过快而引起的饥荒,于是也就避免了灭顶之灾。
尽管如此,在减少人口一事上,饥荒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非常原始的条件下,饥荒的影响也许并不像在一个不很发达的农业社会中那样大。1846年至1847年,爱尔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从那以后,爱尔兰的人口就再也没有达到过饥荒前的水平。在俄国,饥荒是屡见不鲜的,1921年的那次饥荒我们每个人都至今记忆犹新。1920年我在中国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闹饥荒,其严重程度和第二年发生在俄国的饥荒不相上下,但是中国灾民所得到的同情要比伏尔加灾民所得到的少得多,因为他们的厄运不能归咎于共产主义。以上事实表明,人口的增长有时确实会达到,甚至超过粮食的极限。然而,这主要发生在那些粮食突然而猛烈减少的地区。
凡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区,基督教总是要取消一切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只有节制性欲除外。屠杀婴儿那是自然要禁止的,人工流产也是要禁止的,而且一切避孕措施都是要禁止的。的确,那些牧师、僧侣和修女都是信守独身主义的,但是我认为,在中世纪欧洲,这些人的数目并没有现在英国的未婚女子多。因此,他们在控制人口增长一事上并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和古代进行比较,那么中世纪因饥荒和瘟疫而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恐怕要更大些。当时,人口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在18世纪,人口的增长率只是稍有上升,但是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统计,1066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平方英里有26人,1801年,人数增加到153人,1901年,人数又增加到561人。这样,19世纪期间的人口增长要比从诺曼人掠夺时期到19世纪开始时的人口增长快了将近四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因为在此期间,不列颠民族正在掠夺以前为少数野蛮人居住的大块领地。
人口的增长与出生率的增长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人口的增长应归因于死亡率的减少,而死亡率的减少,一部分是由于医学上的进步,但更主要的,我认为,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1841年英国开始记载人口出生率时起,到1871年和1875年止,出生率几乎是稳定不变的,后期曾达到35.6%的最高点。在此期间,发生过两起重大事件。第一起是,1870年颁发了教育条例,第二起是,1878年,布雷德洛对宣传新马尔萨斯学说一事提起公诉。因此,从这时起,出生率开始下降,起初很缓慢,后来就变成灾难性的了。教育条例是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因为孩子不再是有利的投资了,而布雷德洛则提供了造成这种情形的手段。1911至1915这5年期间,出生率下降到23.6%。1929年第一季度,出生率竟一落而为16.6%。英国人口虽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已开始缓慢增长,但很快就会达到静止不变的程度。众所周知,法国人口早已处于不变之状。
在整个西欧,出生率下降是相当普遍且极迅速的。只有类似葡萄牙那种落后的国家不在此列。出生率下降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为明显。最初,这种情形只存在于富人当中,但现在已蔓延到城市和工业区的各个阶层。穷人中间的出生率要高于富人中间的出生率,但是如果把现在伦敦最贫困区域的出生率和十年前最富裕区域的出生率做一番比较,前者要比后者低得多。众所周知(虽然有些人不肯承认),这是由于人工流产和使用避孕法的缘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种保持人口稳定不变的方法会停止使用。这种方法很可能会继续使用下去,直到人口开始减少,而且最终可能导致,我们不敢断言,大多数文明民族的灭绝。
要想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产生良好效果,就必须明了我们的目的何在。在经济技术的任何特定状态中,都存在着卡尔·桑德斯所说的最佳人口密度,即能使每个人获得最高收入的密度。如果人口低于或高于这个密度,经济福利的基本水准就会降低。总的说来,经济技术每提高一步,最佳人口密度也会随之提高。在狩猎时代,每平方英里一人比较适宜,而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每平方英里数百人也没有过多之虞。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自欧洲战争以来,英国已有人满之患。
我们不能说法国也有同样情形,更不能说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法国或任何西欧国家也许都不会由于人口的增长而提高它们的平均收入。因此,从经济角度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人口增长。那些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往往出于国家军国主义的动机,所以他们所希望的人口增长是不会持久的;因为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这种愿望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这些人的真实立场是,与其用避孕法去控制人口,那还不如通过战场上的死亡来实现这一目的。凡是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断然不会持有这种观点,所以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纯属糊涂到了极点。撇开与战争有关的那些论点不谈,我们高兴地看到,控制生育的方法正在使文明国家的人口趋于稳定不变的状态。
然而,如果人口真的减少下去,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人口不加控制地一味减少意味着人类最终灭绝,而我们是不会希望看到那些最文明的民族从世界上消失的。因此,我们只有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避孕法的使用限制在能够保持现有人数基本不变的范围内以后,才能大力提倡使用避孕法。我认为,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困难。人们限制家庭发展的原因,虽然不是全部;是经济上的,因此,通过减少孩子的费用,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使孩子成为父母的收入来源,人口出生率就会提高。然而,在现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上,这种做法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它会被用做保证军事优势的手段。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各主要军事国家都在武装民族中加上以“大炮必须有炮灰”为口号的繁殖民族,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这样,如果我们希望文明能够存在下去,我们又绝对需要一个国际政府了。这样一个政府若想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发布条令,限制一切军事国家增加人口。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对峙可以证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日本人口增长得极为迅速,而澳大利亚人口(移民除外)却增长得相当缓慢。这种情形造成了极难缓和的对峙情绪,因为双方争执的时候都有各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欧的出生率在短期内不会引起人口增长,除非各国政府采取确实措施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只要那些军事大国存在,其他国家就不可能仅仅依靠生育来改变力量对比。因此,任何一个想要顺利履行自己职责的国际权力机构都必须重视人口问题,并且坚持在那些不顺从的国家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舍此,世界和平就无法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