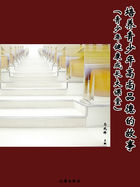天明了,白白的阳光空空地染了全室。
我们快穿衣服,折好被子,平结他自己的鞋带,我结我的鞋带。他到外面去打脸水,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气愤地坐在床沿。他手中的水盆被他忘记了,有水泼到地板。他问我,我气愤着不语,把鞋子给他看。
鞋带是断成三段了,现在又断了一段。他重新解开他的鞋子,我不知他在做什么,我看他向桌间寻了寻,他是找剪刀,可是没买剪刀,他失望地用手把鞋带做成两段。
一条鞋带也要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一条鞋带。
他拾起桌上的铜板说:
“就是这些吗?”
“不,我的衣袋还有哩!”
那仅是半角钱,他皱眉,他不愿意拿这票子。终于下楼了,他说:“我们吃什么呢?”
用我的耳朵听他的话,用我的眼睛看我的鞋,一只是白鞋带,另一只是黄鞋带。
秋风是紧了,秋风的凄凉特别在破落之街道上。
苍蝇满集在饭馆的墙壁,一切人忙着吃喝,不闻苍蝇。
“伙计,我来一分钱的辣椒白菜。”
“我来二分钱的豆芽菜。”
别人又喊了,伙计满头是汗。
“我再来一斤饼。”
苍蝇在那里好像是哑静了,我们同别的一些人一样,不讲卫生和体面,我觉得女人必须不应该和一些下流人同桌吃饭,然而我是吃了。
走出饭馆门时,我很痛苦,好像快要哭出来,可是我什么人都不能抱怨。平日他每次吃完饭都要问我:
“吃饱没有?”
我说:“饱了!”其实仍有些不饱。
今天他让我自己上楼:“你进屋去吧!我到外面有点事情。”
好像他不是我的爱人似的,转身下楼离我而去了。
在房间里,阳光不落在墙壁上,那是灰色的四面墙,好像匣子,好像笼子,墙壁在逼着我,使我的思想没有用,使我的力量不能与人接触,不能用于世。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平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
他回来,只是自己回来,不带馒头或别的充饥的东西回来。
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着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你肚疼吗?”我说不是,他又问我:
“你有病吗?”
我仍说不是。
“天快黑了,那么我们去吃饭吧!”
他是借到钱了吗?
“五角钱哩!”
泥泞的街道,沿路的屋顶和蜂巢样密挤着,平房屋顶,又生出一层平屋来。那是用板钉成的,看起来像是楼房,也闭着窗子,歇着门。可是生在楼房里的不像人,是些猪猡,是污浊的群。我们往来都看见这样的景致。现在街道是泥泞了,肚子是叫唤了!一心要奔到苍蝇堆里,要吃馒头。桌子的对边那个老头,他唠叨起来了,大概他是个油匠,胡子染着白色,不管衣襟或袖口,都有斑点花色的颜料,他用有颜料的手吃东西。并没能发现他是不讲卫生,因为我们是一道生活。
他嚷了起来,他看一看没有人理他,他升上木凳好像老旗杆样,人们举目看他。终归他不是造反的领袖,那是私事,他的粥碗里面睡着个苍蝇。
大家都笑了,笑他一定在发神经病。
“我是老头子了,你们拿苍蝇喂我!”他一面说,有点伤心。
一直到掌柜的呼唤伙计再给他换一碗粥来,他才从木凳降落下来。但他寂寞着,他的头摇曳着。
这破落之街我们一年没有到过了,我们的生活技术比他们高,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从水泥中向外爬。可是他们永远留在那里,那里淹没着他们的一生,也淹没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但是这要淹没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条狗,和别的狗一样没有心肝。我们从水泥中自己向外爬,忘记别人,忘记别人。
1933.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