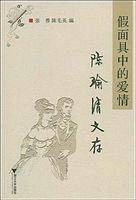上午十时左右
阳光似金花一般撒满人间。春天之使者似在各处舞跃:云间,树上,流动的河水中,还来到人类的各个底心内。在采莲底家里,病的孩子稍稍安静了,呼吸不似以前那么紧张。妇人坐在床边,强笑地静默想着。半空吊起的心似放下一些了。萧涧秋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女孩是在房内乱跑。酸性的房内,这时舒畅不少安慰不少了。
忽然有人走进来,站在他们底门口,而且气急地——这是陶岚。他们随即转过头,女孩立刻叫起来向她跑去,她也就得慢地问:“小弟弟怎么样?”
“谢谢天,好些了,”妇人答。
陶岚走进到孩子底身边,低下头向孩子底脸上看了看。采莲的母亲又说:“萧先生用了新的方法使他睡去的。”
陶岚就转头问他,有些讥笑地:“你会医病么?”
“不会。偶然知道这一种病,和这一种病的医法,——还是偶然的。此地又没有好的医生,看孩子气急下去么?”
他难以为情地说。陶岚又道:“我希望你做一尊万灵菩萨。”
萧涧秋当时就站起来,两手擦了一擦,向陶岚说:“你来了,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呢?”一个问。
“她已经知道这个手续,我下午再来一趟就是。”
“不,请你稍等片刻,我们同回去。”
青年妇人说:“你不来也可以。有事,我会叫采莲来叫你的。”
陶岚向四周看一看,似侦探什么,随说:“那么我们走罢。”
女孩依依地跟到门口,他们向她摇摇头就走远了。一边陶岚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除出学校还有别的地方吗?”
“慢些,我们向那水边去走一趟罢,我还有话对你说。”
萧涧秋当即同意了。
他慢慢地抬头看她,可是一个已俯下头,问:“钱正兴对你要求过什么呢?”
“什么?没有。”
“请你不要骗我罢。我知道在你底语言底成分中,是没有一分谎的,何必对我要异样?”
“什么呢,岚弟?”
他似小孩一般。一个没精打采地说:“你运用你另一副心对付我,我苦恼了。钱正兴是我最恨的,已经是我底仇敌。一边毁坏你底名誉,一边也毁坏我底名誉。种种谣言的起来,他都同谋的。我说这话并不冤枉他,我有证据。他吃了饭没事做,就随便假造别人底秘密,你想可恨不可恨?”
萧这时插着说:“那随他去便了,关系我们什么呢?”
一个冷淡地继续说:“关系我们什么?你恐怕忘记了。昨夜,他却忽然又差人送给我一封信,我看了几乎死去!天下有这样一种不知羞耻的男子,我还是昨夜才发现!”她息一息,还是那么冷淡地,“我们一家都对他否认了,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说,叫他勇敢地向我求婚呢?为友谊计?为什么呢?”
她完全是责备的口气。萧却态度严肃起来,眼光炯炯地问:“岚弟,你说什么话呢?”
一个不响,从衣袋内取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一处清幽的河边,新绿的树叶底阴翳,铺在浅草地上。春色的荒野底光芒,静静地笼罩着他俩底四周。他们坐下。他就从信内抽出一张彩笺,读下:
亲爱的陶岚妹妹:现在,你总可允诺我底请求了。因为你所爱的那个男子,我和他商量,他自己愿意将你让给我。他,当然另有深爱的;可以说,他从此不再爱你了。妹妹,你是我底妹妹!
妹妹,假如你再还我一个“否”字,我就决计去做和尚——自杀!我失了你,我底生命就不会再存在了。一月来,我底内心的苦楚,已在前函详述之矣,想邀妹妹青眼垂鉴。
我在秋后决定赴美游历,愿偕妹妹同往。那位男子如与那位寡妇结婚,我当以五千元畀之。
下面就是“敬请闺安”及具名。
他看了,表面倒反笑了一笑,向她说,——她是忿忿地看住一边的草地。
“你也会为这种请求所迷惑吗?”
她没有答。
“你以前岂不是告诉我说,你每收到一种无礼的要求的信的时候,你是冷笑一声,将信随随便便地撕破了抛在字纸篓内?现在,你不能这样做吗?”
她含泪的惘惘然回头说:“他侮辱我底人格,但你怎么要同他讨论关于我底事情呢?”
萧涧秋这时心里觉得非常难受,一阵阵地悲伤起来,他想——他亦何尝不侮辱他底人格呢?他愿意去同他说话么?而陶岚却一味责备他,正似他也是一个要杀她的刽子手,他不能不悲伤了!——一边他挨近她底身向她说:“岚弟,那时设使你处在我底地位,你也一定将我所说的话对付他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明了你底人格,感情,志趣。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的,深深地相信你的。不过你不该对他说话。他是因为造我们底谣,我们不理他,才向你来软攻的,你竟被他计谋所中吗?”
“不是。我知道假如你还有一分爱他之心,为他某一种魔力所引诱,你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叫他向你求婚的。何况,”他静止一息,“岚弟,不要说他罢!”
一边他垂下头去,两手靠在地上,悲伤地,似乎心都要炸裂了。陶岚慢慢地说:“不过你为什么不……”她没有说完。
“什么呢?”
萧强笑地。她也强笑:“你自己想一想罢。”
静寂落在两人之间。许久,萧震颤地说:“我们始终做一对兄弟罢,这比什么都好。你不相信么?你不相信人间有真的爱么?哈,我还自己不知道要做怎样的一个人,前途开拓在我身前的又是怎样的一种颜色。环境可以改变我,极大的漩涡可以卷我进去。所以,我始终——我也始终愿你做我底一个弟弟,使我一生不致十分寂寞,错误也可以有人来校正。你以为不是吗?”
岚无心地答:“是的,”意思几乎是——不是。
他继续凄凉的说:“恋爱呢,我实在不愿意说它。结婚呢,我根本还没有想过。岚弟,我不立刻写回信给你,理由就在这里了!”停一息,又说:“而且生命,生命,这是一回什么事呢?在一群朋友底欢聚中,我会感到一己的凄怆,这一种情感我是不该有家庭的了。”
陶岚轻轻地答:“你只可否认家庭,你不能否认爱情。除了爱情,人生还有什么呢?”
“爱情,我是不会否认的。就现在,我岂不是爱着一位小妹妹,也爱着一位大弟弟吗?不过我不愿意尝出爱情底颜色的另一种滋味罢了。”
她这时身更接近他的娇羞地说:“不过,萧哥,人终究是人呢!人是有一切人底附属性的。”
他垂下头没有声音。随着两人笑了一笑。
一切温柔都收入在阳光底散射中,两人似都管辖着各人自已底沉思。一息,陶岚又说:“我希望在你底记忆中永远伴着我底影子。”
“我希望你也一样。”
“我们回去罢?”
萧随即附和答:“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