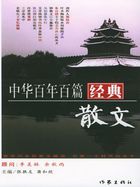你一定见过一棵树,一棵普通的树。在行走或是发呆的过程中,一棵树会使你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
或许是在你家楼下,一个小花园中,或许是在喧闹的路旁。那里都不只是一棵树,十几棵或是几十棵同样的树。但你只看到了一棵树,这是心灵的选择。你的眼神认得它每一片叶子的脉络。
我遇见过这样的树。我和它既是路人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朋友。那么多次我从它身边走过去了,晚霞中,晨曦里,我留下的脚印逐渐变大,影子被拉长,时光在一层层地消磨过去。它的枝干变成了一个纸杯的粗细,每一片叶都披上了厚重的叹息声。一棵树不必知晓它的性别,这样省去了不少麻烦。它的年龄都是模糊的数字,我只记得自从搬来新家的那天,它便在这里了,那时还像个小孩子,细细的腰杆儿有些弱不禁风的意味,甚至连绿色的资本都如此相形见绌。可它还是一棵树,只是默不做声地成长。
我们擦肩而过无数次。一个人和一棵树的会晤,不会有更多的故事。但我们小心地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有一根银色的细线牵在我们的灵魂之间,我们都不敢去触碰,生怕不小心毁坏了这秘密般的美好。
有一天夜里,星色正好,镶嵌在空中像是波斯猫的眼仁儿,大块儿的墨云像是被细心裁剪过的拼布图案。我从学校归家,有些疲惫。那棵树在风中左右摇摆,翠绿的发丝翻卷在半空中。我走上前去抚摸它的枝干,只是朋友间默允的打招呼方式。这里比我想象的更粗糙一些,在指尖划过一缕一缕隽着暗芳的暖风。这没有指纹的风,更看不见它的面庞。过去的夜晚它也曾经这样迈着小碎步行走在树的皮肤上。我不知道风它有没有人类惯用的握手方式,它和树每天的见面机会很多,但它们的心灵间的默契舛讹百出。
安静的树,在我的面前没有语言。或许是我不懂它的语言,是“沙沙沙”地歌唱吧。想到这里我有些黯然,这里的每一株草每一朵花都能够明白的语言,我却不懂。
春天到了,这棵树上结了许多粉嫩的花骨朵儿。春风一吹便骄傲地伸展腰身了。每一朵花都有快乐的神情,它们从花瓣中溢出的桃红色香气,在树的周围轻轻地跳着一曲又一曲的舞蹈。我拿了相机下楼拍照,是去拍那棵树开花的样子。
又一阵风吹过了,这是不让人快乐的风,彻底打乱了树安逸的遐想。树枝上粉色的花瓣雨飘落下来,像是大自然中真正的雨水,因为它们不消几日便无踪迹,幸运的人偶尔只在微微泛潮的泥土中看到一些淡粉的脑袋。我是一阵风中的过客而已,确切些说风是我身边的过客,分明是它去,我留。树的喜怒哀乐只能匆匆地敷衍了事。
我们有些伤心,只冲对方无力地摆摆手。从搬进新家来的那天,至此已有四年的时光。我的头发已留得很长,院子里住进了不少新的树苗,我认识的那棵树再去同它们相比,显得壮硕多了。
这阵风过后,我和这棵树的个子突然长高了。那时,也是春天将尽未尽的时节。我们兴奋地又唱又跳。树站在原地露出微笑的表情,去年在它身上安家的麻雀家族又添了新的子孙,一家老小唧唧喳喳地絮叨着家长里短。
我为花草、鸟兽和雨露,都写过记录的文章。现在我又提笔,去写一写院子里的那棵树。确切些说,它是值得我多费些笔墨的。因为有那么一天,我走到了树的跟前,就像是打量交往了很久的老友了,我们不用语言的交流,而是在心里:“你长大了,比我来之前高大多了!”我笑着说。“你也一样,但我看得出,你的童心依旧,像画纸上的太阳不会落下。”那棵树真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