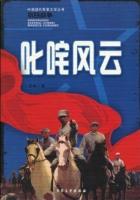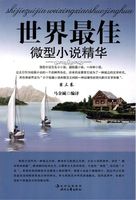终于有一天,茧子宣告:“我明天回去。”不是因为父母唠叨,也不是佑辅催促,而是千花打电话来了。
“预产期那天本想打电话给你,后来一想,不知道你会不会正在生,所以忍住了。后来瞳说,应该生完了吧,可以打打看。所以我才打的。生孩子很辛苦吧?对了,是男孩还是女孩?”话筒那端兴奋的声音,有如暑假没见到面的知己好友般令她怀念。茧子告诉千花,是女儿,名字叫怜奈时,千花发出一点也不像两个孩子妈的尖叫声。
“哇——是女儿,跟我的一样!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快点让我们看看怜奈嘛。我们大家一起去上次你说的那家照相馆好不好?好期待啊。真的呀,是女儿啊!”
“可是啊——”听到千花的声音,她开始想早点回东京,像以前那样出去野餐,或是到谁家集合,但是茧子带着撒娇的声音,道出自己回东京一个人照顾孩子的忧虑。
“哎哟,你说什么呀,你哪会是一个人?还有我和瞳、容子在呀。如果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过去呀。而且我妈妈家很近,我妈也可以尽量使唤。”千花在话筒那端,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那,我过几天就回去。回去之后再打电话给你。”茧子说完,一挂上电话,马上走到客厅宣布:
“妈,我明天回去。”
佑辅说,如果是周末的话,他可以来接。但茧子还是如她所说,在千花来电的隔日,用快递将行李运回东京,自己则抱着怜奈,坐上去上野的电车。
抱着上个月还没出生的孩子坐电车、换电车、坐地铁,对茧子而言是场大冒险。她担心怜奈在拥挤的人群中哭起来时,自己会吓破胆,也害怕怜奈会不会像蛋糕一样被挤烂。宝宝背带越来越沉重,虽然将近穿外套的季节,但她还是走得满身大汗。下了地铁、走上地面的时候,怀念和安心的感觉让她差点当场跪下去痛哭。
就因为如此,当她在大楼门口遇到六楼的夫人时,虽然说不上认识,却也油然生出想朝她奔去的心情。而且一向只对她礼貌问候的夫人,竟亲热地靠过来,一脸惊奇地说:
“咦?繁田太太,这是你的宝宝吗?”
茧子忍不住憋起脸,把对方当成千花或瞳一般哭诉:“才刚生的。我今天第一次一个人带着宝宝搭电车。”
“哦,那很辛苦的吧。一个人带呀,真了下起。宝宝也是第一次出门吧?好可爱啊,是女孩吗?”
夫人整个脸都在笑,她用食指碰碰怜奈的小手。茧子曾模糊地想过,永远都会摆出少奶奶姿态、全身上下时髦得无可挑剔、太接近她就会态度僵硬的夫人,一定与自己是不同世界的人吧。然而,她现在却是那么温柔,望着夫人明亮、灿烂的侧脸,茧子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啊,完蛋了,刚一察觉,两行泪水已从眼中潸然而下。啊,完蛋了,她一定会觉得我是个怪女人,为什么要哭呢,不准哭、不准哭!可是心里越是这么想,越是紧张,泪水便不断地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