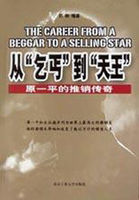他的脸上恐惧之情更甚,浑身几乎都战栗着,道:“只见得四处是全副武装的禁军,领头一人振臂高呼,国主驾崩,明王英明,当为新主等语。下官一细看,那人却是统领付将军,拥着明王,直朝禁城而来……”
她闻言,浑身一震。哑然道:“当真。”
赫先政连连点头,几欲哭出来。连连道:“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他的声音苍老急促,静夜听来,仿佛天降灾祸,挟裹着无限多的惊惧,已经洪水般便要淹没过来。一干宫人自茫然间回过神来,便都个个没了六神,胆小些的,已经哭出声来。
鄂多更是几步抢至慕容璨身侧,摇撼着他,唤道:“国主,国主。醒一醒,出大乱子了。”
慕容璨还自躺在椅上,一颗头颅随着他动作左右摇来摇去,只无动于衷。
赫先政喃喃道:“国主酒醉,下官方才又用了那安神之剂,一时半刻恐难醒来。”
鄂多见状,更慌乱了。哭丧着道:“我的主上,您好选不选,偏选这等时候醉酒。这可如何是好。”
她回头看去,见他还自无知无识的沉睡,日间时常拧在一处的两道剑眉,而今倒微微舒展了些。笔挺的一管鼻子,口唇俱褪了血色,只一种苍白。更显得他一张脸,倒有种略带病态的俊美。实则他关上他睥睨世间的眸子,放低他万乘之尊的身段,也就是一世间寻常的男子。亦会失意,会痛苦,会失算。有着“人”这样物种的缺点。
她注视他极短的一会儿。忽然喝道:“静下来。”
她一把女声,娇脆清晰,却不知为何,此刻便带了一种断然的命令之势,生生将一室大难临头的慌乱吵杂压将下去。众人果真定下来看住她。
她转过身,挺一挺腰杆。吩咐道:“都打起精神,听我调派。”
“鄂多,你领着人,先将国主抬至后园花房。”
鄂多哀哀道:“娘娘,后园有何用……”
她打断他:“照我吩咐去。”
众人虽狐疑,却不敢怠慢,本是极训练有素的,当下抬起慕容璨,果到了花房。
她寻着着一壁绿障,爬满了藤蔓,花页在风中欢快的摇曳。命人移开那三只硕大的兰花盆子,趋向前略看了看。道:“把那石板掀了。”
侍从依言照做。
石板后赫然是一溜的石阶。一条黝黝甬道,直通往地底未知之处。她顾不得向众人解释这甬道由来。
便道:“明王既反,禁城定已是四下围死。此道可出城外。尔等前去,全速护送国主出城,务必寻一隐秘处安置。赫先政。”
赫先政此刻已稍稍恢复常态,忙躬身道:“下官在。”
“你跟在国主左右,若半路出甚状况,好生照看。”
“是。”
“鄂多。”她取下袖中金牌,道:“若出了城,你先差一人,速速前往驻军大营寻陈修贤将军。将此金牌面示于他,告知始末。道是我旨意,命他火速前去护驾。”
鄂多应了。
她仰起头,目视莽莽夜空,叹息道:“愿皇天庇佑。”
随即低下头来。冲鄂多缓缓道:“国主藏身处,切不可予他人知道。”鄂多慎重道:“老奴识得。”
她稍一迟疑,接着道:“谁前去送金牌传旨。”
侍从中一年纪轻的,行礼道:“奴才年轻,跑得快。愿往。”
“好。”她看着那侍从,语气却显出一种苍凉凝重来,“若你送信有功,日后定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若果天道不仁,陈将军亦反了。那么你起个誓,便是死。也不能透露国主踪迹。”
那侍从果噗通跪到地上,斩钉截铁的起了一誓。
“鄂总管,若至天亮,发现形势未变,便请速回泰和,另谋他计。鶻孜社稷江山千钧重担,今夜便在尔等几人肩上了。万望诸位莫负国主往日恩典,今日便将国主托付诸位了。日后论功行赏,自不必多说。”
鄂多此刻才察觉出来,不由问:“娘娘您呢。”
她倒笑了笑,道:“我还能如何,定然得守在前头。拖得一时是一时。”
浅香闻言,不由尖声道:“娘娘。……“
她抬了抬手,示意她噤声。冲他们道:“事不宜迟,速去。”
今夜倒没有月亮,后园花木扶疏,她头顶是漆黑无边的天。灯光打在她脸上,猛然一看,倒有一种朦胧的光晕。衬得她便似天人一般。
鄂多不由老泪纵横,道:“请娘娘受老奴一拜。愿娘娘洪福齐天,逢凶化吉。”
果跪下去咚咚咚扣了几个响头。一折身,领着人架起慕容璨,便入了秘道。
众人又将花盆按原样恢复了。看上去,便同日常无异。
她回至前厅,便唤浅香:“不拘甚么热热的吃食,替我拿一些来。”
“取我妆夹披戴。”
“将这正殿一应门窗俱开了,将所有灯烛全部点上。”
众人已唯会听她号令。一时脚步匆匆,不一刻,便办妥了。
她便于大殿正中坐定。道:“都给我镇定些。听我差遣行事。”
一阵踏步人声交错吵杂由远渐近,不一刻,便到了跟前。四围将这正殿团团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