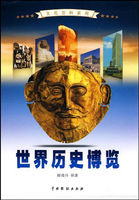这一刻,他从他万众景仰的御座上走下来,摒弃世间的的一切君臣尊卑之念,放低他的万乘之尊,谦恭而诚恳的,渴望得到她的回应。
灯火远了,人声远了,家国天下,外间的纷纷扰扰,尽皆去得极远。山川庄严肃穆,只如都在俯首聆听。她的心,忽然间变得说不明的柔软,一种平静安宁,仿佛已尽溢满,又仿佛仍空空如也。
恍惚间,竟是极愿意沉溺其中。
鄂铎在远处候着,初初见他二人还颇有交谈。眼下只见他们四目相对,也不言语了。说含情脉脉吧,明明又相隔甚远,且各据亭中一角,只一动不动。
另一近侍似也看出异样来,凑近他耳边,轻声道:“您瞧瞧,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光线太暗,看不到他们脸上的神情。鄂铎徒劳的将头往前伸了伸,喃喃道:“没看明白。”
那近侍摇一摇首,又道:“阿弥陀佛,别又是敏妃娘娘倔劲儿上来了,她这一使性子,奴才们可又有十天半月没好果子吃了。”
鄂铎正凝神往那亭中看去,闻言随口答道:“可不就是。”
那近侍一听,便拧眉道:“您瞧这敏妃娘娘,一枝柳条儿而似的,风吹吹就飘了,真不明白她哪里来那胆子。不过怪就怪在咱国主就吃这一套。您别说,还真是一物降一物。”
鄂铎见他洋洋自得,越说越远,忙回手重重的在他头上敲了一记,狠狠道:“你小子别是不要命了。嚼什么嘴。”
那侍从啊呜一声,抱了头,不敢再作声。
鄂铎见他二人仿佛着了定身法一般,仍自站那不动。一时间不知是福是祸。情急之下只得接了旁边一盏宫灯,亲拿了两件披肩,屏息静气走过去,远远的回道:“夜间风大,奴才给国主及娘娘送件披的。”
只感觉慕容璨朝他看了看,低声道:“偏只你是个周到的,难得这山间风气清凉,今夜又有繁星满天,你倒要弄件东西来挡住。”
鄂铎听得他实并无责怪之意,倒仿佛还隐隐有些调侃。一颗心方落了地,高声道:“奴才该死。”
忙退了下去。
那侍从见他回来,忙过来探询。
只见他抬首望了望天,自言自语道:“凭这稀落几个星子,也好算繁星?”
过许久,他才遥遥伸出手,她缓缓走了过去,将自己的手交至他掌中。他轻轻纂住,道:“你真觉得这山上好?”
她点点头。
他笑道:“那你就姑且在这山上住些时日吧。等我得闲了的时候。也上来住着,咱们一处儿,只陪着太后。避开那一堆子人,也清静。”
她看了看他,道:“好。”
他又道:“你今天倒是惜字如金。那伶牙俐齿都到哪里去了。”
她垂下眼睛,但笑不语。
他一瞬不瞬的看住,似有感叹道:“那日大同关外,我置身帐中,亲见你一身嫁衣,穿过校场的千军万马,款款而来。随从皆战兢不已,独独你,强自镇定,面上一种视死如归之气。先前我还颇有忧虑,那刻才放了心。”
她奇道:“何忧之有?”
他轻笑:“怕女大十八变,你若变了无盐可如何是好。”
她看他一眼,道:“国主饱读圣贤之书,难道竟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他不以为意,道:“你是不知。当日我在暗处,你在明处,看的真切。自你一下车驾,营房上下数万只眼睛,齐齐聚于你一处,你一身华裳,只仿佛一片云霞似的,飘飘而至。”他微微哼了声,道:“那许多人,可不见得有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