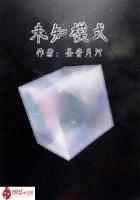刘柱来了,风尘仆仆。
他先是对我说了一通县里工作可以把活人累死死人累活的话,然后依旧拿我开涮,“还是你们省里领导快活,不晒太阳,不下田头。你看我黑得跟孔繁森像弟兄。”我说,“你总是往英雄人物上靠,其实我比孔繁森还黑,你为什么不说晒得跟我一样黑呢?”这时天色将晚,镇政府领导班子已经在“桂花厅”恭候了,刘柱说,“好了,我们先去吃饭!晚上陪你聊天。”我说我们简单吃一点就行了,反正我的伙食费可以回去报销。刘柱说,“今晚上吃的全是家常菜,不然你还不知道我们有多腐败呢。”
我被生拉硬扯地拖进了“桂花厅”,席间大家还说了不少民间歌谣,范中康说他最近又听到一个《当官难》的顺口溜,老百姓说“有钱我不求你,守法我不怕你,有事我要找你,不办我要骂你,办不好老子还要告你”。范中康说现在领导真不好当了,刘柱说,“这就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我们以前把主仆关系都颠倒了。”大家见刘县长这样说,也就跟着附和。范中康向我敬了两杯酒,他说,“这次来,照顾不周,还望多多包涵!”我说,“我已经够骚扰你们的了。”说话越来越客套,越来越虚假,那些说与不说一个样和说了就忘的话刺激着他们拼命喝酒。我以有病在身拒绝喝烈性酒。酒喝多了,话也就无所顾忌了起来,范中康又敬了我一杯,“你的反腐败报道在全省是赫赫大名,如果我们有什么腐败的话,还望你当面提出来,一弄成报道,白纸黑字,这以后工作就干不下去了。”
刘柱打断范中康,“老范,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同学这次来不是为了拆我台的,你再自罚一杯酒!”范中康很困难地摇摇晃晃站起来,自己一仰脖子倒进了满满一杯白酒,他抹着嘴角的残酒对我双手抱拳,“冒犯了,还望老弟恕罪!”
酒后,我和刘柱来到了他的套间。他先是跟我一起聊起了大学里的许多同学的爱情故事,我们在回忆中感情逐渐接近了十几年前我们的那间学生宿舍,十几年前的影子在我们的情绪中纷纷复活。
刘柱说着说着就绕到了这么多年来同学们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中,他说,“我们俩能混到今天都不容易,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珍惜。”
我说,“你要珍惜,我已经没什么可珍惜的了,或者说珍惜也没什么意义了。”
刘柱将外套脱下来,他捋着头上越来越少的头发,说,“我看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你也没必要那么消沉。”
我有些吃惊,他好像已经知道我停职反省的事了。他说,“我岳父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他毕竟在省里还是有些影响力的,我前天去了省城,他说他一定会帮忙的。我的意思是,首先不能撤职,太伤面子了,其次即使调离的话,也要保留住处级政治待遇。”刘柱的岳父现在是省人大副主任。
我很是有些感动,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即使意志再坚强,但感情却是脆弱的,我感到了我在翻船后冰冷的大海上有人给我扔过来了一个救生圈,哪怕这个救生圈是坏的,他也足以让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我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因此,我感动飘过来的每一根稻草。
我一时没想出恰当的话来,只是说了声“谢谢”。
刘柱说,“我这个人的做人的原则就是,干实事,不坑人。我知道你也是这样的人,但你比我更嫉恶如仇,你是知道的,现在是社会转型期,问题很多,要是想查,到处都是问题,虽然省委组织部对我的考察是优秀,但我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看,用什么标准看。”
我急忙申辩,“我这次来,绝无调查你刘柱的任何意图和行动,我自己还在被调查呢。”
刘柱把眼光咬定我,“你当然不会调查我,但是你调查了陈小峰和范中康的问题,而且你还去了偶然出车祸的钱成刚家里。你这让我怎么说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钱成刚家的?”
刘柱说,“这你就不要问了,你让我在下级面前很没面子,人家说我是被老同学暗算了,而我对你的行踪居然一无所知。你应该知道,当年你在学校出了那档子事,有同学嫉妒你平时出足了风头,关键时刻落井下石,但我没干。”
我说,“这一点我很清楚,跟你说实话,我也没调查,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主要是我听了一个死刑犯讲到在云台镇诈骗的事,我只是想知道是否属实。没有任何其他动机,所以我也没跟你说。我这次是来疗养的。”
刘柱说,“我们不说这些了,我完全相信你。”
晚上十点多钟,又有敲门声,刘柱将头伸到门外,没让门外的人进来。我听到一个温柔而抒情的声音轻轻地说“我来了”,这三个字还没说完就听刘柱声色俱厉地吼了一句,“你们搞什么名堂?”
刘柱关上门走进房间柔和的光线里,“真没办法!谁的门都敢乱敲。”
后半夜,窗外下了今年春天的第一场雷雨。我和刘柱坐在雷声中抽烟,烟雾以及我们的谈话在雷声中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