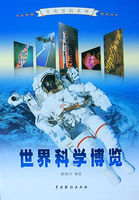在草原牧场上,我总会留意他们,这些可爱的孩子。
有时候,看着他们在黄昏金色的牧场上疯跑,仿佛看到童年的自己。
他们生在广阔的草原上。
狂野的白色风暴,黄昏金色的落日,万只黄羊过草场,这些他们都见过。
如风的骏马和凶悍的牧羊犬陪伴着他们成长,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将拥有一个更与众不同的世界。
我也曾经拥有那样的童年。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回忆生命中这段最美好的日子。
那是永难消退的记忆。
傍晚,白宝音格图赶着羊群回到营地时,并没有在勒勒车旁边的那块草原上看到鬼。
也许已经死了,他喃喃自语。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有一些淡淡的失望。
但他猜错了,当他骑着马走得越来越近时,阿尔斯楞突然从毡包后面跑了出来,一直冲到他的马前。
“爸爸,你猜!”
“猜什么?”被草原上的毒日头无遮无掩地整整晒了一天之后,白宝音格图此时只想扳鞍下马,走进毡房里盘腿坐下,喝上一碗消渴的热茶。他无法从阿尔斯楞的表情上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看。”阿尔斯楞以一位正在表演的著名魔术师拂开身上大氅的夸张动作转了个身。
“蒙恩!”他冲着毡包后面高叫一声。
在草原金色的黄昏中迸出一道耀眼的银色,最闪亮的银子。
雄壮的鬼眨眼之间已经跑到阿尔斯楞的身边。这已经不再是那头陷入死亡边缘的狗了,此时除了包扎过的左后腿还微微地有一点儿跛,怎么看这都是一头极其少见的英气勃勃的巨犬。
鬼狗稳稳地站住之后,注视着白宝音格图,那表情像是在看阿尔斯楞介绍给它的一位新朋友,或者阿尔斯楞只是让它看一看属于他的财产。
怎么看此事都有些令白宝音格图感到不可思议,蹲踞着的鬼比站立的阿尔斯楞还要高出半头。
他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头野兽一样的巨犬会对这个小矮人俯首帖耳。
而阿尔斯楞此时像一个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发出震天吼声穿越校场的将军,一副得意至极的神色。在确信已经在白宝音格图面前充分地炫耀了自己的狗之后,阿尔斯楞发出冲锋陷阵般尖厉的呼哨,冲开惊慌失措的羊群,向前跑去了。而这头银白色的巨犬,似乎在仅仅一天之间就恢复了体力,重又找回了那悍人的气势,摇曳着一身如银子般闪亮的长毛,紧紧地跟在阿尔斯楞的身后。
“这是我的狗了,我给它取的新的名字!”阿尔斯楞高喊着跑开了。
白宝音格图看着他们一起跑出了很远,在阳光中漂亮的剪影呈现出他们撕扯着打闹的轮廓,他们像是要在蜂蜜一样浓醇的阳光里融化了。
乌云从毡房里出来,将一碗酸奶渣倒在早晨放在鬼面前的那个盛粥的铁盆里。
那锅里的粥早已经被鬼吃得一干二净。
“怎么样?”看到走过来的乌云,白宝音格图询问。
“没怎么,早晨把那半盆粥都喝光了,当时看
来真的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是吃粥,中间还歇了一气儿。趴了一中午,头就抬了起来,下午我喂了它一点牛奶。我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和阿尔斯楞一起出去玩了。”
自从营地里那头牧羊犬莫名其妙地失踪之后,
白宝音格图一直没有机会去附近的营地寻找一头新的牧羊犬。年初在他捕获鬼时没有当时就杀死它,也是被这头狗硕大无朋的体形所吸引,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一头非常漂亮的牧羊犬啊。
阿尔斯楞和鬼还在黄昏的草原上嬉戏。在这
空茫的草原上,阿尔斯楞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玩伴。原来那头牧羊犬在阿尔斯楞还没有出生时就有了,在营地里比他的资格还老,说是陪他玩,不过是无奈地敷衍他吧。而鬼的出现却截然不同,是阿尔斯楞将这头受伤的狗带回家的,是他救了它。
鬼是他的狗。
阿尔斯楞高叫着扑向鬼,鬼左右躲闪着,虚张声势地咆哮,夹着尾巴逃窜。随后,鬼又迅速地转换角色,成为追捕者。鬼已经失去了最初的不安和羞涩,它无法控制自己在一种强烈情感的驱策下想要撕咬、想要狂吠、想要咆哮的冲动。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爆发,如果再不发泄出来,它就要爆炸了。
鬼是要杀了这个小小的人类的孩子,这个带给它温暖情感的孩子,它的神。
鬼狂吠着,挑起上唇,露出獠牙,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冲向阿尔斯楞。不要说撕咬,也许仅仅是撞在阿尔斯楞的身上,恐怕也要让他全身骨折。
但那只是一种游戏。
游戏,鬼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情感发泄的方式。游戏,一种为了快乐而进行的活动,以前还从来没有在鬼的世界里出现过。鬼正在学习,对于鬼来说是一种新奇的开始。鬼那像冰壳一样的世界正在开启一条窄窄的裂缝,而阳光正从这条仅有的裂缝里洒进来。
鬼那疯狂的气势令远远的毡房前向这边张望的白宝音格图紧张地拎起了靠在毡房门边的布鲁棒子。阿尔斯楞也许是吓呆了,并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但是像推土机一样跑得烟尘四起的鬼还是向阿尔斯楞冲了过去,就在要撞到阿尔斯楞的时候,白宝音格图已经拿起布鲁棒子向那边跑过去时,鬼却像一只羚羊一样,从阿尔斯楞的头顶一跃而过。
从白宝音格图的方向望过去,鬼正以劈头盖脸的气势压倒在阿尔斯楞的身上。
但是阿尔斯楞响亮的笑声让白宝音格图在一天之中第二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尴尬。
鬼只是从阿尔斯楞的头上跳了过去。
而白宝音格图气势汹汹的架势显然惊扰了阿尔斯楞和鬼,他们颇为惊诧地投来的目光让白宝音格图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于是他颇为艰难地挥舞着那根前头缀着铅砣的榆木棒子,做出一副对草原上蚊子恨之入骨的表情,正在奋力驱赶这些恼人的小虫。先不说蚊子慑于尚未降落的夕阳那可怕的威力尚未出动,只是挥动那根沉重的棒子,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白宝音格图就这样一路挥舞着布鲁棒子回到毡房去了,而乌云此时正站在门口,微笑着注视着这一幕。
而阿尔斯楞和鬼,他们还在那里玩耍。一种最最单调的互相追逐的游戏,竟然让他们玩得如此兴趣盎然。在液质般渐渐沉落的夕阳中,一个孩子与一头巨犬互相追逐、打闹,孩子的笑声与鬼狂暴的吠叫声明亮而欢快,他们扬起淡淡的灰尘,这是草原黄昏中最温暖的一幕。
他们就那样玩得很晚,直到天色渐渐暗淡,白色的炊烟升上草原无风的天空,缓缓消散,乌云喊阿尔斯楞回家吃饭。
——节选自我的作品《鬼狗》
我曾经拥有过那样的童年。
我就那样和我的牧羊犬一起在草原中游戏,互相追逐,直到黄昏时外祖母站在草坡高处喊我回家吃饭。
但那样的日子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我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