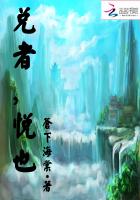我曾经将一头蒙古牧羊犬幼犬作为礼物,送给位于大兴安岭阿龙山区的鄂温克朋友。我以孩子般的好奇心进行了这次尚算完美的实验,当然,那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大兴安岭(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位于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北部,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北起黑龙江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00多公里,宽200—300公里,海拔1100—1400米,主峰索岳尔济山。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是我国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主要树木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皮云杉、白桦、蒙古栎、山杨等。冬季气候极度恶劣,酷寒,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50℃。
那头幼犬来自东旗,即呼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左旗,古时翁吉剌惕部的所在地。也就是成吉思汗当年娶亲之地,他的父亲也速该在这里曾经提醒翁吉剌惕部的首领德·薛禅,说他的儿子帖木真(成吉思汗)怕狗。
这头幼犬先是从草原深处的牧场被带到海拉尔,我一路抱着它从海拉尔坐汽车到根河,然后坐火车从根河到阿龙山镇,再坐汽车从阿龙山镇到山上。最后,它被我从山下一路背到山上的驯鹿营地。
当时,它仅仅是一只大概一个半月大的幼犬,这段漫长的路途对于一只幼犬来说显然极其艰难。这么大的幼犬正是最容易感染病菌的时期,很多幼犬就因为在这一时期感染犬细小病毒和犬瘟热而一命呜呼。而我带着它几乎走过所有人流聚集可能存在这些病菌的地方——火车站、汽车站、旅馆,但它强悍的生命力令我惊叹,竟然安然无恙。
在路上,发生的一件事令我颇为震惊。
当时,我在车站前的小旅馆里等火车。进了客房,把它放在地板上后,我就开始整理装备,它倒是不太认生,一本正经地在房间里四处打探,甚至钻到了床下。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一切都让它感到好奇,它认真地嗅着每一件东西。
我整理完装备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也就是刚刚睡着的样子,就听到哼哼唧唧的声音,睁开眼睛,它正蹲坐在我床前的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它目光中的含义非常清楚,显然是有所企求的。
我以为是自己冷落了它,它感到不安或者不满才发出这样的叫声,伸手将它抱到床上。这种站前的小旅店床单也不是每天更换,本来不是多么干净,我也是将自己的抓绒睡袋铺在上面才敢入睡,让小狗上来也就无所谓了。
但它并没有安静地在我的身边卧下,还是不安地在床上走来走去,发出不满的哼哼。
我困得厉害,本来想顺手将它扔到床下。不过,我分析小狗发出这样的叫声无外乎几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刚刚离开母犬的孤独感和不适应,昨天它已经独自度过一晚,非常安静;不可能是由于饥饿,它今天吃的食物已经足够了;它很健康,也没有病的样子。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了,它要排泄。
这么小的小狗,想排泄撅起尾巴随便在哪里都可以的,难道它还有必须憋着去外面才方便的忍耐力不成。
我算了一下,从清晨坐上长途汽车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小时,它一直没有排泄,对于这么小的狗来说,确实有些不容易。
我抱着它来到小旅馆的后院,将它放在院子中间的土地上。刚刚将它放下,它就急不可耐地在地上嗅闻着,转着圈,很快,它就蹲下,叉开两条后腿撒了足足的一泡尿。随后,它又转移了一个地方,留下一小堆冒着热气的健康的粪便。
完成这些,它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蹲下,抬起头看着我,还是那种目光,看来是希望带它进房间。
我惊呆了,想起我养的威斯拉犬罗杰小的时候,都两个月大了,还在房间里排泄,为教它定点或者外出排泄,我几乎崩溃,甚至不惜亲自趴在地上为它做示范。
而这头小牧羊犬,竟然天生就知道不能在房间里排泄。
我抱着它回了房间,将它放在床上,重新将它审视一番,更加感觉有些爱不释手了。看着它那根小尾巴神气地在背后卷曲着,我不由得伸出手去逗弄着它,它懂得这是游戏,一本正经地假装扑咬着,发出逼真的咆哮声。
在上山的路上,它不小心从我的背包里滑落,掉入林中刚刚开始消融还浮着冰块的冰河里。我以为它会因为着凉而夭折。没有想到,在驯鹿营地的帐篷里烤干了身体之后,它竟然毫发无损。
在营地的最初几天,它对一切都感到恐惧。当我上山外出的时候,它就趴在我背包旁边,既像是在守护我的背包,又像是因为那背包上有我的气味而感到安全。最开始,我对它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驯鹿营地的生活过于粗糙,也许稍不留神,恐怕它就可能葬身于哪头脾气不顺的驯鹿的蹄下,甚至连天天在林子上空盘旋的金雕和雕鸮之类的猛禽也可以顺手牵羊将它掳走。
但它活了下来,迅速地适应了营地的生活。
这小狗当然不会明白,对于它来说,这是一次回归祖地之旅。它的祖先,一种高大强壮的山地犬种,就曾经跟随蒙古民族的先民,从这里走出广袤的森林,进入更为广阔而无边的草原。当然,我这样做除了是将它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山上的鄂温克朋友——这确实是无比珍贵的礼物,另外,我也非常好奇,已经适应了草原生活的牧羊犬是否能够在大兴安岭的林地里安然生活。
这也可以作为这个犬种可以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旁证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头被取名为琴姆且(鄂温克语六趾之意,因其后爪各有一狼趾,因而得此名)的小狗迅速成长为一头体硕毛长的巨犬,对山地生活非常适应,在大兴安岭最低接近零下50℃的隆冬季节,在没有犬舍的情况下,能够在冰天雪地上安然入睡。它也可以很好地承担护卫营地、驱赶野兽和圈围驯鹿的任务。不过因为幼年时追逐幼鹿多次被母鹿袭击,对驯鹿恨之入骨,只要可能从不放弃扑咬驯鹿的机会,一头成年公驯鹿就丧生于它的利齿之下。它也是不错的猎犬,一个冬天,独自捕到6头狍子。被枪击落的飞龙(花尾榛鸡)它竟然连着子弹整个吞下。
2007年冬天,山上的营地失火,鄂温克朋友下山时将它暂时托付给阿龙山镇森林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孙树文先生饲养。它因为过于思念主人而多次出逃,我知道它注定不会在那里待得过于长久。
2008年冬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它在一个落雪的夜晚挣脱了束缚它的铁链。孙树文先生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它的踪影。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它的消息。
琴姆且的父亲,是新巴尔虎左旗草原上一头黑色被毛遍布棕色斑点,汉语名字译过来叫做黑狼的巨犬,被人用枪打死;而它的母亲,一头漂亮的母犬,也被人毒死了。
总之,这个血统的牧羊犬是不会再有了。
当然,我期待着得到这样的消息,也许哪天琴姆且会突然出现在大兴安岭深处阿龙山区的驯鹿营地上。
也许,它回到草原,被哪个牧场收留。
什么时候,当我进入草原上的某个营地,会看到一身浑身纠结着长毛的巨犬慢慢地从蒙古包前的草地上站起,向我迎来。
那时,我不知道它是否还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