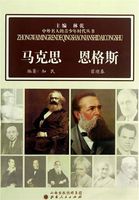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并在出生地终老,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生于瑞士巴塞尔,曾留学德国,师从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兰克。后又受业于美术史教授库格勒,研修艺术史和文化史。在巴塞尔大学长期担任历史学与艺术史讲座的教授,研究重点为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
雅各布·布克哈特出身于瑞士巴塞尔城的一个古老家族。1839年至1843年,他曾经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的兰克门下接受过“西米纳尔”式训练,打下了开展史料批判方面的扎实基础;又在波恩大学受业于美术史教授库格勒,及早涉及到了艺术史和文化史领域。
1843年,布克哈特在兰克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回国2年之后,他就担任巴塞尔大学历史学与艺术史讲座的教授,并且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50年之久。其间当兰克1871年从柏林大学退休的时候,布克哈特曾被柏林大学邀请担任该大学的历史学讲座教授,作为兰克的继承人。
雅各布·布克哈特一生未婚,除了在柏林读书的一段时间和平时的旅游,他从未离开过巴塞尔这个小城,即令是柏林大学盛情邀请他担任讲座教授,也同样遭到拒绝。从这一点上看来,他与大哲学家康德非常相象。不过,不同的是,他爱好旅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于生活也非常讲究,而且天生就有艺术细胞。据说能够了解科摩湖边上什么地方的葡萄最甜;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某某知名之士生前主要喝过哪些种葡萄酒,等等。
雅各布·布克哈特完成中学学业后,在巴塞尔学了两年新教神学(1837~1839年),打算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教士,但他很快发现,历史学更能打动他的心,乃说服父亲同意他到柏林大学学习历史。
此时史学大师兰克已经声名鹊起,成了德国历史学的翘首。他的第一部史学杰作《教皇史》已经于1834年出版第1卷,第2和第3卷也于1836年出版,这部著作很快为兰克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布克哈特已然阅读了《教皇史》,并且能将其中的一部分铭记于心。他之所以决心进柏林大学,就是为了跟随兰克学习当时最新的历史学方法。在动身之前,他曾尝试找人向兰克推荐他,但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却获得了向艺术史教授弗兰茨·库格勒的推荐。怀揣着这份推荐信,21岁的布克哈特于1839来到了作为德国学术中心的柏林大学,他在这里学习了4年,中间有一个学期去了波恩大学。
柏林的三位教授对布克哈特的学术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当然是兰克。他们两人的学术承继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除了布克哈特后来的学术取向大不同于兰克之外,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关系并不融洽。论者均提及,布克哈特并不喜爱他的这位老师,不过这主要是就个人性情、政治和社会态度而言。
对于兰克的历史研究,布克哈特还是推崇备至的。除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和1841年春季在波恩的那个学期之外,他从没有错过兰克任何的课程和讨论班。不仅如此,在兰克的讨论班学习时,布克哈特还提交了两篇长篇论文。前一篇是研究8世纪法兰克人国王卡尔·马特尔的论文,后一篇则是研究德国天主教教派领袖霍希斯特登的论文。两篇论文都使用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而这是兰克十分偏爱的词语,后者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卡尔·马特尔》一文的开头,布克哈特宣称:“本文的目的是确立事实。”这一兰克似的宣言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采用的是兰克的研究方法,即占有全部原始资料,对其进行细致的甄别,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事件的过程。对于布克哈特的这两篇论文以及他后来出版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兰克其实都赞赏有加,并推荐慕尼黑大学给予他教授席位。布克哈特还在其他地方表现出对兰克历史学的推崇。
在1841年夏天,他和波恩大学的另一些同学送给他们的老师兼朋友、波恩大学神学教授歌特弗里德·金克尔一件生日礼物,即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的第一卷。许多年以后,在老年的时候,布克哈特准备了一份自己去世后在葬礼上宣读的生平介绍,其中写道:“我很幸运地在兰克的讨论班上提交了两项有分量的研究,并且很幸运地得到了大师的赞许。”可见布克哈特从未否认兰克对他的影响。
《世界历史沉思录》吕森在谈到布克哈特关于历史的认识时,曾经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说老实话,作为一个老师和讲师,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教历史而慷慨激昂地把它称作世界历史,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入门课,换句话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能力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进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
单从这段话来看,布克哈特对于所谓的宏观历史似乎是没有兴趣的,对于历史哲学更加没有好感,在《导言》中他说:“我们力求避免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并不试图对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观察,而是满足于观察,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历史事件和片断的横切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说起来有点像半人半马的怪物,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他甚至认为,“历史只能片面地和非直接地从事这项工作。”
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他格外看重直接面对史料,以史料为史学之基础,这大概是兰克的影响。他说:“我们在接触更多史料的过程中,通过比较相似的和相对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获得正确的结论,这比读二十本讲解阅读技巧的书更有效。”
他认为原始资料具有两个特性:首先,原始资料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需要靠自己来决定,从这些资料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或结论;而整理性的文献已经越俎代庖地替我们下了结论。不仅如此,只有在直接接触原始材料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才有可能与被阅读对象直接结合,从而产生正确的化学反应。
布克哈特一生勤奋,著述甚多。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有3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和《希腊文化史》(1898~1902年)。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185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史》(1867年)、《意大利艺术史论文集》以及2本遗著:《世界史观》和《历史片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关于这个重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最重要的著作。《世界历史沉思录》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一部,不仅因为他在书中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世界历史。对现实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雅各布·布克哈特布克哈特虽然接受过兰克史学的正规训练,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兰克所倡导的一整套史料批判和考证的方法,但是他并不赞同兰克史学的治史理念,不满足于将自己的史学实践局限于史料考证,也不相信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能够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和心平气和。
于是他一再声称“历史就是解释”、“历史就是批判”等观念,与客观主义史学所标榜的“让史料本身来说话”的原则大相径庭。在历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方面,布克哈特与泰纳极为相似,这一点就连泰纳本人也公开承认。布克哈特的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通过泰纳介绍给法国读者的。他们二人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都致力于寻找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而且都认为这种“典型”特征是在某些稳定因素(泰纳认为是“种族”,布克哈特认为是“国家和宗教”)与时代空间(泰纳认为是“环境”,布克哈特认为是“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因此,布克哈特力图通过宽广的文化史视野来观察“国家和宗教”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作用,从中发现欧洲各个时代的文化形态,进而揭示出各个时代所谓的“典型”特征。
与此同时,布克哈特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也与泰纳一样擅长运用心理分析和心理解剖的方法,而且总是在揭示社会个体的思想、行为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对应关系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应用。例如他在解释佛罗伦萨人对暴君不满的原因时这样写道:“佛罗伦萨在当时是人类的个性发展得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而那些暴君们却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最亲信的人们的个性以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个性存在和发展”。把佛罗伦萨人痛恨暴君的原因归结为个性受到压抑,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解释,而这样的历史解释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见。
布克哈特的史学实践使得他没有能够成为兰克学派的继承人,然而却从另一个角度代表着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融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