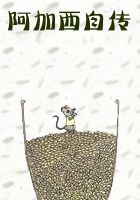就像中国人是在五四以来才兴白话小说白话散文诗一样,《堂·吉诃德》在17世纪西班牙也还是一种新的文学体式。除了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堂·吉诃德》便是欧洲最早的散文长篇。在整个欧洲现实主义长篇创作中起到了开先河之作用。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会凭空产生,《堂·吉诃德》也是在英雄史诗、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等文学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作者继承前人创作经验又不断创作的成果。在塞万提斯看来,骑士小说的可取之处是“题材众多”、“不受韵律拘束”,作家完全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史诗、抒情诗、悲喜剧都可以。塞万提斯作为一种文体尝试,在《堂·吉诃德》中充分表现了波澜壮阔的西班牙社会内容以及变化着的人情世故,呈现了各种人物为了生存而忙碌操劳的景观,众生世相一网打尽。骑士比武场面的“决斗”笑料百出。西班牙士兵的英勇不屈和命运悲惨,被俘虏人的苦难经历和忍辱负重无不令观者为之动容。世事的艰辛、活人的艰难、时代的无道弊病、骄横淫逸的贵族、赤贫的贩夫走卒、薄幸的情郎,芸芸众生,呼之欲出。无不受惠于骑士小说提供的养料。
塞万提斯也摒弃了骑士小说的不足:情节的荒唐脱离现实的内容,人物专写上层贵族、骑士、王公、夫人、小姐等等,下层劳动人民被排斥出描写之列,虽偶有涉及也是竭力去丑化。这些在塞万提斯那里都得到了较好的更正。仅把主仆二人的游侠活动安排在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下,以疯颠滑稽的外表作为修辞策略,对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封建专政社会的腐朽进行了尽情的抨击与揭露。主仆二人便是执行作者这一意图的两个功能性符号一般,用他们的行踪、见闻来串连起了一个活动的社会画面。他通过这一形式,批判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婚姻、教育、文学、社会风尚等一系列问题,以堂·吉诃德的理性大力进攻黑暗社会,展现光明未来,以桑丘的智慧来安排生活事务。在理想与现实相对应的基础上冷嘲热讽、旁敲侧击,一反骑士文学内容庸俗浮躁、浅陋的苍白无力,对西班牙社会进行深刻解剖同时,对西班牙人性的重构起到了超出预料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塞万提斯对流浪汉小说也作了批判的继承。既往的流浪汉小说,多以主人公流浪生活为线索,描写下层平民生活为题材,并从下层人物角度去观察和讽刺某些社会现象,作为16世纪中叶产生的流浪汉小说,冲破了骑士传奇反映生活的范围,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活力,重视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模样。也反映社会各层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西班牙社会的腐朽破落,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受到广泛欢迎,代表作有无名氏的《小癞子》(1553年)。
塞万提斯克服了流浪汉小说主人公怀疑人生、玩世不恭的悲观思想,发展了骑士小说里面英雄人物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把自己较多的同情和爱交给了堂·吉诃德,使这个初看受人嘲笑的可笑骑士从黑暗的时代中矗立起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滑稽英雄。
堂·吉诃德作为喜剧性人物能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激烈的言辞,顽强的追求,非用疯人语言不可,令读者笑过之后,无不肃然起敬,再读便受到鼓励和教育。塞万提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多是善良、智慧、乐观的性格,这也一反流浪汉小说的悲观气氛。好心的女仆玛利托内斯,分赃公平的强盗罗益·吉那特,受到种族歧视迫害的摩尔人李果德,都对西班牙人民给以正面的肯定。总之,塞万提斯是一个宽厚的长者,生活对他虽然不公,命运对他也不幸,可他却寄希望于整个人生,一直乐观地爱着祖国,关心着人民的前途。这才使他成为了一代受尊重的大师。对此,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塞万提斯在武侠小说中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写,掺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诗人海涅充分肯定了塞万提斯在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贡献。他还说,正如同我们把莎士比亚推崇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一样,“我们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
塞万提斯在运用民间口语、谚语方面做出了榜样。前文说过他是第一位运用西班牙语言写小说的人,他在《堂·吉诃德》中对西班牙人民的口语作了大量加工提炼工作,使他的语言不仅具有了民族语言风格,而且也为后代的作家用母语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而且人物语言也极合乎身份,讲求谈吐得体。堂·吉诃德则是学识广博,思维敏捷,高谈阔论,斯文雅致,用词较准。桑丘则是另一路风格,农村语言朴素自然,一串串的民间俗语,而且表意确切,令人无不叫绝。在语言这个文学本体上可算是树立了新的榜样。就连马克思这样的文章大家,都赞不绝口。他和恩格斯都喜欢塞万提斯的语言。马克思还特意以《堂·吉诃德》为教材,为李卜克内西讲授西班牙语。文学大师首先应是语言大师,塞万提斯当仁不让。
文学语言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人们,语言最忌空话、套话、大而无当的废话,最讲求情感特征,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想法,才是好的语言。而今世界范围内的写作发展态势,日渐重视语言为主体的文体学方法。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发展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进展惊人之快。写作者无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力求体现个性,形成风格。作家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文体的兴起与衰亡也实在是语言上的改变。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而塞万提斯的语言特点还有待于我们深入去研究。
西班牙《工人世界》报认为:“所有的语言不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谈吐,而是人民的、清楚有力的精确的语言”。塞万提斯语言的大众化、精确为人公认。研究者还统计过全书应用的谚语有250多条之多,其中4/5集中在桑丘身上。神父说:“这潘沙一家人都是肚子里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桑丘老婆、女儿也一样本事大。此外,儿童歌谣也编进书中,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纯相天成,毫不藻饰,把这些生长于下里巴人中的宝贝语言一经改造,就成了妙语连珠的活动的蹦跳的语言,轻风细雨一般,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对风景的描写都很具体,且服务于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对人物外貌描写也是神来妙笔,让我们一闭眼就会看到“堂·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是一直骑在他的高马上的,而桑丘则仿佛一直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海涅语)”。就连堂·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丘的灰色驴子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堂·吉诃德》这部巨著也有些不足之处,但也算是白璧微瑕。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局限,主人公单枪匹马寻找“黄金时代”,去实行“乌托邦”式的骑士功业。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其次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叛所的火刑,作者作了有意的回避,这也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致,大约他不想把麻烦惹大。
《堂·吉诃德》长篇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是较松散。尤其作者怕冗长叙事吸引不住观者,特意又穿插一些小故事在里边,结果成了美人脸上的疤痕,这也是作家开始时的不太自信所致。游离于整个作品之外,显得无关紧要。
还有小说体例上前后不大统一。原来计划写四卷,后来篇幅加长,等于是个扩建工程,所以设计思想并不连贯。此外还有一些疏漏之处也为行家一再指出。如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拿走了,后来又回到手中。桑丘的“灰点儿”丢了,没找就又骑在了跨下,等等。这是篇幅太长了,作者还没有照应到之处。这或许也是作家年迈之后,老眼昏花,再加生活伙食不太高,居住条件差,让天才的构思总受到环境干扰所致。因为谁都得承认,写作时首先得有个适宜的环境才好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