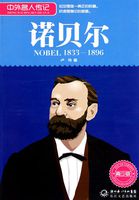梁漱溟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独立的、在野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当权者眼中都是一种叛逆,将来共产党执政,怕是更难容他说话,但他的性格又不允许他去依附于当权者,去说一些违心的话。他已经意识到他在生命的未来岁月中无法避免的悲剧。虽然已为此只发言而不行动,并脱离了组织,但在发言时仍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透露出高度坦达的儒者风度。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因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只好通电下野,让位于李宗仁。当天的《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梁漱溟早已完成的长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文章政治倾向明显,在历数众多事实后,梁明确指出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必须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该文言辞极富挑战性,在当时国民党仍具强大势力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十分大胆了。特别蒋介石虽然下台,但在党内势力未倒,实质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梁的亲友都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梁自己却毫不在意,结果他并没有出什么事。
李宗仁新官上任,立即展开“和平”攻势,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并声称愿意就和平问题与中共重新谈判。他指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并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充任调解人。对梁漱溟也再三邀请,但梁都婉言拒绝,只是向李宗仁提了一些建议,同时劝李也应随时准备引退,不要做蒋介石的替罪羊。
历史是公正的,它再次重演了过去的一幕。不过此时和谈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共手中,对于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表示了宽容,一方面又坚持原则,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其中就包括惩办战犯问题。
对于中共方面的要求,国民党方面表示难以接受。梁漱溟也不满意,他认为如果不谈战犯问题或许更容易达成和平协议。他又一次出来畅所欲言,以期解决和谈中的难题。
首先,梁漱溟满腔愤慨地责问国民党当局:“试问连续三年大战,烽火蔓延数百万方里,前线将士死多少?战区无辜人民死多少?全国各界直接间接所受苦难者有多少……今天一旦你们打不下去,又由你们口里说要和平……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说罪,亦是莫大过失。你们对这过失,竟不负责吗?然而一提到和平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让步,独只有你们自身不容损伤一点,战犯问题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们无罪!好像天下人都该死,只有你们万万死不得!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
之后,梁漱溟则话锋一转:“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切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么做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负而定,成则诸候败则囚,亦没有意味。”随即,梁漱溟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要求国民党要员引咎辞职、闭门思过;共产党也应停止内战,同时也应为内战之发生负责;公推公正人士公开审判,即为定谳。
梁漱溟不自觉中又重演了前次折衷方案一事中的角色,置国共双方的方案于不顾,另立自己的方案。他出发点是争取和平,但在中共看来,无疑是替国民党开脱罪责;而国民党又认为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讨伐自己。梁漱溟自以为不偏不倚却招至双方的怨恨,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所固有的悲惨结局。梁漱溟又何尝不明白这些,只是他一旦认定自己正确后就一定要说出来,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的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
事隔不久,梁漱溟又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一切异已者之存在”,“千万不要重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要求纠正对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者,即他这种人的批判。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称“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的”。如果中共坚持使用武力,即使统一全国,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毁国。梁漱溟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显然已失去了客观和冷静。他公开袒护国民党不算,还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公开讥讽,称之为“替天行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的确起到了很大的负作用。
出于对梁个人的尊重与爱护,共产党并没有追究此事,只是不闻不问,不听取他的建议。但在学术上,立即有不少左翼人士对梁进行反判,指责他不懂马列而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妄加评论,其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击中了梁漱溟的要害,因为这句话正是他经常用来批评别人的。他顿时哑口无言,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便声明自己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不在组织中。同时拒绝了中共请他参加新政议的邀请,退回到重庆勉仁书院的书桌旁,继续他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