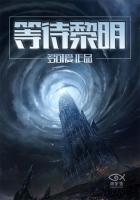斯托里茨的府邸被烧了以后,我觉得城内激愤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人们也安心了。但是,尽管人们烧毁了他的住宅,但毕竟没有见到他的尸体,他可能逃过了这一劫。部分天真的市民发挥无穷想象,坚持认为凶犯已葬身火海,不然的话,他如何能逃过大火的焚烧呢?
这时,斯普伦贝格警方传来急电证实:威廉·斯托里茨没有在故乡露过面,他的仆人也失去了踪迹,两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躲在哪里。他们很可能还留在拉兹。
尽管城里稍微平静了些,但罗特利契家却没有。可怜的米拉的精神状态没有丝毫好转。她对一切仍无动于衷,对亲人们给予的关心照顾也漠然视之,她仿佛不认识任何人。医生们不敢持乐观态度,因为她没有间歇性的情绪激动,如果大吵大闹一番,医生们还能想办法刺激她,使其作出某种有益的反应。
尽管米拉身体很虚弱,但万幸的是,她没有生命危险。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白如纸。如果有人想扶她起来,她就发出阵阵呜咽,眼睛中充满害怕的神情,双臂扭曲着,嘴里喃喃着不成文的句子。她想起了可怕的往事?她在神智混乱中又看见了花束被毁,花冠被夺,又依稀回到教堂里?她又听见了那恶狠狠的威胁?但愿如此,至少她头脑里还保留着对过去的记忆。我们只能等待,时间能治愈一切吗?
大家可以想象,如此不幸的家是怎样度日的!玛克一刻也没离开过罗特利契家。他和医生、罗特利契夫人陪伴在米拉身边,他亲手喂米拉进食,他多想再见到米拉眼中那俏皮的神情。
22日下午,我漫无目的地闲逛在街头巷尾。心中预感,不知是否会碰到什么。
忽然,我决定去多瑙河右岸看看。我早想去那边瞧瞧,但情况不允许,何况目前这种心情也不适合。我走过桥,穿过斯闻多尔岛,到达了彼岸的塞尔维亚。
真是一片壮美的原野。这个季节里,庄稼、牧草长得绿油油的,令人心情舒畅。我发现塞尔维亚的农民和匈牙利农民有着相似之处:同样的漂亮迷人,同样的姿态。男人们的目光有点冷酷,他们迈着军人般坚实的步伐,女人们仪态万千。塞尔维亚人身上的政治热情特别浓烈,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极度关心政治。塞尔维亚被喻为“东方之门”,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行政职能的城市,正扼其咽喉。虽说它名属土耳其,匈军向土耳其缴纳三十万法郎的捐税,但塞尔维亚是奥匈帝国最大的基督徒聚集地。
塞尔维亚民族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一位法国作家说得好: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地区,只要登高一呼,立刻就出现千军万马,这只能是塞尔维亚,这个爱国、尚武的省份。塞尔维亚人是天生的士兵,他们生为士兵,死为士兵。这个南斯拉夫民族向往的圣地,难道不是首都贝尔格莱德吗?如果有一天,这个民族起来反抗日耳曼人;如果革命爆发,必将是塞尔维亚人用坚毅的手擎起这面独立的旗帜!
我沿着蜿蜒曲折的河岸,一路走,一路沉思。左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尽管塞尔维亚人认为,砍倒一棵树,等于杀死一个塞尔维亚人。但树木砍伐依然严重,已经没有茂密的森林了。
我也时常想起威廉·斯托里茨。我暗自琢磨,他是不是躲在原野上的一幢别墅里,他是否已恢复人形。不会。他的可怕在多瑙河两岸都传得童叟皆知,如果有人在此发现他和海尔门,塞尔维亚警方会马上逮捕他们,送交给匈牙利警方。
大约6点钟,我又回到桥上朝斯闻多尔岛的中央大街走下去。
我刚走了几步,远远看见了斯泰帕克先生。他也是独自一人,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们两人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仍没有新发现,我们一致认为拉兹城前段日子的恐慌已经过去,城市开始恢复平静。
大约三刻钟以后,我们来到岛的北端。夜幕降临,树林里一片漆黑,小路上冷冷清清,木屋紧闭,路上没有一个人。
我们正要朝回走,这时,一阵说话声传来。
我立刻刹住脚步,拉住斯泰帕克先生的胳膊,示意他停下来;然后我俯身过去,小声地对他说:
“您听到有人说话了吗?好像是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警察局长也轻声地问。
“确实是他。”
“既然是他,就一定不能让他发现!”
“不止他一人。”
“可能还有他的仆人。”
斯泰帕克先生拉着我,猫着腰,躲到树丛后。
浓浓夜色方便我们向他们靠近,使他们无所觉察。
我们迅速地躲进树丛里,离威廉·斯托里茨大约有几米远;也许他们都隐身了,我们没有看见人影。
现在,我们可以确信威廉·斯托里茨和海尔门就在拉兹。
天赐良机,让我们在这儿巧遇上他们,并没使他们发觉。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甚至可能抓住他本人。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就在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我们半蹲在灌木丛中,在树枝间,屏住呼吸,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主仆二人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树丛边,他们的谈话也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我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威廉·斯托里茨在问):
两人在用德语交谈,斯泰帕克先生和我都能听懂。
“我们明天就能住进去?”
“一定能”,海尔门答道,“而且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你什么时候到拉兹的。”
“上午刚到。”
“你带药水了吗?”
“带了两瓶,但藏在房间里。”
“海尔门,你能保证我们在光天化日下住进去,而不会被认出来?”
威廉·斯托里茨说出一个城市名称,但遗憾的是我们没听清楚,因为说话声音离我们又远了,当声音近时,只听海尔门反复保证:
“主人您放心,我用的是假名,拉兹警局查不出我们。”
拉兹警局?他们还住在一个匈牙利的城市里?
脚步声越来越微弱,他们走远了。这时,斯泰帕克先生才低声对我说:
“必须搞清是哪座城市?用什么化名?”
“还有,”我补充道,“为什么两人又回到拉兹?”我不禁暗自为罗特利契家担忧起来。
当他们又走近时,一切都明白了。
“我不会离开拉兹。”威廉·斯托里茨说,声音中充满怒气。
“我要报仇雪恨,除非米拉和那个法国人……”
他没说完,接着胸中发出一声怒号!这时,可以感觉到他离我们很近,一伸手,或许就能抓住他!但海尔门的话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拉兹人现在都知道了您能隐身,只是不清楚隐身的秘密。”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永远!”威廉·斯托里茨咬牙切齿地说,“我跟拉兹没完!每家每户……他们以为烧掉了我的房子,就烧掉了我的秘密!疯子!不!拉兹逃不出我的报复,我要让它片甲不留。”
话音刚落,树枝猛地被拨开。原来是斯泰帕克先生,他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扑了过去,那就在我们藏身处三步远的地方。
我也迅速跟上,这时,他喊道:
“我抓住了一个,维达尔先生。您对付另一个!”
显而易见,他的双手捆缚着一个人,虽然看不见,但完全触摸得到。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开了,要不是我抓住他的胳膊,他就摔到地上了。
当时,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因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而且周围一片漆黑,这时,左边响起一阵笑声,随着“啪啪啪”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竟让他溜了。”
“出师不利!”斯泰帕克先生大叫,不过,我们也有所收获,隐形术并不妨碍我们抓他的身体。”
轻而易举地让两个坏蛋从手中溜掉,我们心中非常懊恼。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但我们清楚地了解,罗特利契家、整个拉兹城仍然置于流氓的魔掌之中。
我俩走出斯闻多尔岛,过桥后,在巴蒂亚尼堤岸分手。
晚上九点钟,我回到医生家,当时,罗特利契夫人和玛克守在米拉床边。重要的是,应该马上告诉医生发生在斯闻多尔岛上的事件,并提醒他,威廉·斯托里茨仍在城内。
当我单独和医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明白,面对那个家伙的威胁,面对他执意向罗特利契家复仇的意志,离开拉兹已势在必行。必须离开,而且越早越好!
“我有一点担心,米拉能否承受旅途的颠簸?”我问道。
医生沉思了一会儿,他回答道:
“我女儿的健康没问题,她只是精神受到伤害,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她就会好起来。”
“尤其是安静,”我说,“在法国,她会找到安静,她不用再恐惧什么。在那里,父母兄弟,还有她丈夫玛克精心照顾她,毕竟玛克和她之间举行了世俗婚礼,谁也不能拆散他们。”
“谁也不能,维达尔先生!但我们远走他乡,就能避开危险了,威廉·斯托里茨不会跟踪我们吗?”
“只要我们秘密行事,不泄露行期,绝对不会有问题。”
“秘密?”医生不无怀疑地低声说。
医生和玛克一样,对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疑惑,因为谁也难保威廉·斯托里茨没有蹲在屋内,偷听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又在策划什么新的阴谋,企图阻止我们离开拉兹?
但是,尽管如此,离开拉兹是决定下来了。罗特利契夫人也没有异议,她巴不得米拉早已被护送到另外的地方。
玛克也没有反对。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在斯闻多尔岛与威廉·斯托里茨、海尔门的巧遇。我觉得告诉他也于事无补。但我把斯闻多尔岛上的巧遇告诉了哈拉朗上尉。
“他还敢在拉兹!”他听后叫道。
他没有反对此次转移,还极力赞成,又说:
“您一定会陪着玛克吧?”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陪他,您也必须防……”
“我不走。”他回答道,语气中显示出内心的决定不可动摇。
“不走?”
“对,我必须留在这,我有预感,我留下来乃是明智之举!”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于是我又问道:
“可是,上尉……”
“我信任您,亲爱的朋友,有您在我家人身边——他们也是您的家人,我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您尽可放心!”
第二天,我到车站预订了火车包厢。这是一列快车,晚上8点57分发车,途中只在布达佩斯停靠,次日凌晨抵达维也纳。我们再转乘“东方快车”,我已电告,让人预留一间厢。
随后,我去拜访局长先生,并把计划告诉了他。
“英明之举,”他说,“只可惜,不可能全城的人都搬走。”
警察局长显得心事重重,也许是因为昨晚我们听到的威胁之词吧。
晚上7点钟左右,我回到罗特利契住宅。我相信,出发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应该料理妥当。
8点刚过,一辆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停在住宅前,是罗特利契夫妇、玛克和神智不清的米拉乘坐的。哈拉朗上尉和我坐另一辆马车,从另一条路驶回车站,这样可以避人耳目。
医生和玛克走进米拉的房间,准备把她抬到马车里。但是,米拉已不在房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