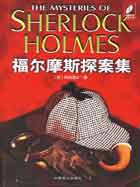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强壮得跳下床就能飞跑,这在我苏醒后第五天上厕所时感觉出来的。每次上厕所,都有三个专政队员押着我——一左一右两个抹着我胳膊,另一个跟在后面监督。把我塞进窄小的厕所里,他们就只能站在门口守候。这时我就试着用双手撑着墙壁,让整个身子离地,果然就离地了。我为自己康复得如此快也大感吃惊,我甚至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有鬼神保佑我,只是我想不出鬼神为什么保佑我。可细细想想却觉得这要归功于刘剑飞,刘剑飞教我腾空飞跣,经常就往沙滩上狠摔。锅炉房的煤堆全是粉碎过的煤面子,煤面子远比海沙子软和多了。
我开始强烈地思恋姐姐和那个喊我舅舅的小外甥女。病房门每一次被推开,我都感到是姐姐走进来。然而除了表情严谨的医护人员,再就是表情冰冷的专政队员。
一天,一个表情最严谨的女护十突然对我露出生动的笑容,她小心地回头看了看门外,然后小声说:你疯啦,从那么高的烟囱往下跳!
我说,我还要跳——我把她们和专政队看做一是伙的,我决不能让这些家伙知道我心里的软弱。
她说。用不着再跳了,形势快要明朗了……
我不明白明朗是什么意思,只好怔怔地看着她。我发现她和姐姐年龄差不多,眼神也有我姐蛆那样的温柔。她给我喂饭时,动作最熟练。而且扶我欠身的高度最合适,所有的饭菜都顺利地送进我的嘴里,没掉外面一粒米和一个菜叶。而别的护士总是草草地往我嘴里塞着,一碗饭最多吃进去一半,那一半全在枕头和褥单上。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解开绳索?
她说,你疯啦,你想让我也被绑起来呀!
这时,门被用力地推开,一群专政队员走进来。我以为他们又要强行押我上厕所,但我发现他们至少五六个人,而且进来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动作粗野并干练地将我掀下床,连拖加拽,不一会儿,我就从医院走廊到楼梯,从黑洞洞的冈车到拘留所,最终被关进一间只有一个小窗洞的屋于。
当老坏带着一个专政队员走进来,我明白完了,要吃大苦头了。老坏的形象就够恶劣的了、另一个更不像个样子,就是两只跟几乎长在一起,绝对海里的比目鱼。老坏和比目鱼正在阴险地朝我冷笑。
老坏说,陈胡子,我来感谢你,感谢你给我打成英雄了。
我不吱声,心下只是万分懊恼。
比目鱼说,你水子竟敢打断我们队长的肋骨……
老坏立即打断比目鱼的话,又故意笑了笑,我们无产阶级是钢筋铁骨,你这个反动派是打不断的!
接着,两个家伙就顾不得假装笑了,开始凶相毕露,并咬牙切齿地骂起来,骂我是疯狗,是流氓,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老坏指着我的脑门,你他妈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这一条就能枪毙你好几次。
两个阴险的家伙骂够了,就又冷笑着走了。他们说先给你养几天精神,准备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再教育。
我不吱声,反正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绝对不会把我打死,因为他们怕我死。可我却总是不明白,这些家伙如此凶狠地打我,可为什么怕我死呢?坦率地说,我从烟囱七跳下来之后,也开始怕死了。我恐惧地感到,我身上负责胆量的器官绝对摔坏了。
老坏说话倒算数,我在小屋里一直躺了两天,并没什么动静。意外的是伙食还有了改善,竟然能吃到面条。星期天的晚上还加了个两面(白面和玉米面两掺)馒头,我吃得挺香。
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些消息,某某被平反了,某某被释放了,某某被解放了。然后我就做起了美梦——我被解放了,专政队笑呵呵地送给我一套新服装,上面还印着革命委员会好的金字,我大概还戴上一个红袖标,光光彩彩地在大街上走。倒霉的是还没走上一分钟就掉进一个大坑里,坑边上的石块随我一起掉下去并很疼地砸在我身上——我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我是躺在水泥她上。我再眨眨眼,才明下三我是被老坏带着一群专政队员拖下床的。我装作昏昏然,暗暗用两臂护住脑袋,贴着地面看那一圈大头鞋,我就知道又要来一次。天这么暖和了他们还不脱大头鞋,大概就是为这一手。
谁知这些家伙并不打我,反而摸摸索索地整理我的床铺,似乎要给我铺得舒服些。他们仔仔细细地铺完床,却又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上去。正当我莫名其妙时,老坏一下子按住我的四肢,用宽布条把我手脚牢牢地捆绑在床上。我大声叫骂,但没叫几声,他们就给我嘴里塞上东西。
你绝对想不出他们用什么方法打我,全世界最有水平的打手也打不出这个水平来。这些家伙把我绑牢后,再扒下我的衣裤,但并不凶狠地拳打脚踢,而是在我的皮肉上放一块极其光滑的木板,然后用木棒小心翼翼地打那块木板。这些坏家伙从半夜一直这么仔细地打到早晨一打得我五脏俱裂,疼痛难忍。但由于有光滑木板垫在其中,我那粗糙的皮肤不仅没有一丝伤痕,还变得细嫩透明,像姑娘的脸蛋,尤其是我的屁股,肿得红盈盈亮品晶的像西红柿。
老坏并不满足,他不断地来观察我的伤势,又认真仔细地打了我几次,最后,我浑身肿得像个发炎的牛膀胱,他们这才住手。
我从烟囱跌到煤堆上,应该说够厉害的,但只是昏厥了几天,并没感觉到太多的疼痛。老坏他们不动声色地打我,却比跳一百次烟囱还要命。我以后许多天不但不能说话,连喘气都相当困难,就像全身的皮肤里插满了碎玻璃,稍微蠕动一下都万箭扎心。
军管会的官儿并没忘记我,多次派人来检查询问过,但他们都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医生也断定我没挨打——他说这是我从烟囱上跳来的后遗症。你想想,一个人从那么高的烟囱上跳下来,肯定会有后遗症。
我什么也不说,我知道说什么也没用。
我好长一段时间不得不站着睡觉——因力我肿得红亮的皮肉特敏感,即使接触柔软的棉花,也像撞到坚硬的钢铁,后来,即使刮来一阵风,皮肤都能产生痛感。我敢说,要是全世界比赛疼痛,我绝对能得第一。
我忍受疼痛的毅力甚至感动了老坏的副手。一个年龄挺大的专政队员,他暗地里给过我不少帮助,还给我接过好几次尿。我当然不能被他感动,说不定这家伙是用新的花招来麻痹我。
一次夜里这个老家伙值班,他大概喝了些酒,竟然就跑到我的小因室里坐着不走,也不管我听不听,就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原来这家伙也有个与我年龄一样的儿子,脾气也和我同样直爽——这家伙不说暴躁说直爽,这让我对他有点好感。他说他直爽的儿子得罪了他们单位的专政队,被抓去将两腿都打断了。最后用担架抬回家。这老家伙牢骚满腹——他说你小子一定要咬住牙,第一你没杀人放火搞破坏,第二你没讲反动话也不是反革命,第三你的出身好得不能再好——我们专政队派人调查过,你父母旧社会逃过荒要过饭,你家祖宗三代穷得连裤衩都没穿过。打架斗殴算什么错误?电不是打革命群众!……这老家伙的儿子因为曾被专政队打断了腿,思想就不坚定了,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他酒喝得太多的时候,甚至都把我当作他的儿了。
形势看来真是要明朗了,军管会的首长也亲自下来检查。但专政队的人很会对付检查,这些家伙在我们面前横眉竖眼,飞扬跋扈,但见了戴帽徽领章的,却像个孙子——一个个颠颠的,兔子似的跑来跑去。平日满嘴粗话的专政队员,变戏法似的一下子文雅得像教授。他们当着军管会头头的面给我端水,给我打扫床单,还不时地对栽做出甜蜜的微笑状——似乎压根就是这样。
军管会的头头很满意,连连点头,满意万分地走了。
有一天,一个军管会更大一些的大官来了,因为专政队的头头们全都到位,而且一个个哈巴狗一样地点头哈腰。我对这些检查已经绝望了,甚至连脸也不转过去。可是我猛然听到那个大官尖细的女声。我立即转过身子,脱口喊了一句,解放军郝叔叔!
那个大官儿愣了一下,眯着眼睛看我。
我说,郝叔叔,你不认识我啦?说着,我掀开衣服,让他看我肚子上的伤疤——从大豆角树上飞跳下来,被尖玻璃剐开肚皮露出肠子……但我掀衣服的动作使我打肿的身子痛得钻心,我不由自主地哎哟了一声,差点就跌下床去。
我发现专政队的人全乱了。他们扎撒着两手,想去扶我却又不敢扶。
郝叔叔竟然认出我来,他不但认出我,而且还能喊Ⅲ我的名字——小立世!并亲自上前来扶我。我却一下子昏厥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昏过去并非专政队毒打所至,而真正是从烟囱上跳下来的后遗症——我尽管奇迹般地活下来,但神经却摔坏了。后来的年月,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昏厥一次——完全像挨了一铁棍似的,脑袋轰的一下就过去了,要是有什么激动的事,我昏厥的次数更多。每次昏厥至少要昏睡整整一天,幸运的是只要醒过来,立即就正常人一样,而且能立即健步如飞。
郝叔叔已经升为司令——也许是副司令,反正挺有权力。所以,我被拉进市里大医院里检查。大医院里的大夫医术高强,不但发现了我摔下来的后遗症,同时还发现了我被打肿的身体。不过,他们也惊讶得眼镜全都掉到地上,因为他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皮肤肿得如此漂亮。
我说过,我的身体素质太棒了,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就健康得能参加奥运会。我对郝叔叔讲丁我的全部经过。最后,我学那个老家伙的说法——第一我没杀人放火搞破坏,第二我没讲反动话也不是反革命,第三我家祖宗三代穷得连裤衩都没穿过……很快我就被解放了。郝叔叔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尽快地见到姐姐和姐夫。
郝叔叔用非常感动的目光看了我足足一分钟——原来他所说的要求是问我怎样处理专政队打我的家伙。
我说只要放我出来,管他什么要求我都不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