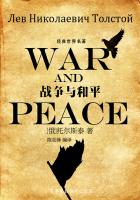我奶奶以哄孩子们玩为乐事,她最爱把孩子拉到自己的身边,似爱抚一只猫儿、狗儿似地、抚着孩子的头发,摸着孩子的脸颊,和孩子们说些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话。我奶奶和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把我搂在她的怀里,一只手不停地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拿我当一只小狗儿。和我姐姐说话,她就搂着我姐姐的肩膀,一只手也是不停地抚摸着我姐姐的头发,拿我姐姐当一只小猫儿。和杏儿、桃儿说话,说着说着,我奶奶就把杏儿、或者是桃儿的手握在她的手里了,还不停地摸弄着她们的小手,把她们两个看得和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一天晚上,听说我奶奶没出去打牌,我母亲就带着桃儿姐姐过来陪我奶奶说话,当然也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好说,就是东拉西扯呗,我奶奶说老老年间的事,我奶奶说,我们家原来在积善里的老宅,有一年闹狐狸,总听前院里一到夜深就有动静,就象是有人出没似的。那时候吴三代还是个年青人,他胆子大,有一天深夜,他又听见前院里有声音传过来了,他提着脚跟,就悄悄地往前院摸。才走过二道门,他就看见前院院当央有一群小老头围在一起坐着,似是正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吴三代步子轻,就一步一步往前挨,走到近处一看,你们猜猜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一群狐仙在下棋。也是车马炮地走着,就是棋步不对,老帅摆在河沿上了,卒子却又摆在老帅的城里了,噗哧一下,吴三代忍不住笑出了声音,你猜怎么样?狐仙们连理也不理吴三代,还是乱走棋步。第二天,吴三代把他在夜里看见的情景告诉了你们的曾祖父,你们的曾祖父就在前院里的石桌上放了一本棋谱,谁料到了第二天再一看,那本棋谱下边多了一副棋子,唉呀,有气性,人家不下棋了。
说着,我母亲和桃儿姐姐一起全笑了。
可是就在我母亲和桃儿姐姐笑的时候,我奶奶一伸手就把桃儿的手拉过去了,我奶奶一面还说着老宅里闹狐仙的事,一面就摸弄着桃儿的手,摸着摸着,我奶奶似是有了一点什么感觉,她把桃儿的手抬起来,又低着头细细地查看,这一下,桃儿似是紧张了,她立即就把她的手从我奶奶的手里抽了出来。
“你让孩子做什么粗活了?”我奶奶向我母亲问着。
我奶奶再糊涂,她也能感觉出来桃儿的手再不似以前那样柔细了,手指又硬又直,皮肤也粗得成了一层树皮,不光是没有染红指甲,手背上已经有了裂痕,这不是桃儿的手,就是那些做粗活的婆子们的手,也不似桃儿的手这样粗。
我母亲慌了,桃儿去芸姑妈家做活的事,到现在我奶奶还不知道,她虽然也知道一些梁月成家的变化,但她想不到芸姑妈会受苦,更想不到桃儿每天会去梁家做那种粗活。如今真是纸里包不住火,怎么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破绽呢?我母亲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向我奶奶说着:“我房里会有什么重活呀?”
倒是桃儿机灵,她立即对我奶奶说:“也是这一阵风野,怎么才几天洗手没擦雪花膏,手背就‘苫’了呢?”
“苫”是天津话,到了秋天,北方的风野,女子的纤手,一不当心,手背的皮肤就变粗了,我们小的时候,洗过脸、洗过手之后,桃儿姐姐总要在我们的脸蛋、或者是手背上涂些雪花膏,就是怕“苫”了我们的皮肤。
“不对。”我奶奶摇着头说:“风再野,手指不会变硬的,我知道你们有事瞒着我。”我奶奶说着,脸色沉了下来。
当即,我母亲就吓慌了,有事情居然瞒着老祖宗,这也是做媳妇的大胆了,我母亲正想着该如何度过这一关,我奶奶又沉着脸向我母亲说起了话来,“我说过的,宋燕芳那里,不能给她派人,宠得她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怎么就不能自己做点活呢,还想养着她那一双手唱戏去呀?不能自己做活,就让她出去。”我奶奶厉声厉色地说着。
“不是宋燕芳的事,桃儿压根儿也没有到小的儿房里去过。”我母亲对我奶奶解释着说。
“那你是支使孩子干什么活了?”我奶奶倒也不是不能让桃儿和杏儿干一点粗活,我奶奶有她的规矩,她不允许桃儿和杏儿到前边和那些佣人们一起做事,男男女女的,多是非。
“老祖宗放心,少奶奶可疼着我和杏儿了。”桃儿向我奶奶说着,一双眼睛还向我母亲望着。
“侯家大院里有侯家大院的规矩,谁应该做什么活,谁就去做什么活,桃儿、杏儿是总和我一起出去的孩子,她们两个人的手这样粗,让亲戚们看见又该如何想?人家一定会说,侯姓人家不厚道了,连贴身的孩子都支使去做粗活。”我奶奶向我母亲说着。
事到如今,我母亲感到实在也是瞒不过我奶奶了,想了一会儿,我母亲便对我奶奶说道:“实话对奶奶说了吧,我是派桃儿到姑奶奶家做活去了。”
“芸之家怎么了?她们不是使唤着好几个人了吗?听说连那个梁小月上学,都有专人替她提着书包。也太不象话了,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好好读书呢?”我奶奶愤愤地说着。
“梁月成在外面惹大祸,少奶奶家败落的事,老祖宗是已经知道了;可是家败之后,梁家也就不能再过那种荣华富贵的日月了。”一五一十,我母亲把梁月成家迁出原来的公馆,如今迁到大杂楼里的经过,都对我奶奶说了,说过之后,还说到芸姑妈给那俩个孩子洗衣服的事,话还没有说完,我奶奶就插言向我母亲问道:
“芸之怎么有力气做那种累活?”
“所以桃儿才瞒着老祖宗,和我商量到姑奶奶家去做活的,媳妇怕婆婆耽心姑奶奶的境况,不敢让婆婆分心,也就一直没敢对婆婆说。”我母亲终于把事情向我奶奶全说出来了。
“这个梁月成,他把芸之给坑苦了。”我奶奶听过之后,叹息地说着。
“梁家的日月,婆婆只管放心就是,茹之说了,无论多少开销,他全包下来了。这种事,又不能从咱们的大帐房支钱,各房各院的眼睛多着呢,谁院里多开销一点,就是听不完的闲话,咱们养了南院、北院这么多年,真是犯不上听那些闲话了。茹之倒是知道自己的责任,他给了我一笔钱,每次桃儿到姑奶奶家去,我就让桃儿给姑奶奶带些钱去,衣食住行,姑奶奶是不会受委屈的。”
“真应该把芸之接回来才好。”我奶奶对我母亲说着。
“媳妇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媳妇再一想,把姑奶奶接到咱们府里来,梁月成怎么办?把他一个人放在他们家里,只怕他连口热饭都吃不到嘴的。还有那两个孩子,跟过来,就是恶吃恶打,那两个孩子的开销,可是比咱们一个院里孩子们的开销还要大得多呢。”我母亲向我奶奶解释着。
对于我母亲的安排,我奶奶实在是应该感谢了,她心疼女儿,听着女儿受苦心里不安宁,可是我奶奶也想不出好办法来,能让梁家重整旗鼓,一时半时地,还看不出有什么迹象会让梁月成东山再起。
“我说这些日子总没见茹之呢。”我奶奶感叹了一阵,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你们看个机会,把茹之接回来住些日子,我也是想她呀。”
“老祖宗的话,桃儿留心就是了。”这时桃儿才接过话来说着。
随之,我奶奶又询问了芸姑妈每天的饭菜,我母亲回答说,钱是按时交给芸姑妈的,饭菜也是由芸姑妈安排,芸姑妈自己不上街买菜,全都是桃儿上街去采买的。这时,我奶奶就感激不尽地对桃儿说着:“真是难为桃儿了,怎么就能上街买菜买鱼去呢?”
我奶奶又问到芸姑妈一家的穿衣,我母亲回答说,冬天的衣服已经做下了,前些日西北客商送来的那些皮货,桃儿已经送到芸姑妈那里去过,芸姑妈留下了一件银狐腿的袍子,还给两个孩子各自留下了一件裘皮,说是到过年的时候给他们做新衣服的。一切一切都询问过了,我奶奶这才放下心来,这时她又拉着桃儿的手说:“桃儿是在咱们侯家大院立下功劳的人了。”
“桃儿真是不敢当了,老祖宗这样疼爱着桃儿,桃儿尽心尽力地做点事情,算得了是什么功劳呢?”桃儿谦恭地说着,随后,就和我母亲一起从上房走出来了。
桃儿记着我奶奶的吩咐,总想着找个机会接芸姑妈回家来住几天。梁家有钱的时候,芸姑妈的确没有多少事情好做,所以回到侯家大院来,一住就是半个月,家里的事,全都有人操持。可是如今梁家不行了,芸姑妈竟然一分钟也离不开了,有一次好不容易两个孩子不在家,桃儿把芸姑妈按回家来,可是芸姑妈只吃过午饭就回去了,芸姑妈说家里还有一个梁月成,整天躺在床上,有时一天也不吃饭,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其实呢,就说我们的芸姑妈吧,虽然是富里生、富里长,可是嫁到梁家,随着梁月成过上了苦日月,也不是什么没法活的事。我母亲也是富里生、富里长的大家闺秀,嫁到侯姓人家来,不是也遇上我老爸这么一个不成器的丈夫了吗?那年月又不兴离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就是一个人生闷气罢了,谁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对于芸姑妈来说,最难的事情,是她那两个前窝的孩子,他们可真是让芸姑妈生气了。
梁月成破产了,梁家的开销没有缩减,衣食住行,梁小月和梁小光没有受一点委屈,按道理说,他们应该多少懂得一点道理了。只是他们的欲望永远也没有一个满足,总是要这要那,稍一不称心,就骂闲话,芸姑妈听见,自然就要生气。
桃儿是个息事宁人的好孩子,有时候,那两个孩子明明冲向着桃儿说芸姑妈的闲话,桃儿只装做是没听见,也就把事情化解了。但是,终于有一天,事情化解不了,这样,就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事。
那一次,梁小月说学校要组织远足,就是旅游,也不出什么远门,就是到一个近地方去玩一天,芸姑妈听说之后,立即就吩咐桃儿给梁小月买了面包、香肠,巧克力、还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足够梁小月吃一整天的了。只是,象梁小月读书的那类学校,学生们就是彼此比阔,比穿衣,比打扮,比谁身上的毛病多,比谁不好侍候。梁小月曾经对我说过,梁小月说她的一个同学,就为了买了一双皮鞋配不上合适的鞋带,楞气得三天不去学校,梁小月对这种人很佩服,说这种人有志气,我说这种人就是欠揍,狠狠地揍她一顿,她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梁小月要远足,就要买新皮鞋,就要买新裙子,就要买新手帕,买回来之后,这个花色不中看,那个颜色太剌眼,就没有一件东西合她的心意。不合心意,那就再要钱去买,再买回来,也还是不称她的心意。
那一天,桃儿正在芸姑妈家做活,正赶上梁小月向芸姑妈要钱,芸姑妈什么话也不说,就是要钱给钱好了;可是给钱也要往外拿呀,就因为芸姑妈拿钱时慢了一点,就惹得梁小月好大的不高兴,梁小月接过钱来,一面向屋外走,一面嘟嘟囔囔地说着:“反正差着一点难着了,花这么一点钱,瞧把她心疼的。”
芸姑妈当然听不下这句话,她便在梁小月身后说着:“小月,你这话可是不当说,怎么就差着一点难着了呢?你到侯家大院里去看看,你舅娘房里的孩子们,哪个似你这样花钱?”
“我怎么花钱了?”梁小月停住脚步,转回身来向芸姑妈问着,“我花我爸爸的钱,又没有花你们老侯家的钱。”
“小月,你还当你父亲挣下多少钱了吗?”我芸姑妈对梁小月说着,“你看见了,你父亲整天在家里坐着,房子也没有了,若不是舅娘好心,只怕你们未必就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照你这样说,合算我们花的是你们侯家的钱了?”梁小月一副不讲理的样子,恶凶凶地就对芸姑妈喊着,“你也别拿我们当不懂事的孩子看待了,你没有进门之前,我们梁姓人家也算得是有钱有势的人家了,怎么你一个扫帚星才进得门来,我们梁家就败落了呢?钱也没了,公馆也没了,搬到这么个大杂楼来,过穷日子,别逼得我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我们梁家的钱,还不知道你折腾到哪里去了呢。”
梁小月放泼大骂,把芸姑妈气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芸姑妈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面,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捂着胸口在椅子上坐着。这时,桃儿也是气不愤,才走过来对梁小月说道:“我看还是对小月姑娘说清楚了的好,今天我过来的时候,我们少奶奶还让桃儿给姑奶奶带过来20元钱的呢,刚才我们姑奶奶给小月姑娘的钱,就是我刚刚带来交给姑奶奶的。”
桃儿的话,说得梁小月没了理,她冲着桃儿就喊了起来:“一个臭丫环,哪里有你说话的权利,你从我们家滚出去!”
“我可不是看望小月姑娘来的,我是看望我们侯姓人家的姑奶奶来的,滚不滚的,桃儿还要听我们姑奶奶说话呢,不怕小月姑娘过意,你有话,还和我说不着。”桃儿从生下来没有和人说过气话,今天她实在是看芸姑妈太窝囊了,才挺身而出为芸姑妈撑腰。
“你们侯姓人家也太厉害了,住在你们家里,你们上上下下地欺侮我们,躲回到我们自己家里来,你们还从娘家搬兵到我们家来打架,你们不就是靠着美孚石油和大阪公司的势力吗?”
“梁小月,你放肆!”我的芸姑妈没有本事和人吵嘴,她只会说这么一句没有力量的话,人家梁小月才不怕你呢。
梁小月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她摆出一副不含乎的样子来,向着芸姑妈和桃儿就是破口大骂,喊声把整个大杂楼的人全惊动了,大家就都跑下来看热闹,这些人自己家里倒了霉,就最爱看别人家比自己家还倒霉,他们围在梁月成家的门外,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闲话。
梁月成呢?桃儿说他才是一个蔫土匪,他听着他女儿骂我芸姑妈,他仍躺在床上抽烟,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象是看别人家的热闹一样,梁小月越骂嗓门越大,穷得发疯的人,就是豁得出去,她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不中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她一点也不象是一个中学生,她象是一个泼妇。
“你你你……”芸姑妈看着门外的邻居,听着梁小月的臭骂,只气得全身不停地哆嗦,桃儿怕芸姑妈生气,也就再不和梁小月理论,她只是劝着芸姑妈别和梁小月一般见识。芸姑妈忍着忍着,最后,就听见芸姑妈“噢”地一声喊,芸姑妈捂着胸口倒在了桃儿的怀里,桃儿一把将芸姑妈搂住,这时,芸姑妈已经不省人事了。
“姑老爷,我们姑奶奶犯病了。”桃儿向着梁月成喊了一声,这时,梁月成才从床上蹦下来,向着他的女儿梁小月喊了一声:“小姑奶奶,你就绕了我吧。”
梁小月看芸姑妈气得犯了病,她拿着钱一步就跑走了,桃儿在家里服侍过芸姑妈,她知道芸姑妈犯了病是多可怕,立即她就对梁月成吩咐说:“立即要车,送马大夫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