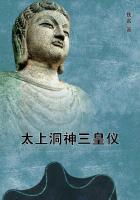梅掌柜抱一匹白纸马出来,责备伙计道:“火上房啦,还不快去干活。扎‘楼库’的秫秆不够了,去收拾一捆。”他见谢时仿问:
“先生您?”
“定一套寿衣。瞧你这儿很忙。”谢时仿说。
也不知道镇上何人驾鹤,买卖店铺几乎都定制了冥器,档次很高,要求精工细作。连吃百家饭的花子房,也定了冥器。梅掌柜的冥衣铺昨晚顾客挤歪门槛。
“梅掌柜!”铺内有人喊道,“皇宫的门安不上。”
“我去一下,您稍等。”梅掌柜说。
从冥衣铺出来,管家和徐德富朝孟记杠子房走去,路上他说:“怪了,不知谁家大出殡……”
徐德富也奇怪烧活儿(冥器)一夜间便火起来了,他绝不会想到这些冥器与他家有什么关系。
“家兄壮举实在令人钦佩。”杠子房孟掌柜拱手道。
“孟掌柜过奖啦,赌耍之辈何谈壮举?”徐德富说,“赌耍不成人,汗颜啊!
“徐兄,日本宪兵队长角山荣横行霸道,生杀予夺,谁人敢碰倒他一根寒毛还不得跪着扶起来呀。四爷敢和小日本动输赢,全镇谁人不竖大拇指。徐兄,请给小弟一次机会,这次送葬我们杠子房包啦,不收您一分钱。”孟掌柜要以最隆重的方式送徐德龙,说,“四爷大杠式,六十四人抬。今晚我们去亮杠。”
“德龙知道你们这样看他,九泉之下也会欣慰啊!徐德富不胜感激道。
这是亮子里镇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最隆重的葬礼。送葬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铭旌飘荡。
骰子石棺由六十四位杠夫抬着:杠夫头戴红缨黑帽,身着绿花驾衣,黄裤青靴,随司杠响尺的号令,抬棺步调一致、敏捷稳剑。
街口,两支队伍加入进来:一支由悦宾酒楼掌柜梁学深率领的鼓乐班子;另一支由棺材铺耿老板带领,手持“雪柳”、祭幛;“缝穷”女人、郝家小店郝掌柜、绸缎庄吕掌柜在送葬队伍中;王警尉衣衫褴缕手牵一男孩在送葬队伍中;鼓乐班子吹奏“黄龙调”,哀乐声声。送葬队伍滚雪球似的增大,每到一个街口、岔路,都有买卖店铺的人加入进来……角山荣着军服,伫立在宪兵队部窗户前向外望。送葬队伍从宪兵队门前经过,他面部肌肉抽搐,手按在军刀刀柄上。
送葬队伍塞满街道,人流如潮。全镇人倾巢出动,陆续加入。冥器骡车,与真车大小相同,车老板子挥鞭抬腿,活灵活现;白马一匹,跟班侍者一人,还有男女仆人……满街纷扬纸钱,白花花一片……徐德成这一路向西走寻找蓝大胆儿绺子,一个他没想到能遇见的人街西,富贵堂的大掌柜带领花子房的老少乞丐,抬着四只冥器的骰子,加入送葬队伍。
西大荒徐德成遇到了徐秀云,她的大红骡子突然蹿出柳条通。
“大当家的,”她俨然是个女胡子,带几分匪气。
“你这是要去哪儿?”徐德成问。
“找你。”她说。
徐德成一愣,似乎明白了什么,留下随他来的人,把她带一边说话,走进更深的柳条趟子里。
“山口枝子因你们而死。”徐秀云劈头盖脑地说。
“这?”
“她去给你们报信……”徐秀云讲了目睹日本人袭击运黄豆军车的过程,她说,“她怕你们不明真相,而让宪兵队的阴谋得逞。”
想想山口枝子死时的惨象,徐德成十分愧疚。
“我和蓝大胆儿有一面之交,他们决心抗日……”徐秀云说,她亲眼见蓝大胆儿绺子烧了日军骑兵的草料场,说,“我正考虑到他们绺子去挂柱。”
徐德成感激的目光望着她。
“那你还找蓝大胆儿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找,一定要找到他。”
“什么,你去打他们?”她误解道。
“不。”徐德成对她说了实情,已经派人秘密接触蓝大胆儿,联手消灭角山荣。他看清宪兵队长的阴谋诡计时,就看到蚌埠相争渔翁在后了,当他们消灭蓝大胆儿,日军在消灭他们。他说,“这事真得你去和蓝大胆儿深一步谈谈,他还有些犹豫。”
“好,我去。”徐秀云侃快答应道。
“谢谢你秀云。”
“三哥!徐秀云突然叫了一声。
“啊!”徐德成一愣,半天才缓过神来,问:“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你掉进捕狼的陷阱……”徐秀云说,“德龙对我说过,你左胳脯弯处有一块疤,是你偷谭村长家的海棠果被狗咬的。”
徐德成回想掉进捕狼陷阱摔晕后,刮破的衣服被两个女人换过,自然看到了身上的疤痢。
“山口枝子怀上了德龙的孩子。”徐秀云说。
消息令徐德成惊讶,日本女人山口枝子怎么和四弟还有这么浪漫的一节,除淑慧还有小香、秀云,四个女人的结局如何呢?山口枝子被杀,秀云流落荒原,小香沦落烟花巷,淑慧孤独凄苦地生活在部落点里。他谓然长叹道:“德龙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人各有志,随他去吧。”徐秀云不再惋惜,说。
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徐德龙已死,亮子里那场空前的葬礼他们没见到。
“三哥,你肯收留我吗?”徐秀云问。
徐德成沉吟,他迟疑的原因是想劝她回到德龙身边去,走马飞尘、风餐露宿的艰险生活她怎么受得了啊。
“三哥你别为难,不方便我单搓(单身为匪)。”徐秀云想到每个绺子的规矩不同,也许他们不收留女人。
“这件事过后再说,咱们先说服蓝大胆儿……”徐德成同徐秀云商定了下次见面的地点、方式,然后分头行动,他回到特混骑兵队露营地,徐秀云则去找蓝大胆儿。
草头子秘密从蓝大胆儿那儿回来,从胡子老巢回来。
“怎么样,有没有线索?”冯八矬子急忙上前探问。
“白挠毛儿(费力无所获)!冯队副。”草头子说,“没找到他们。”
冯八矬子悻悻走开,早晨徐德成出去前,叫他留下看好队伍,队长去侦查,留下副队长合情合理,他无话可说。徐德成他们走了大半天,他倒不担心他们借此跑掉,因为大部分人在,总不至于撇下他的众兄弟自己逃命吧。
“看好喽。”冯八矬子对身边的几位心腹说,将岗哨换成警察,防止其他人逃跑。他和角山荣约定好,有蓝大胆儿准确消息,立即派人回亮子里报告,待徐德成消灭蓝大胆儿,日军从后面再消灭徐德成这伙胡子,这盖头一层又一层,层层有玄机。算盘可谓打得不错,故此冯八矬子暗自高兴。
“大哥,给你。”黑暗中,草头子弟过来一样东西。
“什么?”
“摸摸,便知。”
徐德成摸一摸,是一串桃核,很光滑,说明串缀年代已久。
“有人叫我带给你。”
“嚄!徐德成再摸桃核串儿,数桃核的数量,十五颗,他猛然坐起文:“他人在哪儿?”
“和蓝大胆儿在一起。”草头子说。
草头子去见蓝大胆儿,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胡子大当家的介绍很简单,说是一位朋友。
事实上在商讨如何消灭角山荣宪兵队时,都是他在布置,头头是道。
“此人厉害……”草头子暗想。
“草头子兄弟,全听我朋友的吧。”蓝大胆儿说。
“大当家的,我问你……”草头子把蓝大胆儿叫到一边问,“他是什么人啊?”
“抗日队伍。”蓝大胆儿说,“我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抗日。”
草头子临回来时,神秘中年男子将一串桃核让他带给徐德成。
桃核串儿——护身符——徐家人的特别东西,四凤给自己戴在脖子的那个桃核串儿,至今还戴着。
“大哥,他是你二哥吧?”草头子说。
“是!”徐德成没否认。
“这串桃核是?”
“护身符。”徐德成说,“我大哥亲手穿的送给我们,每人一个……而且是十五颗桃核。”
他们等消息,为不引起怀疑,草头子不再去接触蓝大胆儿,等布置好后,定派人送信来。
“徐秀云在场。”草头子说。
“那一定派她和我们联络。”
果真,三天后,徐秀云送来消息,传达了具体的行动细节。
“该是冯八矬子为我们请人的时候了。”徐德成说,“二弟你今天出去,回来就说找到了蓝大胆儿的匪巢。”
“哎,我去。”草头子很快回来。
“怎么样?”冯八矬子问。
“找到了。”草头子说,“他们在月亮泡子趴风(藏身)。”
“明晚我们发起攻击。”徐德成说。
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连环套,日军利用胡子去剿杀胡子最后再消灭胡子,胡子呢暗中联手借机消灭日军。
冯八矬子派回去报信的警察夜半离开宿营地,站岗的胡子得到徐德成命令,假装没看见放他出去。
次日傍晚,徐德成朝天放两枪,高亢地喊:“弟兄们,鞴连子(鞴马),向月亮泡子,压!”
压!胡子都爱听这个字,每每大柜喊出后,他们便放开马缰绳,抽出匣子枪,勇猛向前拼杀。
马队来到月亮泡子北沿的沙坨上,徐德成朝芦苇塘喊:“蓝大胆儿,你为啥打歪了我兄弟?吐(讲)!”
“天狗,你投靠花狗子(兵),还有脸来摆阵头(评理),问你日本洋爹去吧!蓝大胆儿在芦苇荡未露面,回答道。
蓝大胆儿的狂话,不知真相的人认为激怒了徐德成,于是他虚张声势地边打枪边指挥特混骑兵队朝里冲:
“为大德字报仇,压!
胡子钻进芦苇荡立刻消失,只剩下冯八矬子一伙警察。
“冯科长不对呀!一个警察惊醒道。
“妈个B!我们上胡子的当啦。”冯八矬子气急败坏,说,“马上撤出芦苇荡去!”
日本宪兵和占大队长带领的警察大队包围了月亮泡子,数挺轻重机枪对准芦苇塘。
“队长,不要开枪!”冯八矬子喊道。
角山荣白色手套凌空劈下,顷刻间,轻重机枪,小型迫击炮一齐射向冯八矬子他们,芦苇被打着,月亮泡子被血火染红,燃烧中散发出人肉和马毛的焦糊味……就在这时,角山荣的背后顿然响起枪声……许久,枪声才平息来来,月亮泡子恢复了激战前的宁静,晨阳柔和的光辉给横躺竖卧的死尸镀上一层金色,干涸的血斑像一朵朵鲜艳的卷莲花,盛开在冬天的荒原上。
角山荣死在马背上,未瞑的双眼怅然盯着天上那轮圆红的东西,他的身旁一个死去士兵的刺刀下,也飘着那个圆红的东西……陶奎元从四平街警察局开会回到亮子里,才知道角山荣带宪兵队倾巢出动,去了月亮泡子。他清楚他们去干什么,胜利的果实即使不能亲手摘,别人摘自己在场也沾点荣光。
“梦天,跟我走!陶奎元叫上徐梦天道,“去月亮泡子!
两匹马出了城,马背上陶奎元说:“我们去观一出戏。”
“到月亮泡子看戏?”
“天狗消灭蓝大胆儿,皇军再消灭他们。”
徐梦天听到消灭天狗心给蜇了一下,他倏然想到匣子枪中压了八颗子弹。
月亮泡子变成一片灰烬,像遭受了天火一场洗劫;日军、警察的尸体横躺竖卧一地……“回去!”陶奎元调转马头往回跑,徐梦天紧紧跟上来,一枪把局长击落马下。
奄奄一息的陶奎元问:“你为什么杀我?”
“你死盯着徐家人不放。”
“谁跟你说的?”
“我三叔。”
“徐……德成……他、他果然活……活着……”陶奎元说仇人活着自己却死去了。
又一代徐家人徐梦天结果了仇人的性命,他毕竟成为以后岁月的主角,这与下面做的一件关键的事情有关——他朝自己左臂开了一枪,将陶奎元的尸体驮回三江县警察局……一个月以后,徐家人来祖坟地上坟。大小不同的坟包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徐德富、徐郑氏、丁淑慧、二嫂、梦天、梦人、四凤……给徐德龙坟茔烧纸。
坟前石碑上的积雪被烧纸烤化,露出徐德富亲自撰写的碑文:
吾胞三弟德龙,生于公元1901年夏丑时。一生无所事事,以赌为业。赢钱获命,终不成器,1938年冬卒,自备奇特石棺一口,六面刻有数点,棺形如骰子矣。他一生博塞与斯,死与斯,赌命也。相唤想呼日征逐,野狐迷人无比酷。一场纵赌百家贫,后车难鉴前车覆。
兄徐德富。康德五年冬吉日立。
春风情人一样抚摸亮子里镇,金灿灿的毛毛狗爬满柳树的枝头。有三件与徐家有关的故事在这个普通的春天发生,简记于此:
——从四平街警察局调来一个姓安的人任警察局长,徐梦天提升为警务科长。
——受南满抗日组织的派遣,徐德中秘密回到亮子里,做药店当坐堂先生。
——新任宪兵队长林田数马找徐德富,敦促他在獾子洞祖田上种大烟,徐家和罂粟是另一部书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