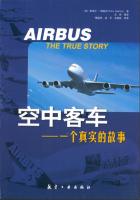如绪论所述,当前对上海港和宁波港的发展过程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大多数仅是对单个港口的历史进行考察,没有把港口的发展过程放在港口体系中,这样就很难把握港口发展的阶段和特点。而仅有的几篇探讨上海港和宁波港关系的单篇论文还不够深入。本章将从三个层面对两港的空间关系进行考察。第一节将打破时空的界限,在时间上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从唐朝至近代考察上海、宁波两港在长三角港口体系中的不同发展轨迹;在空间上克服仅仅研究两港的局限,把两港放在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中进行考察。第二节从内向化和外向化这一切入点来分析两港在开埠前后发展态势的转变。第三节从枢纽港—支线港的角度考察两港的空间关系,并引入基尼系数、增长偏移模型等数理工具对两港港口活动的集中趋向进行量化分析,最后把近代上海港的发展放在世界港口体系中进行考察,以期能更深刻地认识上海港在世界港口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至迟到南宋末年已经南移到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寻找货物进出港口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于是在长江三角洲涌现出许多港口,扬州、宁波、上海等港口成为各时期的首位港口。本节拟简述唐代至开埠之前长江三角洲首位港口的位移过程,进而在这个大的演变过程中把握上海、宁波两港的发展脉络。
一、扬州——唐代长三角的首位港口
自隋代修通大运河以后,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开始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由于距海不远,扬州的海上交通也相当发达,是当时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贸易港。
在唐代,今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由于濒临印度洋且有着发达的航海业,往往经海路乘船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经商,安史之乱后这些地区前来中国的海商人数有所增加。大中九年(855年),卢求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即成都),以扬为首,盖声势也”,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等等,都是对扬州商业繁荣的写照。唐后期的扬州与广州、泉州是当时我国海商较多的三个港口城市。黄盛璋认为扬州在唐代的位置,其情形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就国际贸易来说,虽仅次于广州,但就国内市场论,就要算东南第一商埠。
唐代长江三角洲的另一个重要港口,是今天宁波所在的明州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港正式开港,到唐朝后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其中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者在明州登岸,这是日本使船第一次到达明州港,也是明州港第一次接待外国船只。此后,日本遣唐使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开成三年(838年)两次在明州登岸,由明州经扬州、楚州、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到达长安。开成四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到中国,但两国的民间往来更加频繁。从那时起,到907年唐朝灭亡的七十年间,中国商人从明州港出发到日本贸易的就有三十多次。
尽管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确切地比较扬州港和明州港的繁盛状况,但综合上述有关资料,可以推测,明州的客商主要来自日本,扬州的客商则来自大食、波斯、日本等国,扬州是当时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又是中国南北物资转运的枢纽。在这种背景下,扬州作为长江三角洲贸易港的重要性应该在明州之上。由此可以认为在当时长江三角洲的诸港中,扬州港是最重要的港口,明州港是中日航线的重要节点。明州的地位之所以不如扬州,要归之明州介于扬州和泉州之间不利的港口位置,“日本南下之道,常为扬州所夺,而外商由广州北上扬州之道,中间已有泉州停顿,所以明州在唐代始终不能成为大港市”。
二、明州——宋元长三角的首位港口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扬州所在的淮南地区战乱频仍,扬州也遭到惨重的破坏,据说“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后在割据者杨行密的大力招抚下才慢慢得到恢复。但是,五代和北宋时期扬州在全国的地位已无法和唐后期“扬一益二”的盛况相比。此外,随着长江三角洲的逐渐发育,特别是今天的南通市及其以东地区的逐渐成陆,使得长江口从唐代扬州以东不远的今江阴一带,一直推进到接近今天的长江口。长江口的东移又使得昔日宽广的扬州—镇江间的长江流速放缓,河段日渐束狭,江心洲发育,不利于航行。到了北宋,位于扬州以西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市)逐渐取代了扬州的地位,成为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当时的江、淮、两浙、荆湖等路的发运使均驻在真州。然而,真州只是内河航运的中心,前来停泊的外国商船为数不多。
明州所在地区因长江的阻隔较少受到战乱的破坏,人口和区域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超过淮南。政治经济和自然地理面貌的巨大变化,使得长江三角洲的首位港口,开始从长江以北向长江以南转移,确切地说,是从长江北岸的扬州向杭州湾以南的明州转移。
北宋时期,朝廷把海外贸易视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一些贸易港口,包括在长江三角洲的杭州、明州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市舶司的兴废设置可以作为替代指标,以衡量港口在当时的重要性。
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繁荣地区的中心,可以通过杭州湾入海,又是大运河的起点。至迟在端拱二年(989年)杭州已经设立两浙市舶司。元丰五年(1082年)之后朝廷规定只有杭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发往南海的贸易船只,才被视为可以合法下海的贸易船。
尽管明州在唐代是重要的贸易港之一,但在北宋设立市舶司的时间仍稍晚于杭州。淳化三年(992年),两浙市舶司移到明州的定海县,次年又移回杭州;到了咸平二年(999年),在杭州和明州两地都设立市舶司。明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发展很快,贸易地位迅速上升。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也就是把去日本、高丽的唯一合法港限定在明州。两年之后又补充道:“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商舶舡者,以违制论”,即明州也是去南海船舶的合法始发港之一。
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因靠近首都,地位更加突出,为南宋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明州、杭州)之一。杭州尽管是首都所在地,但由于钱塘江潮急浪高,暗礁密布,港口条件不如明州。当时“商舶船只怖于上潭,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也就是说,船舶一般先来到明州港,再经余姚江和浙东运河到达杭州,明州港实际上承担了杭州外港的角色。到了绍熙元年(1190年)光宗继位以后,朝廷禁止商船停泊在附属于杭州的澉浦港,此后杭州也不再置市舶司;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继位以后,朝廷又禁止商船前往江阴、温州、秀州,原先这些地方设立的市舶机构都撤销了,只有明州一处尚有市舶司,“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南宋改明州为庆元府)得受而遣焉”。说明此时明州(庆元府)是长江三角洲唯一可进行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港口。
元代庆元与泉州、广州并称全国三大港口,虽然泉州、广州的地位特别突出,但在长江三角洲,庆元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港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在庆元设立市舶司,同时又于上海、澉浦分别设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又于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在元朝于沿海设立的七个市舶司中长江三角洲竟占了四个;但是,到了大德二年(1298年)以后设立于澉浦、上海以及温州的市舶司都被并入庆元市舶司,直隶中书省,而杭州市舶司则被并入当地税务,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庆元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性。
除了宁波和杭州,在长江三角洲,青龙镇、上海镇、刘家港等港口也曾有过比较繁荣的对外贸易。唐宋时期,长江口的主要港口设在青龙镇,后来一迁上海镇,再迁刘家港,第三次迁到今天的上海市区。金立成、邹逸麟、茅伯科、张修桂等人对长江口港口位移过程都有较深入的研究,笔者对此不再展开。
宋代鼓励发展海上贸易,吴淞江下游的江湾镇、长江口南岸的黄姚镇、钱塘江口的澉浦、长江南岸的江阴等也都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一定的繁荣局面。然而,所有明州以外的港口,甚至位于南宋首都所在地的杭州港,都未能撼动明州港在长江三角洲的首位港口地位。
三、双屿港——明代私人贸易港的勃兴
明代的对外贸易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市舶司进行的朝贡贸易,一种是不经过市舶司的私人海上贸易。朝贡贸易是由外国官方派出,以进贡名义,通过市舶司进行的贸易,而私人贸易是未经政府许可的违法贸易。因此,明人说:“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司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
明初,市舶司设于太仓州黄渡(在今上海市嘉定区黄渡),不久因朝廷担心“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1374年),又于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其中宁波接待日本、琉球(在今日本冲绳群岛)的船只。明朝认为“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而“日本叛服不常”,只许十年一贡,每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后期虽放宽到十年一贡,每次三百人,船只限定为三艘。从1404年至1547年,共计143年中,日本船来宁波17次,明朝去日本的船仅8次,足见宁波港之萧条了。
明前期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极力压制的做法。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下令禁止民间使用来自海外的番香番货,严禁私人海上贸易。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沿海人们为重利所诱,违禁下海贸易。由于朝贡贸易对外国船只的来华时间、船只数量和人数均有种种限制,贸易规模较小,远远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于是私人贸易成为海上贸易的主流。洪武至隆庆两百年间(1368—1567年)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并不是市舶司所在的港口,而是位置比较隐蔽、官方控制比较薄弱的私人贸易港口,这种港口南从广东的东莞,北至长江三角洲的丁屿、马迹,不下数十处。自嘉靖初起,最重要的私人贸易港开始向宁波府的双屿港(在今舟山市普陀区西南部的六横岛)转移。
双屿港在1526年到1548年的二十多年间,发展成为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日后被藤田丰八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中国商人和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在此频繁出入,商业极为繁盛。葡萄牙旅行家宾托(Ferand M endea Pinto)曾留下双屿港繁盛的记载,并认为“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他的记载被许多国内学者引用,而外国学者则戏称他为“小说家”,认为他“谎话连篇”。但不可否认,中日葡三国商人确实曾在此进行过几十年的贸易,其后捣毁双屿港的户部尚书朱纨曾说:“内地叛贼常于南风迅发时月,纠引日本诸岛、佛郎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内地奸人交通接济,习以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胜言。”1548年,四月初七双屿港被攻破,五月十七朱纨登临双屿,发现岛上“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虽未表明双屿港的位置,但倭寇入宁波的线路清晰可见。
双屿港被捣毁后,长江三角洲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仍保持相当的规模,海商首领王直率众改往烈港(在今浙江定海县西北),势力渐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领之……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由于前往贸易的中外商人众多,地方官唐枢上书督府,要求在定海设关开市,允许中国商人在定海验关收税后再赴烈港贸易。
四、上海港——开埠前最大的内贸港
明代繁荣的私人海上贸易,到了清初因严厉的迁海令和禁海政策而被压制下去。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由于台湾郑氏集团降清,禁海令得以解除,海上贸易重新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就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而言,不仅原有的海路都得以开通,而且开始有海舟经过山东登州海面,直趋明代“通商未广”的天津和奉天(今辽宁省)的海港。江浙海船开始赴奉天贸易时,“岁止两次”,几十年后增加到“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与各国的贸易同样较为兴盛,“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在此背景下,上海港开始得到发展。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凡运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舢舻相衔帆樯比栉”,上海商业的繁荣程度不下于当时号称繁盛的仪征(今属江苏)和汉口。
刘家港在明代和清前期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繁荣,明永乐年间郑和数次下西洋均从这里起航。它与江南最重要的城市苏州有浏河直接沟通,为苏州通海之门户,“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范金民认为刘家港是元明以来江南最大的港口,刘河镇也是清代前期江南最大的饼豆市场。刘家港是否是元明以来江南最大的港口值得讨论,因为没有同质文献记录刘家港和宁波港等的相关情况,因此很难进行比较。但刘家港和上海港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则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刘河镇记略》等文献中,从中可以确知刘家港的地位在很长时间内都超过了那时的上海港。刘家港衰落后,明代经过大力整治的上海港取而代之,成为太湖流域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沙船、鸟船合收上海一口。由于贸易便利,鸟船在福建和上海之间的南洋航线增加了航次,上海也因位于南北洋航线的交点,为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口岸打下基础。刘家港衰落、上海港兴起的过程,本书前引张忠民、杜瑜、戴鞍钢等人的论著多有研究,不再赘述。
乍浦港位于上海港的南端,直接面海,西距嘉兴府城不远,有河道相通。元明两代,海运往来曾有一定的规模。自清代康熙年间海禁放开,海船接踵而至,大多往返于华南及日本航线。但由于偏离长江入海口,与江南经济富庶地区的交通联系不及刘家港、上海港便捷,港口外又有浅滩横亘,退潮时“商船难拢口岸”,乍浦港的贸易规模终受制约,不少原先停泊该港的闽广商船,后来移至上海港。
刘家港、乍浦港的衰退,使开埠前的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主要出海港的地位越发突出。李星沅对1841年的上海港、乍浦港、刘家港等港口情况作了对比:“悉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有洋商四家半。上海县外为黄浦,即洋货拨船(如沙船等名色)停泊之所,距大洋九十余里,洋船不能深入。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由此可知,开埠之前,乍浦港、刘家港的发展都不如上海港。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海港崛起之前,宁波港是长江三角洲最主要的贸易港,上海港之所以能取代宁波港,主要归功于北洋航线的迅速发展。清代的沿海航线分南洋、北洋两种,“出(上海)吴淞口,迄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迄北由通(南通)、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上海和天津是北洋航线的南、北两大中心,人称“海船南载于吴淞,而北卸于天津,两地为出口入口之总汇,实海运成始成终之枢要”。
宋元明时期,由于屡受战争和黄河决溢改道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日趋衰落,人口增长裹步不前,南北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到了清代,随着美洲作物在北方的广泛传播,人口大增,商品生产出现了宋明以来没有达到过的繁荣程度。东北的初步开发使豆麦余粮成为国内重要的流通商品,而乾隆年间以后,南方商品化农业大量需要北方的大豆、豆饼用于施肥。这样长期备受冷落的北洋航线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行驶在北洋航线的船舶除了部分南方的鸟船外,主要是吃水浅适应北方沿海水浅礁硬特点的沙船,上海是沙船的主要聚集地。聚集在上海的沙船约3500—3600艘,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海禁后“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万余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进出上海的南洋海船多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以及东南亚各国。到了嘉庆年间,“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巨舶……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云”;“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指南洋群岛)、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加上通过苏州沟通的长江航运,上海成为“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随“阿美士德号”来上海考察的胡夏米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初上海港的繁荣情景:“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一到这里,我就对入江船只的数量之巨叹为观止。连续几天,我试着统计一下,结果是7天中,经吴淞驶向上海,100吨至400吨不等的船在400艘以上。在我们停留之初,多数船只是来自天津和满洲各地的北方四枙沙船,所载货物多为面粉和大豆。但在我们停留的后期,福建船源源而来,每天有三四十艘,其中不少来自台湾、广东、东印度群岛、交趾支那和暹罗。”
咸丰八年(1858年),何桂清奏称:“江苏一省,精华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称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贩运,逐十一之利也。”时人认为上海在开埠之前繁盛的原因是“由于沙卫各船贩运南北货物,往返数千里,咸转输于上海一隅。沙船盛而豆米油麦土布南货各业皆盛,而沙船之转输贩运益日出不穷,是固相为维系者也。当其时,浦江帆樯相接,往来如梭,船之利于行者,岁每五六次,其不利于行者,亦三四次”。沙船“往来闽、广、鲁、直一带,载南货而北,又载北货而南,一转瞬间,获利倍蓰”。上海码头,“起初的兴旺,就全靠沙船,集市此地。把稻米运到北方,把棉花杂货装到南方。那时船只不下三四千艘”。陈子彝也认为北洋航线非常重要,其中豆业是中心:“上海开埠前交通运输不得畅流之际,商业以沙卫船商号为巨擘,豆业更为历史之中心。”在开埠初期,北洋航线的重要性也超过了南洋航线。1845年6月15日传教士施美夫等人进入长江口,发现“南行的船只寥寥无几,而北上的出口里,满载的帆船林林总总,显然是前往山东及更北的省份”。在此背景下,上海港迅速成为长江三角洲甚至中国最重要的内贸港口。
根据樊百川的估算,鸦片战争以前,每年进出上海的北洋航船和闽、广、浙的海船,以及长江航船和江南各处及本地内河客货船,当不下300万吨;他认为上海港这样巨大的吞吐量不仅为国内各港口所不及,即便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亦可纳入大港之林。在开埠之前上海港已经是我国最大的内贸港。戴鞍钢认为开埠之前的上海港从属于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经济区,担当着该区域出海口和转运港的职能,与其他传统商港并无二致,对上海港的地位不应估计过高。虽然在港口功能上海港是苏州的外港,即上海港承担着苏州货物进出的功能,但是港口功能和港口规模之间并不矛盾,外港同样可以有很大的规模,因此,他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鸦片战争前,虽然受清朝规定的一口通商的限制,与西洋的贸易只可在广州进行,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物资生丝、茶叶却多产自江浙地区,长途运输导致丝茶价格大大提高。由于这一原因,1840年以后当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时,我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在数年后便转移到上海。此后,我国最大的国内贸易港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一直都在上海。
五、首位港口从长三角两翼向中心的位移
纵观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唐朝时扬州是首位港口,宋元时期宁波上升为首位港口。明代虽然海上贸易处于非正常状态,但也显示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趋势,宁波外侧的双屿港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自然也是当时长江三角洲的首位港口。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以后,上海港发展迅速,并随着北洋航线的兴盛逐渐发展为本区域乃至中国最大的内贸港。近代开埠之后上海港发展更为迅速,不仅贸易量远远凌驾于其他港口之上,而且还将同一港口体系内的其他港口变成自己的支线港。
通过上述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的首位港口,大体上呈现出从三角洲的两翼向中心转移的趋势,先从长江北岸的扬州转移到杭州湾南岸的宁波,又从宁波转移到上海港。这种空间变化,既是长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变成陆地并渐次开发的结果,也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船只航行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由于长三角的海岸线不断东移,使得扬州远离长江口,不利于海上运输,上海港则接近海上交通;扬州港和宁波港位于长三角的两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而经济地理的原则是要节省运输成本、便利各地的运输,最佳的区位是其运输集散地位于区域的几何中心。上海港虽不位于长三角的几何中心,但处于长三角海岸线的中心,通过吴淞江可以很方便地和苏州沟通,并处于三角洲的一个顶点,便于向三角洲各处集散货物。尽管唐代的扬州港、宋元的宁波港,甚至近代地位极高的上海港,在不同时期的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上海港甚至将其他所有的港口都变为自己的支线港,但这并不影响其他规模较小的港口的存在,这些港口仍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Taaffe等人对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港口体系的研究及Rimmer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港口体系的研究,都显示在港口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某一港口的发展,其他港口会趋于衰落。但是,长江三角洲从来都没有出现一港独尊、众港皆灭的现象,这和Notteboom对1980年至1994年间欧洲大陆的港口体系的研究结果相似。Notteboom认为港口体系并不是先减少到一个或几个较强的中心,然后再由小港口对原有的港口体系进行挑战。由于当地交通或政策的缘故,小港口在港口体系中继续存在。
到了近代,上海港在长三角港口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在港口体系中仍然呈现“一体两翼”的格局。南翼的宁波港虽然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但在浙江省内仍是最重要的港口,即使在温州、杭州相继开埠及与上海港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绝对值仍在不断增长;而在北翼,镇江取代扬州在历史时期中的地位,成为近代江轮进出长江的门户。船只由上海起程入长江或从九江、汉口出长江,一到镇江,“必在该口湾泊,并报明领事官、镇江关方准过口”。
近代镇江的贸易地位很高,就货运总值而言,在长江流域诸口岸中,镇江与上海港的联系紧密程度仅次于汉口。1887年的镇江领事报告认为镇江位于许多流贯南北的河道的交叉处,其位置对于发展贸易很理想,河南全省的洋货完全由镇江供应。虽然河南可以在上海购买洋货,但没有镇江这一条约口岸,洋货就无法大量深入。济宁州、徐州和海州等也从镇江运入大量布匹。自开埠到20世纪初,镇江的对外贸易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海关贸易报告提供的数据,1906年贸易总额为35948965两,创历年进出口贸易的最高纪录。之后随着沪宁、津浦铁路的相继通车及港口的淤浅,对外贸易渐趋衰落。上海港、宁波港、镇江港分别位于长三角的三个顶点,上海港是长三角港口体系中的首位港口,成为枢纽港;宁波港和镇江港为上海港的支线港,是港口体系中的第二层级;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是民船集中的地方,是港口体系中的第三层级,各层级的港口构成既协作又竞争的“一体两翼”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