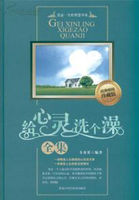我躲在旅馆里,不愿回公寓。赖了几天,觉得这不是好办法,决定回去面对现实,即使要搬家,也有必要当面说清楚。
下班回到公寓,客厅里昏黑一片,没有人声。我打开电灯开关,看到一切如初,好像未曾有人动过似的,唯有空气中流淌一种浓郁的各种化妆品混合的香气。
也说不清,那天晚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陈佩琪又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再将陆竞城拉到身旁。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未到分崩离析的程度,小吵小闹小误会,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和好就和好了。
而陆竞城,他不过是偶尔出轨的列车,我是一个与他有缘的搭车人。“看来我真的要搬家了。”我抚拭屋里的一物一件,心里溢出不舍之情,说不清是我太过留恋居住于这里的舒适,还是怀念那个背弃自己而去的男人。想到要别离,眼睛就湿了。我的喉咙里始终苦涩,像含着一枚苦果,就算过去许多天,我还是不能对这个事实保持淡定。
可我必须走,再多的眼泪都要吞进肚子里,不让陆竞城为难,也免得三人难堪。敞开卧室的门,收拾行李,把原来从皮箱里搬出来的东西,再一件件地收回去。但愿能恢复到原来的我,坐看云起空山,闲听庭院雨落蕉叶,岁月静好,不再想他。
在公寓里等了几天还不见陈佩琪,不知她去了哪里。我只好主动联系,问她晚上何时回公寓。
在电话那头,陈佩琪只字不提那晚的尴尬事,好像我们之间不曾发生过什么,还用疑惑的语调问我有什么事。我直说:“没什么,只是想跟你聊聊。”她说还有应酬,需要到十点后。
我想我愿意等。这样的等待不是第一次,但愿是最后的。
通完电话后,我把行李停到客厅里,表示我将去远行,不再回来。但是,不管去到哪里,过去多少年,我想我都不能淡忘这间公寓。在这里,我遇见终生难忘的男人,与他经历过千回百转的爱情,辛酸过,甜蜜过,这样就足以到老的时候,拿出来告慰寂寞了。
至于结果,并非所有难忘的爱情,都会有美满的结局。
陈佩琪回来得还算早,晚十点半进门。没喝醉,大脑清醒,穿得妖艳动人,浑身散发出酒精和香水混合的气味。
见到我,她的神情和往常一样友好,没丝毫波澜。很自然地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展开双臂,跷起二郎腿,很放松的样子。看到放在门口的行李,她有点吃惊,声音很轻地说:“怎么,你要出差? ”
我难堪得要哭了,不知如何启齿。她不可能对那晚的事无所谓,只是在装,不愿与我当面撕破脸皮罢了。不明白这是出于为人处世的原则问题,还是她在玩花招,逼我老实招供。
看她那不以为意的作态,我再也忍不住了,将准备好的结算清单递给她,用一种哀伤的声音说:“我要搬走了,费用我已按离开的那天结算好,你过目。也不知还需要什么手续,那就请你指教了。”陈佩琪惊讶地抬了一下眉毛,动作迅速地接走我递来的单据,难以置信地看了看,鄙视似的噘了一下嘴。我趁机致歉,“佩琪,我感到万分抱歉。不再打搅你们。 ”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她白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走,也是你自己先提出的,我可没伤害你,也没逼你,别到时候忘了又去找人哭诉。 ”
我有些懵了,不明白她为何要这样说,再次澄清道:“没错,一切都是我决定的。 ”
她挺直腰,坐端正了,酸溜溜地叹道:“刘舒,我看你就别走了,这房子不错,你就好好在这儿住吧。 ”
“不,我走。”我很坚决地说,却不敢抬头正视她。
“你最好还是留下,”她说,“因为我要走,搬离这套房子。 ”
我惊骇,抬头看她,难以置信。她竟然提早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凭我对她的了解,这个女人才不会心怀善意地为别人着想,她要搬走,必定有其他原因,有可能这是陆竞城的意思,他要去到另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去,远远地躲着我,遗忘我。
“因为我要回家了,刘舒,”她狐媚地笑,“你以为你在和谁暧昧呢,那不是别人,是我的丈夫。 ”我非常震惊,眼睛都瞪圆了,有种想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的愕然。
“我们早就结婚了,是在四年前的秋天。”她说,“只是一直没有公开消息,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戴钻戒。不过,这种生活并不美好,我们决定重新开始,给彼此戴上婚戒。”她伸出左手,“你看,昨天他为我戴上的。 ”
她无名指上的钻石闪烁出的光芒,就像刀子割伤了我的心,让我的惭愧更加剧烈,懊悔更加惨白。
在陈佩琪幸福的笑容面前,我全傻了,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这对夫妇居然在世人面前,完美演绎了一场逼真的非婚生活,把我这个整天与他们同住屋檐下的在读博士都蒙晕了眼,仿佛一个稀里糊涂的盲人,不曾把一些疑点看在眼里。原来,陈佩琪不在公寓住的时候,就是回他们的爱巢,她所谓的回家几天,不是回娘家。可是,他们为何要对世人隐瞒婚姻的身份,难道暧昧的关系才适合保持爱情的新鲜和长久吗?
而陆竞城,他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张开怀抱只是逢场作戏,难道他的亲吻是一种****的冲动,难道,他是个厌烦了婚姻的烟火味,逃出围城去走一走的孩子?
我的心全乱了,事实完全与我想象的背道而驰,之前那些“为了他”的高尚情怀,被陈佩琪这三言两语打击得灰头土脸的,反过来,只能嘲讽自己是个大傻帽。
这下,我更觉得对不起陈佩琪了,神情讪讪地说:“佩琪,说一句老实话,你到底恨不恨我? ”“恨,”她干脆利落地说,“连这种事都不恨,那就不是女人了。 ”
这话让我难受极了,像被泼粪一般,浑身龌龊,连自己都嫌臭。可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宽容,通情达理。“既然恨,”我起疑地问,“那你为何进门的时候不骂我,或者是生气地跟我打一架?”我真的希望她别对我假装若无其事,而是凶神恶煞地嘲讽我,羞辱,诅咒,威胁……怎么样都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摆出一副菩萨面,佛祖心,假惺惺地让我羞愧,自己折磨自己。
可陈佩琪却哧笑,“我哪里敢呀! ”“怎么不敢?”我都被她的笑声弄糊涂了,“你也知道,我是最不擅长吵架的。 ”
“不行,不行,为了社会和谐着想。”她隐晦地说,然后把话题一转,“时间也不早了,我还要赶回家,我大概两天后来搬东西,到时候提前通知你。我走后就会有新的住户来,我希望你能替我帮房东把这房子维护好。”说着她站起来,舒心地呼了一口气,山河一片大好的感觉,用无比温馨的声音对我说:“我走了,刘舒,你是个好人,我清楚,也希望你能好人当到底,给大家安宁。 ”
她的意思是希望我忘掉陆竞城,不要再去破坏他们的婚姻生活。
那晚,陈佩琪走后,我就像被雷电击傻的呆子,僵住了。不知是该悔恨地恸哭,还是该疯癫地笑,麻木不觉地坐在沙发上,整整一夜。
也不知是哪个时刻,我突然歇斯底里地哭起来。窗外狂风呼啸,冷意袭人,月亮都知人间事,早早地为我黯然而去。宁静的世界,其实是如此错乱。触手可及的爱,其实真假难辨。原来我多么傻,以为只要有爱就有明天,而此刻,我只想抱着绝望投海自尽,获得来自天堂的上帝的抚慰。
两天后的周六,下着绵绵冻雨,不是个好天气。陈佩琪坚持搬家,因为有住户下午搬进来,耽搁一天也不行。
那天早上,我闷在卧室里不吃不喝,失魂落魄地背对着房门坐在地板上,窃听外面的声音,从中去联想那些无言以对的情景。
他终究还是来了,客厅里满是他的声音,总听到他说:“来,这个让我来……你别管,由我处理……你拿那些小东西跟上来就行了。 ”温柔的男人,也给过我疼爱,在夜里亲吻过我,刮着我的小鼻子好声哄:“今夜好梦,要梦见我。 ”
是的,我拥有过,而今还奢望什么?世间万家灯火,有人哭也有人笑,这就是生态平衡。就好比狮子吃掉斑马幼儿,角马踩死同伴过河,黑熊偷吃蜂蜜越冬,他人的幸福,总要建立在某一种痛苦之上,皆大欢喜都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