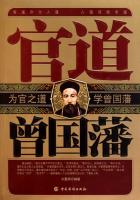我是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对哲学只是一知半解;了解的哲学知识还是40多年前大学的哲学教材书给的。脑子里的哲学概念不少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新的发展知之甚少。但这十几年来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常常不由自主地同哲学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觉得十月革命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往往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哲学原理有关,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必须从世界观上、从哲学上解决问题。
一、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
整整100年前,列宁写的《怎么办?》一书,其中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的“灌输论”。他强调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书中提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的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列宁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自发论,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这对于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以布尔什维主义武装的共产主义政党,对列宁这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偏差,产生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脱离实践去谈理论的指导作用,脱离人民群众去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有时不能摆正政党、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结果离开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政治上形成了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领袖个人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权的权力体制和工作机制。
这里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相互关系问题涉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程度是同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正确程度成正比的。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他们的接受程度去谈理论的指导作用,就容易搞唯意志论,就难以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
80多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就因此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在“左”的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和时期,掌权者实际上是在反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旗号下,把“左”的政策强加于社会,强加于人民,并以“阶级斗争”作为武器,搞政治运动、大批判、大清洗来维持这种错误。而人民群众总是以各种形式的“自发”的斗争来抵制这种错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在执政的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正常、紧张,甚至尖锐对立的地方和时候,从总体上说,人民群众总是对的。1976年中国发生的“四五”运动,便是最典型的事件。20世纪50—80年代,波兰先后发生三次危机,新上台的党的领导人在总结教训时,总是正确地指出,人民在事件中所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可惜由于体制和工作机制没有重大改变,他们上任后又不可避免地重犯前任的错误。
这种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其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其作用往往是通过“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代表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也常常是“自发”产生的。诚然,这并不是说“自发”的东西体现了规律性,“自发”产生的新生事物,有其不成熟性、不完善性,需要爱护、扶植、助长。也正是这个原因,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党的领导、党的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首先就在于善于发现、集中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总结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支持、扶助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表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如果忽视、轻视、无视这些新生事物,甚至把它视为“异类”,这就会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党要代表“自觉性”,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从根本上失去动力、方向和基础。
苏联东欧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之一,就是长期对人民群众的“自发”要求和愿望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自命不凡,似乎自己是真理的化身,结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灌输”方法,而人民群众对那些脱离实际的说教总是提不起兴趣,结果丢失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武器。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滚滚袭来的时候,他们不能用正确的理论战胜其他各种不正确观点,也无力引导群众的“自发运动”朝正确的方向走。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举起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大旗,批判了“两个凡是”,尊重、支持人民群众改革旧体制的首创精神,肯定、推广农民“自发”搞起来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邓小平同志以十分鲜明的语言提出,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这无疑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典型范例。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群众的实践经验,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总结、提高,变成党的方针和政策。
二、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正确地把握和处理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事关事业的成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原理,建立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从苏联开始,长期忽视社会的统一、协调和合作的意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似乎社会的发展就是斗出来的。斯大林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提出共产党只有打垮小资产阶级党派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才能巩固和发展、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等错误观点。毛泽东把这种观点进一步理论化了,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论断。在政治上,国内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革”时期发展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均在“打倒”和“横扫”之列,知识分子则统统姓“资”,是改造对象,“小资产阶级”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要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国际上就是打倒帝、修、反(各国反动派)。总之,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天下。这种极“左”的理论和路线的危害已是尽人皆知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当然是充满冲突和斗争,但是没有统一、联合、妥协、和平,就根本谈不上发展。
2002年10月,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发了中国传统和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他说“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向国际社会推出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和为贵”、“和而不同”,反映了东方共产党人在不同的两个时代、两个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哲学,表明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动力的不同理解和把握。
这里有必要重温恩格斯晚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著名的“合力论”。笔者常想,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如果能深入研读这封信,可能是很有教益的。革命、建设,动力问题十分重要。社会向前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动力就会有反动力,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对的社会力量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会存在,这当然就要斗争,要克服,要排除。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动力从来就不是一支纯粹又纯粹的社会力量,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说,是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共同的事业,推动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各个阶层、集团,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其目标和愿望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其行进的方向是不能完全一致的,有的偏“左”一点,有的偏右一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摩擦、甚至冲突,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但他们都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发挥其作用。形而上学的发展动力观,都要求这些阶层、集团在思想、言论、方向上完全一致,在政治实战上就只能搞匈牙利拉科西的“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极“左”政策,把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即使是落后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甚至是反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他们的意志也加入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的总的“合力”。这种方向不同,甚至相反、对立的力量同样是构成整个意志“合力”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有这种方向相异的力的加入,才造成历史发展的曲折以至于暂时的倒退。但对于发展道路上的“阻力”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马路上的大石头,要排除、要搬开,否则就会翻车;但不是所有的“阻力”都不利于发展,有的“阻力”恰恰是防止滑向深渊的防滑剂。小雪化后,冻结成冰,骑车人常常滑倒。此时我们特别感谢沿街一些好心人,他们在马路上撒上炉灰、煤渣。他们就是为行人增加路面的阻力和摩擦力的。可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从高层和普通百姓有不少这样的好心人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遭到“横扫”和批判。这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屡屡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渐进和飞跃
这也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没有长期的量变的积累,事物的质变、飞跃就不可能发生,也就不可能有发展。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左”的政策的突出表现就是急于求成,实际上否认了事物的发展需要有长期的量变作为基础,把任何主张渐进、改良都视为“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斥之为“庸俗的进化论”。这便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超阶段的理论根源。而“超阶段”的错误则是80多年来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破坏最为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的“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在1958年宣布“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掀起大跃进,等等,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少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和活动家常常对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又估计过高,因而产生急于过渡的思想,制定高指标和赶超(发达国家)战略,然后采用强迫命令的做法,用权力来推进战略的实施,而下层则用浮夸、虚报来对付,这就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党内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的风气。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总结了这一历史教训,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成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是我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四、关于平衡论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平衡”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由于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危机。自然生态的破坏、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失衡、南北差距的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在不断接近、融合过程中引起的不协调和冲突,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诸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导致旧的平衡的破坏,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根源。
现在城市里有中高收人的中老年人不少人面临健康危机,也是身体内部失衡所致,首先就是饮食不平衡,主副食、动植物食品、细粗粮比例不合理、不平衡。
哲学上,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何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就是因为矛盾双方’或体系中的结构有合理的比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长期以来被强调的是不平衡的绝对性、有条件性,平衡的暂时性、相对性、有条件性,而往往忽视了相对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条件”。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平衡和不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持续、不全面,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其实,在十月革命后,有一位了不起的理论家就试图阐述“平衡”在工人阶级执政后的意义,并且提出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针。这个人就是布哈林。布哈林在阐述平衡论时虽然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但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不能否认的。他提倡各种经济成分要“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用经济的、和平的办法逐步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他提出工人阶级执政之后,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要用自己的国家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和平。特别是在苏联用超经济的力量搞高速工业化时,他强调农、轻、重要协调发展,警告不要造成比例失调。但布哈林的“平衡论”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斯大林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通过严酷的阶级斗争手段,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工)的方针,造成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很紧张。
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又处于备战的条件下是十分必要的。但把它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的长期适用的方针就不对了。
鉴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曾经从理论上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的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对农轻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个人种种关系,都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不能“太不平衡”、“都必须兼顾”的方针。这些重要观点可以视为是纠正了笼统否认“平衡论”的偏差。
今日的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又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平衡”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便是根据事物发展过程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协调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几对关系,其意义十分重大。
五、关于适度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要处理好一系列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如党群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民主与集中、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理论与实践等等关系。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处理这些关系往往不是简单地划清“左”与右、姓“马”与姓“修”、姓“社”与姓“资”的界限问题,问题常常出在“过”或“不及”上,尤其是过火、过“左”、过急、过快。所以,掌握“适度”原则,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的重要领导艺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度”就是质与量的统一,是保持一定质的量的界限。所以处理这些关系必须“心中有数”,“掌握分寸”,求得平衡。比如,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如何把握“度”,影响极大。不讲场合和条件,一味强调稳定,而不是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稳定”可能就是掩盖、捂住矛盾,是表面的、虚假的,使社会潜伏着危机,就像勃列日涅夫时期那样;脱离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鼓吹和推进改革,以为改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为改革是发展的惟一动力,就会破坏稳定大局,最后可能因失度而导致全面失控,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使改革之车陷人泥潭。中国二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寻求最佳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在新的基础上的稳定。
综上所述,从哲学上讲,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合力论、适度论,正确对待渐进论、平衡论、“自发论”及其相关的“灌输论”。这是一个总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个总问题就是:历史上过“左”的政策的思想理论根源、哲学根源,在于对不发达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难度和长期性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可能胜利估计过快、过于简单,想更多地依靠人的意志的力量、理论的作用,对社会发展必然存在的长期的量变过程失去耐心,企图依靠少数人、用政治权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来推动,期望“一天等于20年”,想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中改变几十年,乃至几万年形成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运转机制’结果许多问题把握不好“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可见“适度”之重要。
既然是“适度”,自然就要防止“过”,也要防止“不及”。在反对一种倾向性时,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老话现在讲的不多了,其实都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总结上述历史经验,并不是说,可以贬低自觉性、理论指导的意义,而是说,正确的理论并非脱离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实践而产生的;并不是说,可以否认“飞跃”、“质变”的意义,而是说,“飞跃”、“质变”必须有长期的“量变”的积累作为基础;并不是说,可以否认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因为不打破旧的“平衡”,事物就无从发展,而是说,没有相对的平衡,也就没有事物的稳定和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否定事物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双方摩擦、斗争的绝对性,而是说,没有统一、联合、妥协、和平,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进步和发展。但是,和平、合作、统一总是要通过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甚至通过不可避免的斗争才能取得,比如,我们讲“和为贵”,人家不同你讲和怎么办?它就是要搞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咄咄逼人地要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和社会模式,所以,同它理论、同它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