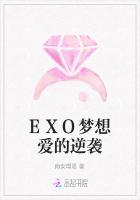一大早,陈惜惜五点就起床,熬了稀饭,做了小菜,先侍候儿子吃过,送儿子去了幼儿园,又拎着两只保温盒,驱车来到医院。先到康复中心给公公送早饭,又到骨科病房给婆婆送早饭。
从医院出来的她,又赶往墓地去做“一七”。
不必让儿子来。他才四岁,太小了。陈惜惜29岁才生下了浩浩,自然当掌上明珠般疼着。爸爸出的事儿,他还不太懂。或者说,懵懵懂懂的,对死亡还没有明确的概念。治丧那几天,儿子让保姆带回保姆家里去,每天照样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们玩,这是陈惜惜的意思,也是公婆的意思,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家里面的悲伤场面波及那颗幼嫩的心灵。事儿过完了,儿子被保姆带回来,再谈到爸爸,他就知道,爸爸出远门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偶尔,他会思念爸爸。思念爸爸的时候,他有属于自己的方式,比如,折一只纸鹤,画一幅表达心意的图画。再比如,把一堆玩具整理整齐了,保存好,等爸爸回来后一起玩……成人的仪式,就不必强加给他了。
做“一七”,也没有和公婆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身就是一大悲,能不让老人直接面对的,就尽可能让他们回避。可她却没想到,在墓园,撞见了春风的母亲,自己的婆婆。
真是意外。婆婆扭伤的腿还没有好利索,早上在医院里,看着她吃粥,她什么都没说。儿子的事一句没提,陈惜惜没想到,她会自己来。一定是打的来的。既然一定要来,为什么不肯吭一声,儿媳的车就不能捎她来吗?不就一句话儿吗?对儿媳开个口,就这么难?
婆婆拄着一根拐棍,让人搀扶着。搀她的妇女,正是陈惜惜为婆婆在医院花高价请来的女护工。婆婆在儿子墓碑前坐下,老泪纵横,从拎来的庞大的纸袋里,一摞摞掏出从医院门口的寿衣店买好的冥币、纸花,用打火机一把一把地点燃。看来,婆婆只是扭伤了腿,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来为儿子做“一七”,也是早就准备好的。由于行动不便,一定也是托人买的这些东西。
受了婆婆的感染,陈惜惜双目全湿,但没有把泪珠滚出来。她一声不吭,任凭它们在脸上滚着。滚了一阵,她努力把后面的泪咽回去。多少有一点眼疾,泪腺循环不好,平时无大碍,医生叮嘱过,要注意过度伤感流泪。
惜惜蹲下去,把带来的鲜花和水果,在石碑前一一摆放。
“来,惜惜,给你男人烧两刀纸。”婆婆说。
惜惜在婆婆身边蹲下来,学着婆婆的样子,将几刀纸一点点散开,又折叠成钱的形状,然后一摞一摞送进跳跃的火焰。
“我的儿啊……老天爷啊,上辈子造什么孽了,你要罚就罚我好了,你怎么不把我带走哇……春风走了,我该怎么活啊!”婆婆连哭带诉,鼻涕眼泪揉在一起,雨泪滂沱。
“妈,别太伤心了,别伤着身子,你还有浩浩呢。”
“你男人没了,你就不伤心吗?孙子是孙子,儿子是儿子,浩浩能代替他爸吗?”婆婆哭声稍止,从泪眼里飞出刀刃一样的眼神,在儿媳光洁柔美的面庞划过,又在儿媳曲线优美的身段上猛划一下,再划一下,划完了,又埋下头继续哭唱。
陈惜惜不再回应,保持了一份悲伤的沉默。
四月的微风吹乱了她乌黑的卷发,她没有哭出声来,只有浓得化不开的哀伤,在那双湖水一般清澈幽深的美丽眼眸里,冰凝着;还有无法说出的痛楚,在心底里深深地冻结。
离开墓园,陈惜惜开车送婆婆回医院,一路上,婆婆哭着要出院。
“在那地方再住下去,我真没法活了,医院那不是人待的地儿,这辈子,我真没想到我也会住院啊,真是住不下去了……”婆婆眼泪汪汪地说着。
“好,妈,我这就找医生谈谈,咱尽可能快些出院。”陈惜惜轻声慢语地应和着。
和医生谈过。医生表示,病人扭伤属于比较严重的那种,手术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执意要出院,若不能每天及时换药而造成感染,后果自负。陈惜惜权衡再三,花了一小时做婆婆的思想工作,婆婆同意一周后再考虑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