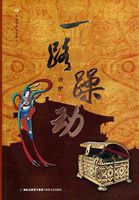一
离开中南海颐年堂,聂荣臻赶回军委作战部值班室,叫值机员立刻接通在安东的彭德怀。
彭德怀不在总部,也不在几个军部,值机员真有本事,他最后在鸭绿江渡口,通过40军的指挥所电话找到了彭德怀,他正在视察过江地点。
江水声很大,声波又弱,彭德怀大喊大叫一阵,总算听清了,聂荣臻告诉他,毛泽东让他暂不执行9号命令,立刻与高岗同机星夜返京。
放下电话,彭德怀说:“看来,赴朝作战的计划又变了。”
邓华猜测地说:“估计是总理在苏联谈得不顺利。”
彭德怀说:“别乱猜了,给我备车,我连夜赶到沈阳。”
就在彭德怀、高岗乘夜航机返京的时候,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又经历了一次自我意识的较量,他忽而站在中方,忽而站在朝方,忽而又设身处地为斯大林着想。
他又是一夜未曾合眼。
床上的被子依然叠得整整齐齐。
时钟指针指向凌晨3点。
毛泽东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口中叼着香烟,他并不吸,烟灰积了有一寸长。
一个卫士轻轻走进来,问:“要吃夜宵吗?”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什么时候吃过夜宵?”
卫士悄然退下。
毛泽东走了出去。
南海水中有几只惊鸿扑棱棱地飞起来,越过朦朦胧胧的北海石桥,向白塔后边飞过去了。
残月在水中抖动着光影,晚风飒飒地吹过一片竹林。
毛泽东在水边走着,脚步很慢、很轻。
一只水鸟轻轻掠过水面,飞入林中,又复归一片静寂。
毛泽东后来干脆跳入水中,在凉津津的水中漫游起来。经水一激,他仿佛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在暗自责怪自己,怎么可以因小害大呢?他再一次确认,出兵朝鲜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苏联的态度而动摇。
当他在水里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去吃了一碗麦片粥,就到颐年堂去开政治局会议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仿佛什么周折都没发生一样,详细地询问了13兵团出国前的准备情况。
彭德怀虽觉奇怪,却也没有多问,如实地告诉毛泽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指什么?也许各有各的理解,毛泽东没有追问。
会议很快散了,毛泽东让彭德怀慢走一步。
毛泽东单独对彭德怀说:“你马上给邓华、洪学智他们拍电报,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他们,你们跨过鸭绿江的时间定在19日,怎么样?”
彭德怀说:“可以。”
毛泽东说:“第一阶段,我们没有空军掩护,可以专打李承晚军队,对付伪军你是有把握的。”
彭德怀说:“斯大林怎么又变卦了呢?”
毛泽东说:“斯大林说没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
彭德怀说:“斯大林几次提到要金日成上山打游击,又说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看来他是不想伸手了。”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能言而无信。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
彭德怀说:“他看到我们要动真格的了,他就犹豫了。”
毛泽东说:“他始终瞧不起我们的土八路。他说我是个农民,一个农民领导的军队,打败了蒋介石,已经是个奇迹,今天又不自量力去同美国碰,他心里没有底。”
彭德怀说:“打败了也不关他事。”
“不然。”毛泽东说,“我们打胜了,他当然高兴。一旦我们打败了,他怕把苏联卷进来,苏联就没有退路,就要冒着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危险。我现在已不再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什么希望了,求人不如求己,彭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彭德怀说:“没有空军掩护,我采用老手法,夜间行动,夜间他飞机也奈何我不得。”
毛泽东说:“我已告诉周恩来,在苏联多停几天。”
彭德怀说:“你还指望斯大林回心转意?”
毛泽东说:“苏联白给武器装备,咱不敢奢望,采用租借办法总可以吧。”
彭德怀说:“万一他要现钱呢?”
毛泽东说:“那不至于,我是两袖清风,哪里拿得出现汇来呀!气话归气话,我还是希望两个月以后斯大林能兑现诺言,那时再说没有准备好,总说不过去了吧?如果一直没有空中掩护,会影响我们的整个战略部署。”
彭德怀说:“真够难的了。”
“你更难。”毛泽东说,“你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呀,惟你彭老总可以力挽狂澜,好自为之。”
两个人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彭德怀敬了个军礼:“我们下午就回去。”
二
10月13日,心情相当复杂的周恩来又一次来到斯大林在黑海之滨的别墅办公室。
斯大林座位的背后墙上高悬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巨幅画像,这两个历史名将的目光永远盯着来访者。
斯大林起身让坐,问:“毛泽东给你回电了吗?”
周恩来沉静地回答:“是的。”
斯大林出奇平静地问:“取消了出兵计划,是吗?”
“不。”周恩来说,“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再多、再大,见死不救也是不应该的。经过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决定计划不变,已电令13兵团所属4个军及3个炮兵师即刻准备过江去作战。”
由于意外,斯大林呆了半晌。
斯大林的目光闪电般来回在周恩来的脸上扫视着,他突然觉得那眼神里流露出中国人特有的倔强,不,不是倔强,而应当说是悲壮。
斯大林的心动了一下,一时甚至不敢与那双黑色纯净的眸子对视。他当然知道,这决定意味着什么!可以说,中国人现在连一架可以升空作战的飞机都没有,而美国已经飞到朝鲜的飞机就有上千架。
斯大林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水,他知道这是感动的泪水。他不想让周恩来看见,忙把头掉向窗外波涛起伏的大海。
他的心也像那大海一样不平静。他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叹息一声:毛泽东,我确实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中国同志真伟大!
三
风尘仆仆的彭德怀又飞回了沈阳,这是10月15日的早晨,距离出兵还有四天。各军备战气氛越来越浓,真的有鼙鼓动地之势了。彭德怀就在高岗的办公室里洗了把脸,让高岗给他弄两个馒头,然后赶回安东去。
高岗说:“刚下飞机,休息一下,明天再到前面去。”
彭德怀说:“不行。火车赶不上,我坐汽车走,还有不少战士没有棉衣呢,你可小心我告你状。”
高岗说:“李聚奎都在装车了,50 000套棉军装一天以后到安东。”
这时,秘书李望进来:“彭总,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到了。”
彭德怀看了高岗一眼,没等说话,朴宪永已经进来了。
不用问,彭德怀也知道他是来告急的。方才彭德怀得到的最新情报是,美军盖伊师的第7骑兵团离平壤不过5公里,白善烨的南韩第1师也只有8英里。麦克阿瑟正督令沃克和阿尔蒙德沿太白山分水岭从东西两面向北进击。
彭德怀赶紧穿上外衣,拉把椅子让他坐。
“没心思坐了。”朴宪永说,“平壤告急,如果丢了平壤,影响太大了,金首相说……”
彭德怀大手一挥,打断他:“别说了!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们中央已经最后决定,10月18或19日分批渡江,请转告金日成同志,你们在这几天里尽量迟滞敌人,拖住敌人。”
朴宪永用力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太谢谢了。听苏联顾问说,苏联出动不了空军,我以为中国兄弟也改变计划了呢。”
彭德怀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中国人说话算数。”
高岗感慨地说:“毛主席十几天之内,瘦了一大圈,可见其决心之难下啊。”
他所以这么说,是想让朝鲜朋友知道,你们难,我们又何尝不难,家家都有难唱曲,只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义字为上,从来不愿叫苦就是了。
就在彭德怀已经对苏联的空中掩护不抱任何幻想时,事情又突然有了转机。周恩来已从黑海之滨回到了莫斯科,他心里很烦闷,只能打道回府了。看着随从人员在打点行装,打点斯大林送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他走了出来。在院子里,翻译师哲兴高采烈地跑过来嚷道:“总理,大好消息。”
他把一份译好的电报送到周恩来手上。
师哲说:“看来,斯大林真的受感动了,一下子答应出动16个飞行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我们,武器装备也同意以信贷方式办理。”
周恩来也很高兴,说:“立刻给毛主席发报,彭老总可能急坏了,听了这消息,彭老总压力就小多了。”
师哲就在宾馆的院子里起草好了电报,周恩来看过,改了几处,告诉他快去发急电,必要时求助莫洛托夫。
师哲还没走出宾馆院子,苏联外交部的一部吉姆车开来了,从车上走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说莫洛托夫请周总理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
周恩来分析是商讨援助的具体细节,他对师哲说:“电报拿到那里去发,走,我们马上去克里姆林宫。”
吉姆车载着周恩来越过克里姆林宫旁的无名烈士墓,大理石平台上的钢盔、战旗的铜雕沐浴在永不熄灭的一簇圣火下,熠熠闪光,这一切都令人激动。一个酷爱独立、自由并为之付出过几千万人生命代价的民族,当然不用别人教,就知道自由的可贵。
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主任说部长要10分钟以后回来,现在正在路上,请周恩来到会客厅去喝咖啡。
周恩来想享受一下秋日的阳光,就带着师哲来到克里姆林宫的院子。
安谧而浩大的皇家园林与中国的格局大不相同。中国的故宫到处是青砖漫地,汉白玉台阶、石栏以及青石的龙凤巨雕。这里却到处是草坪、鲜花。
他们信步走到一处草坪,一个30多岁的清洁工扎着半截白围裙正在剔除草丛中的片片落叶。看起来她是个开朗的人,她抬头冲周恩来笑笑,问:“中国人?”
师哲说:“是的,你好吗?”
那女工说她叫波丽雅,早在1937年就来到克里姆林宫了,她说她刚来的时候卫兵不让她进门,因为她穿着乡下人的草鞋,她不得不去亲戚家借一双靴子。
周恩来说:“现在不会有人拦你了吧?因为你呆了13年了。”
波丽雅有些自豪地说:“是啊。在克里姆林宫,只有两个人不用出示通行证,一个是斯大林,另一个是我。”
周恩来笑了起来:“你和斯大林是平等的嘛。”
波丽雅开心地笑道:“是呀。他负责拾掇全苏联,我负责收拾克里姆林宫,他那个不如我这个好拾掇。”
周恩来又忍不住笑起来,问:“你与斯大林很熟吗?”
“他是个很好的人。”波丽雅说:“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只有他进门之前每次都先擦脚。”
这时莫洛托夫的车开了过来,当莫洛托夫从汽车里下来时,波丽雅指了指他说:“他最干净,他的办公室我几乎不用打扫,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就不行了,纸篓里总是塞满了纸团,贝利亚更糟,废纸都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叫你没法收拾……”
周恩来意识到不能再与这个饶舌的女工谈下去了,冲她笑笑,走近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久等了,对不起。”
周恩来说:“在这里,度日如年啊。感谢你们的慷慨承诺,我明天就启程回国。”
他站着不动,似乎都不想再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去了。
莫洛托夫当然不会这样怠慢客人,还是把他们请进了他的办公室。
真如波丽雅所说,他的办公室洁净得出奇,桌面都像镜子一样光洁可鉴。
莫洛托夫亲自给客人端来了咖啡,周恩来突然发现莫洛托夫的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闪着他。
周恩来的心不禁格登一沉。
莫洛托夫犹豫了一下,说:“很遗憾。方才我刚接到斯大林同志从黑海打来的电话,他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你们志愿军作战,昨天的承诺取消了。”
师哲忍不住地问:“怎么又变了?”
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同志考虑得更长远、更全面,你们不必这样难过。”
周恩来幽幽地说:“如果我们只从自己考虑,我们满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
莫洛托夫听了,半晌没说出话来。
周恩来还能说什么呢?他似乎也认为斯大林朝令夕改,太过分了。斯大林表达歉意的方式,是让莫洛托夫告诉中国朋友,赠送一批鱼子酱。
周恩来说:“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品味鱼子酱的条件,你知道我们更需要的是民族的尊严,为了扞卫这一尊严,吃鱼子酱不是第一位的。”
莫洛托夫更加无言以对了。
四
安东靠近鸭绿江的地方有一带葱翠的丘陵,叫镇江山,山腰有几栋旧式别墅,还是日本统治东北时为占领军长官所盖,现在临时成了第13兵团的司令部。
彭德怀正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13兵团领导及军长们开会。
张国放坐在门口往小本子上记录。
彭德怀说:“现在什么承诺也没有了,朝鲜那边天天在流血,我们不能再等了。各军准备马上过江。”
解方说:“现在,美国和联合国军在朝鲜共有兵力42万,飞机1100百多架,军舰300多艘,其中美军3个军6个师,李承晚9个师。”
彭德怀说:“麦克阿瑟嚣张得很,他前天对记者说,他几乎是进入了没有抵抗的军事空白区,我们让他尝尝空白区的滋味。”
彭德怀又说:“我们原来研究先过去2个军、2个炮兵师,我怕鸭绿江桥一旦被炸,我们过江就要延迟,不易集中优势兵力。现毛主席已经答复,同意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过江。
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我们在国内常用的大踏步前行、大踏步后退的战术,不一定用得上,我们可能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消灭之。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能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身份自居。要做长期艰苦的作战准备。”
这时毛岸英从会议室经过,一眼看见了坐在门口的张国放,一时愣住。
张国放走了出来,恰好一个小警卫员过来,向张国放敬礼:“张副军长,文件已送到下面去了!”
毛岸英惊讶地说:“原来你是副军长!”
张国放说:“不像,是不是?怎么样,拜师的事,你不会变卦吧?”
毛岸英说:“我可不敢收你这么大的人物当学生。”两个人都笑了。
这时,一个干部带着一个女同志走过来,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住张国放的袖子说:“原来逃兵在这里!”
张国放急忙解释:“我在开会,开了会就回去。”他对毛岸英解释道:“这位是我们的卫生处长,这位是后方医院的江医生,我有点发烧,所以事实上是他们的俘虏。”
毛岸英笑了起来。
江小帆说:“他可不是发点烧,大叶性肺炎。”
张国放说:“这是小孩得的毛病嘛。”
江小帆说:“你不好好治,一个月都出不了院。”
“那可不行。”张国放说,“3天之内,我必须出院。”
女医生笑了:“你以为是彭老总命令你守301高地呀?”
人们全乐了。
张国放叹了口气:“好吧,逃兵归队。”
毛岸英说:“回头我去看你。”
五
仁川登陆和越过三八线的业绩,使麦克阿瑟的神话又一阵风地吹遍了北美洲。
杜鲁门决定摒弃前嫌,拿出一个姿态,要会见麦克阿瑟。基于以往的教训,杜鲁门不好以召见的惯例让麦克阿瑟回国去述职,他肯定会拿军务倥偬为挡箭牌堵回去。后来还是约翰逊为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在太平洋中间选择了一个小岛——威克岛,两个人赶到那里去会面,就没有一点“召见”之嫌,麦克阿瑟会理解为平等的会晤的。
杜鲁门纯粹出于讨好或和解,也大没必要,他在任不会久了,又不谋求连任,他无需讨好谁。他隐约有一种担忧,怕美军打过三八线去惹恼了中国人,如果他们一出兵,可就不妙了。
杜鲁门希望这方面能与麦克阿瑟达成一个共识,杜鲁门希望体面地当完他总统任期的最后1个小时。
“独立号”飞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流云在机翼下飞逝。
杜鲁门率领着布莱德雷、佩斯等12人前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
此时杜鲁门正与布莱德雷等人坐在沙发上闲谈。国务院女秘书艾夫里尔·安德逊小姐过来给大家斟酒。她说:“干吗要飞这么远的路程,飞到波利尼西亚群岛来见麦克阿瑟呀?一个命令把他召回去不就得了吗?”
杜鲁门说:“我不能离开白宫太久,麦克阿瑟也不能离开东京太久,威克岛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这不是正合适吗?”
布莱德雷说:“平壤指日可下,胜利已成定局,北朝鲜已经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麦克阿瑟现在有吹的了。”
杜鲁门说:“这正是我急于要见他的原因。他必须受点约束,要防止他更大的冒险。”
威克岛是一个椰林蔽日的小岛,属于美国托管。麦克阿瑟和惠特尼是前一天乘坐“斯卡帕号”飞机飞来威克岛的,耗费了8个小时。他有些不快,认为杜鲁门多此一举。而当初在选地址时,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是选在了夏威夷,麦克阿瑟嫌远,杜鲁门妥协了,这一下杜鲁门要多飞几千英里。
估计杜鲁门一行快要到达时,惠特尼来到海军提供的瓦楞铁活动板房,叫起了没怎么休息好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穿着仍很随便,甚至连“水果沙拉”(戏指勋章)也不佩戴,就穿了敞领卡其衬衫,戴上软塌塌的军帽,走了出来。
机场上停着麦克阿瑟的座机。
此时麦克阿瑟正与惠特尼、驻朝大使穆乔在海滨漫步。
麦克阿瑟望着迷蒙的海天接壤的地方,问:“杜鲁门总统怎么还不到?”
惠特尼说:“他们距离威克岛远。”
穆乔看看表:“再有1小时可以到达。”
麦克阿瑟显得情绪不高,他冲口而出:“我讨厌为了政治原因被召见。”
穆乔问:“将军以为是政治原因吗?”
麦克阿瑟愤然地一挥手:“这还用问吗?我打败了,他们忧心忡忡;我胜利了,他们想在我身上拴一根绳子。”
惠特尼说:“不管怎样,我们越过三八线时,总统亲自拍来贺电,将军既然飞到这里来了,就别叫大家扫兴。”
麦克阿瑟说:“那好吧,我好好演这场戏。”
几个人都乐了。
海风强劲地吹拂着麦克阿瑟的衣角。他仰起头,看着天空。惠特尼、穆乔站在一旁。
“独立号”从天际出现了。跟在后面的三架也出现了。
“独立号”在机场跑道着陆。
舱门打开,麦克阿瑟大步迎了上去。
当杜鲁门走下舷梯时,麦克阿瑟敬了个礼,两人握手,麦克阿瑟说:“您好,总统先生。”
记者们围上来拍照。金丝吉挤在最前面。
杜鲁门微笑着说:“将军,你好吗?我能在威克岛上见到你十分高兴,我等待这次会晤已经等得太久了。”
麦克阿瑟说:“总统先生,我希望下次会晤不会隔得这么久。”
惠特尼在一旁窃笑,他很惊奇,麦克阿瑟今天这么乖,言不由衷地做着这一切。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随行者布莱德雷、佩斯、哈里曼等人握了手,奇怪地问:“艾奇逊先生怎么不来?”
也许因为麦克阿瑟经常说“不与国务院的政客们打交道”,惹恼了艾奇逊。这次杜鲁门拉他一起来威克岛时,艾奇逊拒绝了。艾奇逊挖苦地说:麦克阿瑟具有外国君主的许多特性,并且像任何一个外国君主一样难以对付,因此承认他的这一地位是不明智的。
难道杜鲁门可以把这话和盘托出吗?
杜鲁门带来了20多个记者,这些人拍了照,听了些官样文章的话后,杜鲁门就甩开了他们,与麦克阿瑟乘一辆老爷车开到威克岛东端一幢混凝土房子前,这是他们会谈的地方。进了屋子,杜鲁门脱去茄克坐下,环顾了一下这简陋的房子。
麦克阿瑟今天换了欧石南根大烟斗,礼貌地问:“总统先生,我抽烟您不介意吧?”
“不,”杜鲁门说,“我倒乐意让喷到我脸上的烟比别人多。将军抽烟请随意,只要不放火就行。”
周围的人轻松地大笑。
麦克阿瑟说:“朝鲜的局势不需要介绍了,白痴也会明白,胜利在望。”
“是的,我丝毫不怀疑。”杜鲁门说,“我最关心的是中国和苏联有无介入的可能。”
麦克阿瑟说:“可能性极小。如果他们在战争刚开始时干预,也许有点用处,现在太迟了。”
杜鲁门说:“据有关情报称,中国人在东北集结了30万军队,这是什么征兆?”
麦克阿瑟说:“我更相信我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的估计,他们真正可以出动作战的,不到50000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有空军,而我们在朝鲜有1 000多架飞机,有空军基地,中国人不会不知道,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意味着什么。”
杜鲁门说:“苏联可是有空军的呀!而且从它的远东基地起飞,几分钟就飞到你头顶上。”
麦克阿瑟说:“自然,苏联的空军力量不可低估,如果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苏联用空军掩护的话,会有这种可能。但中国的地面部队与苏联空军不会配合得很好,各怀心事,不像我们可以统一指挥。何况,苏联也没有空中掩护的迹象。总统尽可放心,不等中国出兵,我已经打赢了。”
杜鲁门说:“在远东,有一个很棘手的事,那就是对日和约问题。”
麦克阿瑟说:“朝鲜战争一结束,我们就签对日和约,斯大林不参加我们也签。我以为,总统先生不妨再宣布一个对远东的‘杜鲁门主义’。”好像他成了美国的决策人。
杜鲁门不无得意地笑起来。
这时,杜鲁门叫安德逊小姐:“把礼物拿来。”
安德逊小姐捧来一盒包装讲究的糖果。
杜鲁门说:“这是十磅布隆糖果,请将军转给您的夫人。”
麦克阿瑟说:“总统居然知道我的夫人爱吃布隆糖果?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功劳吗?”
杜鲁门大笑:“中央情报局没有这份细心。上飞机前,我的女儿提议,说日本肯定吃不到布隆糖果。玛格丽特说,有一次晚餐会上,她发觉将军的夫人特别偏爱布隆糖果。”
“谢谢您的千金小姐。”麦克阿瑟说,“可惜我却没有回敬的礼物,我总不能搬一发炮弹请总统捎回华盛顿去呀!”
人们又大笑。
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餐简单的饭后,会晤就算画了句号。
在去往威克岛机场的路上,麦克阿瑟显得很随和。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走在前边,其他的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麦克阿瑟说:“我是个爱放炮的人,我的讲话常常给总统先生惹麻烦,请不必介意。”
杜鲁门显得很高兴:“将军向别人道歉,平生这是第一次吧?”
麦克阿瑟说:“小时候有一次,我把妈妈做的熏鱼全喂了我的沙皮狗。”
杜鲁门哈哈大笑,他说:“自从我当总统以来,还未曾有过比这次更满意的会谈。”
麦克阿瑟问:“你有意竞选连任下届总统吗?”
杜鲁门说:“不,我不竞选了。而且我想在我任期内建议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
麦克阿瑟说:“这很英明,再出类拔萃的人,在最高权力的椅子上坐久了,也会变得愚蠢、昏聩起来。”
杜鲁门说:“听你的口气,你似乎有从政的政治抱负?”
麦克阿瑟说:“政治太肮脏。1944年、1948年我被政客们耍弄,当了两次傻瓜。”
杜鲁门没想到这两次竞选,麦克阿瑟竟把自己看成了受捉弄的人。
至少,杜鲁门对1944年的竞选是知道内幕的,那时麦克阿瑟在打仗,内华达州一个初出茅庐的保守议员阿伯特·米勒博士推举他,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可是后来很惨,他的竞选对手杜威得了1 056票,麦克阿瑟是1票,这使麦克阿瑟大丢其脸,他急忙发表声明,说自己“无意于此”。
而据杜鲁门所知,他好像在一封私人信中攻击了罗斯福总统,而这封信后来被那个米勒博士公布了,麦克阿瑟所说的别人拿他当傻瓜耍弄,大约指的是这件事。
杜鲁门当然也不便揭这个短。
麦克阿瑟看了杜鲁门一眼,又说:“不过,退出政坛后又可以变得清白。我这人,永远当不了总统。如果有哪位将军同你竞选的话,我想那是艾森豪威尔。”
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对政治还没有入门。噢,万一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他的政府会使格兰特政府看起来像一个好样板呢。”
麦克阿瑟笑了。
六
就在麦克阿瑟打保票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的时候,彭德怀又一次赶回安东。部下的人问他,毛泽东已是四下决心,自己犹豫了两次,会不会再变?
彭德怀对邓华、洪学智几个人说:“马上就过江了,变也来不及了。主席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说服政治局的同志,也要说服他自己呀。”
也许他的后两句话说出了毛泽东四下决心的深层原因。
这是10月17日,彭德怀带着邓华、洪学智等人在察看江边地形。
彭德怀说:“水浅的地方,可否考虑徒步涉水过河?几十万大军,只凭几座桥,又只能在晚间行动,怕不行。”
洪学智说:“已经找到了一些渡船,也可以搭浮桥。”
这时解方气喘吁吁跑来,递上一份电报:“彭总,中央军委电令,叫你立刻飞回北京,原定计划暂不执行。”
邓华问:“又出了什么岔头?”
彭德怀猜测说:“大概周恩来回来了。”
洪学智说:“彭老总方才还说再也不能变了呢!”
彭德怀只得下令取消原定过江命令,令部队待命,然后匆忙赶往沈阳搭机进京。
彭德怀到了北京立刻赶到颐年堂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同彭德怀交谈。
彭德怀说:“我刚给邓华拍去电报,明天晚上从安东、辑安过江,再不会变了吧?”
毛泽东说:“我是四下决心啊!还怎么变?斯大林已经是什么许诺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央会议上都一致决议出兵,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
周恩来说:“还可以往最好处争取。我觉得斯大林出尔反尔,变得太快了,一直纳闷,回来后才知道,罗申给他的报告,使他加深了对我们的疑虑。”
毛泽东问:“罗申大使打了什么小报告?”
周恩来说:“罗申不是多次求见过您吗?”
毛泽东说:“他只是一再申明,苏联是社会主义大本营,应得到保护,希望中国在苏联援助下独立承担战争责任。这我都答应下来了嘛。”
彭德怀说:“他是怕我们临死拉他当垫背的。”
周恩来说:“这位仁兄向斯大林报告时,表达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怀疑态度,他认为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把斯大林推入战争漩涡。”
毛泽东说:“这就难怪了。现在好了,咱们自己干!明朝万历年间,日本的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将军率20万大军入侵朝鲜,在釜山登陆,连克汉城、平壤,气势汹汹。明神宗当即派大将军李如松统兵援朝,夺回了汉城,驱逐了侵略者。如今,彭老总你再当一次李如松大将吧。”
彭德怀说:“但是,李如松耗银几百万两,丧师十几万。以今天的现代战争看,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我们的牺牲只能比明朝的李如松要大,战争将更为惨烈。”
毛泽东说:“是啊,自古以来,和平的代价都是鲜血,你彭老总辛苦了。”
彭德怀说:“主席放心,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我彭德怀眼都不会眨一下。”
毛泽东用力握住他的手。
七
上午10点30分,麦克阿瑟乘坐他那辆1941年式的凯迪拉克黑轿车去上班。他的车子一驶出驻日使馆,行车区间的警察和自卫队立刻封锁路面,过往的行人知道是麦克阿瑟去上班了。
他十分守时,下午两点回家吃中饭,他的车子出现在这段路上几乎分秒不差。于是时间一久,麦克阿瑟从家里到达第一大厦的5分钟车程,成了东京的一景。许多市民为一睹麦克阿瑟尊容,在10点35分或下午14时,在第一大厦门外静静等待就行了,准能见到麦克阿瑟,风雨不误。
今天在第一大厦门前围着的人仿佛比平时还多,由于心情好,麦克阿瑟下车后还跟前面的一些老太太寒暄了几句,引发了一阵阵笑声。
斯特拉特迈耶和惠特尼早在办公室等待麦克阿瑟了。
麦克阿瑟问斯特拉特迈耶:“第5航空队司令部和联合作战中心移到汉城了吗?”
斯特拉特迈耶说:“是的。根据您15日命令,其中第8、第18、第35中队也从日本进驻了金浦机场。”
“很好。”麦克阿瑟说,“向沃克和阿尔蒙德发布第4号作战命令。”
惠特尼马上拿笔记录。
麦克阿瑟说:“放弃原定计划,第8集团军、第10军将不在平壤、元山的蜂腰处会师,让两支部队单独前进,直捣鸭绿江边,放弃这一线由李承晚军队主攻的计划,改由美军担任。”
惠特尼提出异议:“这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不符。”
麦克阿瑟断然道:“不管它,战争由我来主导,而不是那些政客。”
惠特尼到隔壁房间去起草命令去了,他不单有倚马可待的速度,而且号称是麦克阿瑟的“第二大脑”,他能准确地在各种报告、文件、命令中体现麦克阿瑟精神,这可能是得到麦克阿瑟如此器重的最直接原因。而麦克阿瑟自己的文笔就差远了,金丝吉甚至说“很糟糕”,她怀疑念书的时候麦克阿瑟的作文可能经常不及格。
八
再有几小时就过江了。这是10月19日下午,天阴着,冷风在鸭绿江上“飕飕”地吹着,枯黄了的芦苇在风中瑟瑟抖动。
战士并不知道他们将开往何处,只有政治敏感的人能猜出八九。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密,甚至志愿军的军官们初期都穿上了裤线有红押条的朝鲜人民军马裤。
40军的一个团的驻地一片忙碌。
部队战士正在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有的在带炒面,有的在检查子弹,有的人把挎包里的书集中到院子里。
连长于占国见一个娃娃脸小眼睛的战士把一本小人书又掖回了挎包,就走过去,粗鲁地拽出来,扔到大堆书中去。
这时彭德怀带着毛岸英、李望走了进来。
那个小战士说:“带图的也不让带呀!上面没几个字呀!”
于占国说:“有一个字也不行。”
娃娃脸噘起嘴:“这叫打的什么仗啊!”
“庞小海!闭上你的臭嘴!”连长训斥了他一句,回头见彭德怀过来,敬了礼,刚要说什么,彭德怀制止了他。
彭德怀走过去,蹲在院中间一大堆书旁,见有识字课本,有《论持久战》,也有小人书。
彭德怀问庞小海:“干吗生气呀?嘴噘得能拴头驴。”
周围战士哈哈大笑。
庞小海说:“连长不让带有字的书,我那是小人书啊,没几个字。”
“是这本吗?”彭德怀拾起来,原来是一本连环画:《失街亭》。他忍不住笑了,“你看的这是儿童团的玩艺儿呀!”
庞小海说:“才不是呢。这是我参军时,老农会大叔特地跑到山城镇给我买的。他说,这是长心眼的书,那个叫马什么的,就是没学好兵书,失了街亭,叫诸葛亮砍了脑袋,我不学学,能打好仗吗?”
彭德怀忍不住大笑。
连长于占国说:“别叫人笑掉了大牙吧!你一个小兵还想指挥打仗?那是将军的事。”
彭德怀说:“这话可不对了哟!法国的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几十年后,我们这位看连环画的小兵,说不定就是一位将军了呢。”
庞小海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别逗着玩了,你这胡子拉碴一大把年纪了,不也没熬上个将军?你大概还在炊事班吧?”
彭德怀、毛岸英大笑不止。
于占国申斥道:“胡说,你又小看人!这位首长,少说也是团、营首长,你怎么看人家是伙夫!”
正巧这时,40军军长温玉成和政委袁升平过来了,见了彭德怀,马上给彭德怀打立正。
于占国愣了,所有战士们都目瞪口呆。
庞小海伸出了舌头:“我的妈呀!这得多大的官呀,我们军长都向他打立正。”
彭德怀拍了拍庞小海的头:“没多大官。你听连长的话,叫你交出有字的书来,必有道理。
留个姓名吧,交个朋友嘛。”
“我叫庞小海,庞统的庞。”他说。
“噢!知道了。庞统号称凤雏先生,是三国时有名的谋士、大将军。好了,再见了,未来的将军。”
庞小海说:“你叫什么呀,首长?”
彭德怀说:“彭德怀。”
战士们全都欢呼起来:“彭老总!”
温玉成说:“走吧,找你都找疯了。”
袁升平说:“给你弄了一辆嘎斯六九车,给你找了个东北籍的司机,叫唐祥,车开得好。朝鲜都是山路,南方人玩不转。”
彭德怀刚要走,一个战士说:“首长,我有意见,连长说过了江,不让我们说中国话,有事打哑语,这不把人憋死呀!”
于占国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啊!再说,教了他们一句呀,叫……叫什么卡哨了?”他自己反倒想不起来了。
庞小海说:“毛拉卡哨。”
于占国说:“对,不管见了人问你啥,一律毛拉卡哨,不知道的意思。”
彭德怀对温玉成说:“看来得做点解释工作,保密可别把战士都憋哑巴了。”
人们又都笑起来。
九
安东的后方医院也是临时性的,占了一所中学。
张国放焦灼不安地躺在病床上。他悄悄地把背包从床底下拿起来,把牙具往里放。
忽听“嘻嘻”一声笑,他抬头一看,是苹果脸大眼睛的机灵鬼小护士丁梅。丁梅问:“军长大人,干吗呢?”
张国放若无其事地说:“没事,看看背包。”
“背包里又不藏耗子,看它干吗?”丁梅伸出手去,“拿来吧。”她在要体温计。
张国放磨磨蹭蹭地在被窝里摸着。
丁梅说:“你这人,把体温计夹哪里去了?”
张国放拿出了体温计交给小护士,她冲亮处一看,皱起了眉头:“咦?”
张国放问:“下来了吧?我早就感觉不热了。”
丁梅讥讽地说:“不热是不热了,有点发冷了吧?”说着,她冷不丁走过去,猛然一把掀开张国放的被子,里面有个饭盒,饭盒里装着些冰块。
张国放伸手去抢饭盒,丁梅早抢先拿在手里。“好啊,你骗人,把体温计插到冰里,我说呢,这人的体温怎么35度以下了呢!”丁梅忍不住笑,张国放也笑。
张国放求情道:“丁梅,小同志,你若放过我这一马,我永生永世都记着报你恩。”
“是吗?”丁梅说,“谈判吧,啥条件?”
张国放说:“我给你买两本书。”
丁梅说:“我自己会买。”
张国放说:“一支大金星笔。”他真的拿出来一支金笔。
丁梅说:“不稀罕。”
张国放为难地问:“那,你要什么?”
丁梅有几分神秘地说:“我跟着你,你上哪,我上哪。”
张国放说:“我回部队呀。”
丁梅说:“别保密了,你们要——过——江。”她小声却又一字一顿地说了出来。
“我不知道,”张国放装傻,“过什么江?”
“你就在这装糊涂吧。”丁梅说,转身要走。
张国放急着跳下地去拦挡:“别呀,再谈谈。”
丁梅扑哧一下笑了:“你呀!你若答应带我走,我告诉你一个门路,只要江医生点个头,病历一改,你就走了。”
张国放说:“你这个人挺厉害。小看你不得呀。”
丁梅说:“江医生也正闹着上前线呢,人家不批,和你同病相怜!”
“是吗?”张国放下地穿鞋,说,“我去试试看。”
部队就要过江了,张国放怎么能在这时候掉队?他真是急死了。
医生值班室里只有江小帆一个人在,机会很好。
张国放悄悄进来。
江小帆道:“体温35度的同志来了?快请坐。”
张国放一笑,只好任她奚落。
江小帆说:“幸亏体温计的下限只有35度,不然你得降到零下去。”
张国放说:“我是来求你的,江医生,我今天晚上必须归队。”
江小帆说:“我不能放一个发高烧的病人出院。”
张国放说:“丁梅不是跟你说了吗?”
江小帆问:“说什么?”
张国放说:“交换条件。”
江小帆说:“好吧。你若给我们林院长打个电话,他放我走,你也立刻可以走。”
张国放说:“可是……无缘无故给一个女同志说情,容易引起误会吧……”
江小帆说:“那你就回病床上躺着去。”
张国放犹豫了半天,拿起了电话:“挂院长室。喂,林院长吗?我是张国放……啊,好了,全好了,怎么,信不过我,还要江大夫说话?”
他把电话递给了江小帆,并向她作揖。
江小帆说:“烧退了,可以出院了,是吗?他们吴军长一天打了四次电话来催问,好,好,你等等,张军长还有话。”又把听筒递给了张国放。
张国放这下可为了难,迟疑半天,说:“啊,将来请你下馆子。”放下了听筒。
江小帆说:“咦,你这人过河拆桥!”
张国放说:“实在张不开口,会有机会的。”
江小帆闪动着长长的黑睫毛,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我就知道你不可能为我说情。”
张国放说:“我们39军的军医、卫生员缺好几十呢!你又是干外科的,你能到我们那去,我绝对举双手欢迎。只是……”“你别害怕,我赖不上你。”江小帆说,“只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朝鲜战场上见吧。”
张国放说了声“谢谢”,向江小帆郑重地敬了个军礼,江小帆反倒脸红了,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十
彭德怀已经做好了过江的准备,洪学智来告诉他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过江来了。
“快请。”彭德怀推开地图,站了起来。
朴一禹一见彭德怀,就问:“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了没有?”
彭德怀说:“已经定下来了,时间就在今天晚上。”
朴一禹眼含泪水,激动地说:“太好了,这就好了,你们若再不出兵,问题可就严重了。”
彭德怀又拉过地图,说:“你看,我们4个军、3个炮兵师分东、中、西三路同时过江。40军从安东和长甸河口过江,之后向球场、德川、宁边地区开进;39军从安东和长甸河口过江,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42军从辑安过江,向社仓里、五老地区开进;38军尾随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朴一禹说:“形势危急呀,昨天,敌人三面包围并向平壤发起了攻势,到昨天下午,已经突破我两道防线,在空军炮兵支援下,以坦克为先导,正向平壤发起总攻,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停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说:“平壤的陷落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目前,美军正在狂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呢。”
屋子里一片沉寂。
彭德怀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朴一禹道:“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正组织党政机关向新义州、江界实施战略总退却,临时首都也迁到了江界,眼下具体打算还没来得及研究,金首相请总司令赶快入朝,共商抗美大计。”
彭德怀问:“金首相现在在哪里?”
朴一禹摇摇头:“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介川到熙川这条线上向北撤。美国人的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金首相需要不断地转移,行踪不定。”
彭德怀说:“那我们就去找。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朴一禹说:“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动身。”
彭德怀重重地一拍桌子,说:“那好,说走就走。”他又略作思索,对着邓华、洪学智说:
“敌进甚急,我得马上入朝,你们几位把部队入朝后的作战具体任务、集结地点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再仔细研究一下,在出发前电告各军、各师,也电告我。另外,部队过江一定要组织好,不能出纰漏,明白吗?”
邓华敬礼:“明白了,彭总,您放心走吧。”
彭德怀走到了门口,又站住,回过头来凝视邓华等人良久,才对李望、刘亮、谢大川等人一挥手,跨出门去。
十一
从空中往下看,平壤城裹在浓烟烈火之中。看得见几路攻城美军在向市区挺进。
大批北撤的军民几乎堵塞了道路。
敌人的B-29、B-26轰炸机铺天盖地飞过平壤上空,炸弹纷纷尖啸着落下,城内火光冲天。
山炮、榴弹炮群在城外轰击。
朝鲜人民军在最后一道防线抵抗。
敌人潘兴式M-26坦克、谢尔曼式中型坦克和MA3坦克开路,步兵正发起集团冲锋。
沃克坐在飞机上在天上指挥,他在对着话筒大叫:“重炮群向东面轰击……”
看着脚下的火光和曳光弹道,贝尔顿说:“太壮观了,只有美国能打这样的仗。”
沃克叫:“爬高一点,别叫我们自己人的炮火把咱们打下去。”
贝尔顿将飞机猛升起来。
得意洋洋的沃克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此时,浩浩荡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跨过界河,并将改变沃克一生的命运。
安东成了军人的城市,军队在开拔,满街是黄色的人流,饱受美国飞机轰炸之苦的安东市民都跑出来送行,嘴上不说,谁都明白大军是往哪开的。
黄昏降临了,对岸的新义州很静,江水无声地卷着漩涡流淌着。
40军开始过江了,个个神色严肃,这些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们脚步匆急地踏上了鸭绿江大铁桥。离远看像是一堵流动的人墙。
汽车上桥了,炮车上桥了,浩浩荡荡。
几辆吉普车停在桥下。39军军长吴信泉和40军军长温玉成在看着部队过江。
忽然,温玉成向队伍里一指:“那不是你的张副军长吗?”
吴信泉眼一亮,叫了声:“张国放!”
张国放从吉普车上跳下来。
吴信泉说:“好呀,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泡病号呢!你倒来得麻利!怎么样,全好了,烧退了?”
张国放说:“退了。”
“差点退到零下呢!”下半句是刚刚赶来的江小帆接上的话茬,她跑得直喘。
“怎么回事?”吴信泉问,“还让人家江医生追了来,噢,你是开小差的?”
温玉成说:“很可疑。”
江小帆打圆场说:“是有正式出院手续的。”她从挎包里拿出些针剂、片剂,送到张国放手上说:“针和药不能停,你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
张国放说:“谢谢。”
江小帆看了张国放一眼,又看了温玉成、吴信泉一眼,说:“我走了,再见。”
张国放站在原地没动,摆了摆手。
江小帆跑下了斜坡,突然站住,像冷不丁想起什么事似的叫:“张军长,忘了一件事。”
这意思当然是让张国放过去。张国放犹豫了一下,看了温玉成、吴信泉一眼,走下了铁路桥坡。
来到江小帆面前,江小帆却又没话了。
张国放有点着急,问:“什么事呀?”
江小帆这才说:“你这人,不讲信用。”
张国放说:“其实,我……是愿意给你说说情的,可是……”
江小帆笑笑说:“现在是抽调一小部分人入朝,过一段,我们后方医院可能集体入朝呢。”
“那太好了,我们又能见面了。”张国放说。
“我可不希望你来住院时才见。”江小帆说。
张国放回头望一眼正在过江的部队,说了声:“我得走了。”右手举到了帽檐上。
他大步跑上了桥坡。
他偶一回头,见江小帆犹在招手。
回到温玉成、吴信泉跟前,吴信泉说:“怎么,好像发烧烧出感情来了嘛。”
温玉成说:“判断准确,这感情有55度了。”
张国放说:“你喝白干呀?”
几个人笑起来。